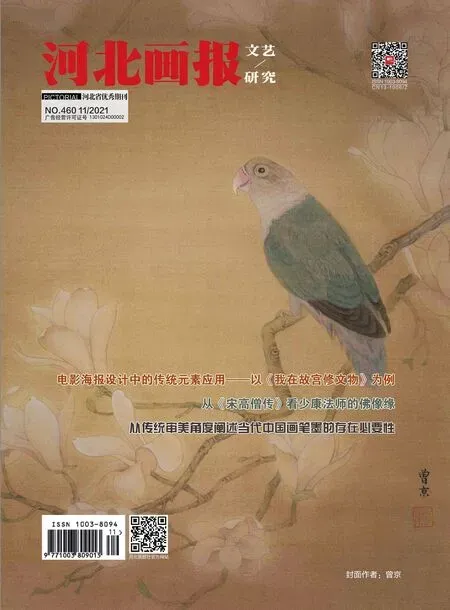淺析綜合材料在當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的應(yīng)用
魯學杰
青島大學
一、綜合材料與當代藝術(shù)的關(guān)系
關(guān)于運用材料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20世紀的西方藝術(shù)家進行了早期的實踐探索。20世紀初,從立體派領(lǐng)軍人物畢加索和勃拉克開始,他們選擇各種金屬片、紡織物、木材、紙張等,結(jié)合繪畫效果,創(chuàng)作了一些作品。其后,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藝術(shù)家勞森伯格、西班牙藝術(shù)家塔皮艾斯,以及法國藝術(shù)家杜布菲創(chuàng)作的作品非常具有代表意義。他們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打破了傳統(tǒng)媒介,開拓了更豐富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影響深遠。
而中國則起步較晚,在20世紀末才開始逐漸接觸綜合材料藝術(shù)。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的綜合材料藝術(shù)創(chuàng)作應(yīng)運而生。1979年10月,由張仃、袁運甫、肖惠祥、祝大年等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的首都機場壁畫面世,改變了當時現(xiàn)實主義一家獨大的狀態(tài),開啟了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新階段。
二、綜合材料在當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的典型表現(xiàn)
(一)安塞爾姆·基弗
安塞爾姆·基弗,戰(zhàn)后德國著名藝術(shù)家,德國新表現(xiàn)主義代表藝術(shù)家之一。他通過繪畫、裝置、版畫、攝影、雕塑等形式創(chuàng)作作品,表達了他對歷史、戰(zhàn)爭、道德和人性的的探索與研究,體現(xiàn)了對本民族的精神和文明的理解和感悟。他的作品主要描繪了德國的歷史和文化,進一步帶觀者進入更廣闊的世界。基弗運用了多種材料,這使得他的作品擁有獨特的閃光點,進而把作品的精神內(nèi)含表達的更加深刻。基弗的作品給人一種別開生面的震撼力和視覺沖擊力,這是因為他經(jīng)常采用巨大尺幅的畫布來進行創(chuàng)作。在其中,觀者能夠深深地感覺到殘酷的戰(zhàn)爭對德國造成的嚴重創(chuàng)傷。
在基弗的作品中,鉛材經(jīng)常出現(xiàn),比如《書》、《煉丹爐》、《舒拉密特》、《瑪格麗特》以及《容器的破碎》等。這些作品中不只有鉛材,它和其他材料結(jié)合,共同出現(xiàn)在畫面之中。鉛材為畫面增加了斑駁、破碎的肌理效果,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悲傷的情緒。鉛材自帶的屬性讓藝術(shù)家有更多的發(fā)揮余地。它可以變成不同的形態(tài),比如鉛絲、鉛皮等,依據(jù)藝術(shù)家不同的需要被運用到更多作品當中。此外最重要的一點是,鉛材擁有特殊的物質(zhì)美感:重量感、堅硬感。他的作品《書》中描畫的是海岸上一本用鉛做的書,加入了油彩、乳膠、蟲膠等其他材料。作品給人一種幽寂、悠靜、寥闊的感覺。這本書,表達了作者對人類智慧的懷疑之情。他用鉛材增強了畫面的表現(xiàn)力,使得其物質(zhì)性表現(xiàn)到最強,傳達出作品深刻的意義。
同樣,基弗也多次在作品中運用稻草。稻草的脆弱感和干枯的特質(zhì),像當時德國人的心中的壓抑和哀傷一樣易碎。稻草被用于基弗若干作品當中,豐富了其藝術(shù)表現(xiàn)語言,比如《紐倫堡》、《名歌手們》、《舒拉密特》、《從埃及起飛》、《瑪格麗特》等。在《紐倫堡》中,畫布上粘了一大片麥秸、稻草,沒有具體的物象描繪。畫面效果由近到遠迸發(fā)出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大的透視線的安排,使得畫面具有悠遠的空間感。天空的下部分是廣闊無邊的田野,暗示著當大面積的稻草燃燒后將變成一片廢墟,而這也象征著新的生機的出現(xiàn)。
(二)徐冰:《背后的故事》
除了日新月異發(fā)展的科學技術(shù),普通的材料亦能創(chuàng)造出驚人的藝術(shù)作品。從作品《天書》開始,徐冰以語言文字類的作品聞名于世,而《富春山居圖》則與以往不同。這件作品使用了眾多干枯的材料、麻絲、魚線、宣紙等日常可見的材料,經(jīng)過藝術(shù)家的自我發(fā)揮,變成了一幅利用光影來投影造型的中國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觀眾只有看到半透明玻璃的后面,才能發(fā)現(xiàn)這些組成的材料。它的基本表現(xiàn)形式:表面看上去是中國傳統(tǒng)山水畫,實際上卻不是。
徐冰從2004年開始創(chuàng)作“背后的故事”這一系列藝術(shù)作品,《富春山居圖》是其中進一步的推進。作品靈感來源于畫家偶然一次在機場發(fā)現(xiàn)玻璃后面盆栽植物的影子。這讓他想到鄭燮“依竹影畫竹”,鄭燮在《畫竹》中有,“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于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意為“只要是我畫竹子,沒有向老師學習,多是由紙窗、墻壁、日光和月影中受到啟發(fā)的”。
在大英博物館舉辦的個人展覽上,徐冰創(chuàng)作了《背后的故事7》,這件作品將清初“四王”之一的王時敏的山水畫立軸,轉(zhuǎn)變?yōu)楫敶囆g(shù)裝置。透過半透明玻璃,這些材料失去了本身的屬性,只剩下了造型和影子。材料與玻璃之間的距離成就了它們的作用,當它們離玻璃遠時,影子淡化,像水墨畫中的暈染效果;當離得近時,效果又像清楚的筆墨用法。這一切都得益于光的作用,光影細致微妙的變化使得作品更加豐富細膩。綜上,徐冰用這種方式展現(xiàn)的不只是一幅山水畫,更體現(xiàn)了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他用這種特別的方式激發(fā)了我們對于傳統(tǒng)文化更加深層的理解,給藝術(shù)家們以啟發(fā),更加有利于宣揚中國文化。
(三)蔡國強:火藥藝術(shù)
當代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材料和形式多樣,以火藥為載體的煙火爆炸藝術(shù)也是其中之一。火藥雖然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之一,但它在現(xiàn)代與藝術(shù)結(jié)合之中又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人文價值。一千多年以前,中國人發(fā)明火藥,用在歡樂上面。一千年以后,火藥引爆世界,成了眾多暴力的根源。無疑,爆炸是一種極致的暴力,能在瞬間摧毀一切,但是爆炸也是一種極致的藝術(shù)。因為藝術(shù)就是爆炸。幾乎所有國人,在節(jié)日里都看過升空的焰火。但有一個人,他把歷史當作線索,對火藥進行無盡的探索。他的存在,完美詮釋了:藝術(shù)就是爆炸。
蔡國強,世界頂級焰火藝術(shù)家。2008年,他把二十九個大腳印送上北京夜空,它們騰空走過了中國整整百年的奧運夢。除此之外,蔡國強用他的焰火,幾乎默默點亮了近年來我們所有重大節(jié)日的夜晚。1989年,蔡國強開始了自己的“外星人”計劃。歷史學家房龍在1937年出版的《地球的故事》中猜想:中國的長城是太空唯一能看得見的建筑物。于是蔡國強動員了大量的游客和志愿者,用六十萬克火藥鋪成一萬米引線,用一場延綿不斷的爆炸,把萬里長城延長了一萬米,企圖用火藥和宇宙對話。蔡國強的出現(xiàn),并不是對過去的藝術(shù)進行歸納總結(jié)。而是將火藥爆炸時能量的釋放,直接成為了藝術(shù)本身。
無序的爆炸是破壞,而有序的爆炸是藝術(shù),為了讓焰火從無序到有序,蔡國強和團隊研制了“像素爆破”,在每一顆煙花里都植入電腦芯片,讓你可以以毫秒為單位,在指定時間、指定空間、指定的節(jié)奏,在空中綻放出你想要的圖案。從20世紀到21世紀,蔡國強的繪畫、裝置藝術(shù)以及焰火表演,徹底引爆了當代藝術(shù)。二十年來,他不斷嘗試,試著用天梯,去尋找火藥最初的“神奇感”。終于在他的家鄉(xiāng)泉州完成了。2015年6月15日,蔡國強點燃了天梯的引線。焰火,一種與經(jīng)典背道而馳的藝術(shù),它無法被博物館展出,無法收藏、無法拍賣,在攝像機都沒有發(fā)明的年代,它甚至無法被記錄。當你點燃導火線,能量積累,焰火沖向天空,在爆炸之前有那么一剎那的暫停。此刻,“火藥”這種特殊的材料實現(xiàn)了與藝術(shù)的完美碰撞。在人文價值和科學技術(shù)的共同作用下,蔡國強的煙火實踐用宏大敘事的藝術(shù)語言拓展了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為當代藝術(shù)注入極大的活力。
四、反思綜合材料在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
藝術(shù)家賦予了材料在藝術(shù)作品中的新的屬性,創(chuàng)作者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逐漸理解并取得成果。中國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應(yīng)該廣泛地引進國外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先進技術(shù)和理念,實現(xiàn)自我變革。其中,材料的表現(xiàn)方式應(yīng)與當代藝術(shù)進一步相互融合,使這種表現(xiàn)語言更適應(yīng)中國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使其更有張力和表現(xiàn)力。對于材料的取舍和使用以及再創(chuàng)造都要基于對于文化、社會、歷史等的深刻研究,才能更有力地彰顯綜合材料的價值。它改變了大眾對于繪畫的固有認知,極具革新意義,更有利于構(gòu)建中國文化精神,會對中國當代藝術(shù)樹立獨特的時代特征發(fā)揮極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