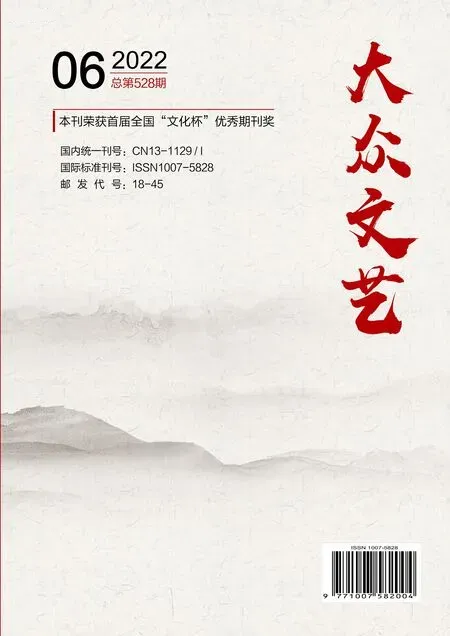文殊山石窟與敦煌石窟飛天樂舞形象比較研究
(河西學(xué)院音樂學(xué)院 734000)
中國的石窟建筑起初是仿造印度佛教石窟的造型形式開鑿的,多建在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地區(qū)1。本文以文殊山石窟與敦煌石窟飛天樂舞形象作為研究對象進(jìn)行比較研究,積極探索我國悠久的石窟文化,從敦煌樂舞藝術(shù)鑒賞的角度去探索其蘊(yùn)含的深刻內(nèi)涵,推動(dòng)中華傳統(tǒng)文化發(fā)揚(yáng)光大。
一、文殊山石窟與敦煌石窟概述
文殊山石窟位于我國甘肅省肅南市裕固族自治縣祁豐鎮(zhèn)境內(nèi),位于文殊山脈前山與后山山壁的崖壁上,南北約長1.5公里、東西約為2.5公里,占地面積約為780萬平方米2。文殊山石窟據(jù)有關(guān)史料記載始建于北涼時(shí)期(4O1—433),在北朝、隋、唐各時(shí)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擴(kuò)建,這一時(shí)期當(dāng)?shù)胤鸾涛幕焖侔l(fā)展,達(dá)到了空前繁榮的盛世局面,該地區(qū)是當(dāng)時(shí)佛教文化傳播的一個(gè)重要區(qū)域中心。文殊山石窟中較為重要的當(dāng)屬千佛洞和萬佛洞,洞中至今還保存著大量地壁畫、塑像等,有學(xué)者認(rèn)為洞中壁畫色彩鮮艷,是不可多得的北朝遺跡。石窟對以“飛天伎樂”藝術(shù)表達(dá)形式為重點(diǎn),畫中的筆墨、畫法多是沿襲了西域地區(qū)當(dāng)時(shí)所流行的凹凸暈染的繪畫技巧,帶給人們粗獷、艷麗的視覺沖擊。
與文殊山石窟相同,敦煌石窟同樣在我國石窟文化中占據(jù)重要地位。敦煌石窟現(xiàn)位于我國甘肅省敦煌市東南方位25公里的鳴沙山陡峭的石壁上,地處我國古代絲綢之路的戰(zhàn)略位置,不僅是聯(lián)通我國與中亞地區(qū)的重要地理紐帶,更是宗教、文化的重要交匯之處,處于重要的發(fā)展戰(zhàn)略地位3。敦煌石窟的開鑿與修建也經(jīng)歷了多個(gè)朝代,在飽受歲月的侵蝕后,以較為完整的姿態(tài)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該石窟群共有壁畫面積約四萬多平方米,多以飛天樂舞的藝術(shù)繪畫形式為人熟知。敦煌石窟壁畫富麗多姿,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臘等國家的古代藝術(shù)之長,呈現(xiàn)出不同的繪畫風(fēng)格,是中國古代美術(shù)史的光輝篇章。
二、文殊山石窟與敦煌石窟飛天樂舞形象概述
“敦煌樂舞”與“飛天伎樂”作為我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的特殊樂舞形式,寄托著人們對美好事物的向往,縱觀它優(yōu)美的舞姿,畫家用特殊的線條與色彩勾勒賦予了飛天伎樂鮮活的生命力,飛天樂舞形象以它婀娜飄逸的舞姿、扣人心弦的樂曲、纖細(xì)跳動(dòng)的線條,展現(xiàn)出獨(dú)特的敦煌舞蹈藝術(shù)表達(dá)形式,如同一個(gè)個(gè)閃爍的精靈,奏出了生命與舞姿相互結(jié)合的最強(qiáng)音。
飛天伎樂源自古印度的藝術(shù)表達(dá)形式與西方有翼天使的有機(jī)融合表現(xiàn)形式流入東方后,緊緊跟隨著中國古代道教“飛仙”的演進(jìn),轉(zhuǎn)變成為兩種表現(xiàn)文化相互交融的特殊藝術(shù)表達(dá)形式4。“飛天”是人類對生命與藝術(shù)的古老探索,將人的各種生活姿態(tài)與樂舞藝術(shù)有機(jī)結(jié)合,成功做到了“天人合一”的藝術(shù)最高境界,對后世來說具有深遠(yuǎn)而持久的重大影響。這不僅僅是偉大藝術(shù)的體現(xiàn),更是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下的獨(dú)特產(chǎn)物,它承載了中原與西域、佛教與傳統(tǒng)思想的文化基因與血脈,見證了佛教的傳播與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同時(shí),“飛天樂舞”藝術(shù)表達(dá)形式以優(yōu)美的樂舞深刻反映出西域文化與中原藝術(shù)相互交流的過程。由文殊山、敦煌石窟造像與壁畫可以明顯看出,不同時(shí)代的“飛天”文化都凝聚著濃厚的時(shí)代氣息,而這種迥然不同的風(fēng)格使“飛天”藝術(shù)兼有不同的審美特點(diǎn),這種不同審美特點(diǎn)的樂舞表達(dá)形式對后世樂舞的發(fā)展起著重要的影響,5因而石窟造像、壁畫中飛天伎樂人物形象、服飾、和所持樂器與整體表現(xiàn)手法等方面,明顯可以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飛天樂舞藝術(shù)形象。此外,石窟造像、壁畫中還有異域人的場景,更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域文化的相互碰撞,用音樂和舞蹈的特殊表現(xiàn)形式展現(xiàn)了宗教在中國的流傳印記。這種西方藝術(shù)深深扎根與當(dāng)?shù)貍鹘y(tǒng)文化中,其文化創(chuàng)造成為具有民族獨(dú)色風(fēng)格的飛天藝術(shù),在傳播中不斷地吸收各地的優(yōu)秀文化,在流傳至長安時(shí)以達(dá)到藝術(shù)的最高峰,明顯具有“中國傳統(tǒng)特征”,不僅具有較為明顯的印度文化特色,更具有濃厚的中原風(fēng)格,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產(chǎn)物。
三、文殊山石窟與敦煌石窟飛天樂舞形象藝術(shù)特征的比較研究
1.文殊山石窟與敦煌石窟飛天樂舞形象藝術(shù)特征的共同性
佛教?hào)|傳主要依靠南北兩條線路,又加北方統(tǒng)治者大都崇信佛教,因此甘肅河西走廊地區(qū)石窟寺大興,而文殊山與敦煌的石窟壁畫中,以飛天樂舞形式展現(xiàn)給世人,尤為引人注意。文殊山、敦煌石窟中的壁畫多以反應(yīng)人們的真實(shí)日常生活為主線,畫家用獨(dú)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與繪制技巧向人們傳達(dá)了藝術(shù)與生活相結(jié)合的繪畫風(fēng)格。在這些石窟壁畫中有多數(shù)屬于深刻反映勞動(dòng)人民生活場景的畫卷,展現(xiàn)出了古代先輩們耕作、紡織、舞蹈音樂等日常場景。壁畫中沒有對當(dāng)時(shí)人們的服飾形象以及配飾做藝術(shù)處理,而是大量保留了各族人民的服飾和配飾,是對古人生活的真實(shí)寫照。
2.文殊山石窟與敦煌石窟飛天樂舞形象藝術(shù)特征的差異性
文殊山石窟與敦煌石窟中的壁畫圖案多姿多彩,是我國石窟壁畫藝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文殊山石窟開鑿于文殊山前山和后山的崖壁上,現(xiàn)存有前山千佛洞與萬佛洞,后山千佛洞與古佛洞,窟內(nèi)壁畫重修于西夏時(shí)期,大多已模糊不清,其中流傳最多的壁畫當(dāng)屬千佛畫與飛天樂舞圖像。在后山古佛洞的頂部,大多都繪有飛天伎樂圖,大都是以左右三人組成的樂隊(duì)為主圖,畫中的人物表情神采奕奕、悠閑自得、落落大方。以后山千佛洞為例,壁門繪有一幅《水月觀音圖》:觀音菩薩側(cè)身半跏坐于山巖之上,其面前下方的水面升起一云頭,云內(nèi)繪兩身人物,前身為天男,后身為天女,均佛教裝束。類似這樣兩身的壁畫人物形象,敦煌莫高窟第九十五窟元代的《水月觀音圖》中也可以見到。此外,從壁畫中的人物動(dòng)作上可以看出,不同的樂師使用不同的樂器,在幾種不同樂器的共同演奏下形成一種節(jié)奏感鮮明的音樂氛圍,從畫中觀眾的眼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鏗鏘有力的音樂節(jié)奏流入到每位觀眾的心中,引起人們的心理共鳴,壁畫的中央是一位舞姿曼妙的舞伎,她的動(dòng)作輕柔、嫵媚,與音樂有機(jī)結(jié)合在一起,婀娜多姿的肢體動(dòng)作向觀眾們傳達(dá)著舞蹈所帶來的魅力。
飛天樂舞形象是敦煌石窟中最具代表的人物壁畫形象之一,它的流入與東方繪畫技術(shù)緊密結(jié)合,將“飛天”這一形象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獲得了唐人“天衣飛揚(yáng),滿壁風(fēng)動(dòng)”的極大贊譽(yù),一度成為敦煌石窟的象征6。敦煌石窟中有彩色造像近2000座,塑像各個(gè)神采奕揚(yáng)、栩栩如生,仿佛多年前的盛大景象就展現(xiàn)在眼前,這些極富藝術(shù)色彩的頂峰之作不僅反應(yīng)出了我國古代人民的智慧所在,更深刻地反應(yīng)了宗教與當(dāng)?shù)氐娘L(fēng)土人情,古人非凡的技藝成就了如今敦煌石窟的輝煌。該石窟建筑是我國歷史上集古建筑、雕塑、壁畫為一體的藝術(shù)瑰寶,石窟尤其以多姿的彩色壁畫著稱于世,壁畫的畫容量與技藝高超豐富,是當(dāng)今世界其他地方宗教建筑所不能為之媲美的,壁畫中最多的則是尊像壁畫,這也充分體現(xiàn)出了當(dāng)時(shí)人們對于神、佛等形象的崇拜與敬意,此類壁畫向世人展示了佛教美好的天上人間的景象,極大宣揚(yáng)人們眼中的極樂世界,壁畫與佛教傳說故事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刻畫的栩栩如生,生動(dòng)形象地向人們展示了佛教文化的力量7。
迄今為止,學(xué)術(shù)界對于石窟壁畫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從宏觀角度出發(fā),對壁畫進(jìn)行整體研究后進(jìn)行科學(xué)的分類,進(jìn)行系統(tǒng)整理與分析研究;二是從微觀事物角度出發(fā),深究壁畫的具體時(shí)期、具體種類風(fēng)格,或?qū)Ρ诋嬤M(jìn)行比較研究,從比較中得出其事物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和演變過程;三是從文化鑒賞的角度來探討兩者壁畫藝術(shù)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中的藝術(shù)價(jià)值。以上研究方法重視對壁畫歷史淵源、發(fā)展、流傳的專業(yè)研究,學(xué)者往往采用考古學(xué)、分類學(xué)、管理學(xué)等方法系統(tǒng)科學(xué)地對壁畫的演變歷史進(jìn)行揭露,充分揭示了壁畫的發(fā)展史。這些重要文物研究對壁畫圖案的史學(xué)研究、闡發(fā)其藝術(shù)特點(diǎn)具有十分重要意義。此外,目前國內(nèi)對壁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學(xué)、考古學(xué)或藝術(shù)美術(shù)史上,隨著時(shí)代的不斷推移,一代又一代的學(xué)者前赴后繼,在研究石窟壁畫上取得了豐碩成果,有少數(shù)研究結(jié)果借助當(dāng)代藝術(shù)心理中的研究方法與實(shí)驗(yàn)成果對壁畫圖案中的動(dòng)靜規(guī)律、人物形象進(jìn)行深度研究,充分向世界展示了壁畫的藝術(shù)魅力。在專業(yè)學(xué)者眼中,飛天樂舞壁畫中動(dòng)靜結(jié)合的綜合表現(xiàn)手法與美學(xué)表達(dá)意義在兩者石窟壁畫中隨處可見,對于人們深度研究石窟圖案的歷史與藝術(shù)鑒賞起著重要作用。
四、結(jié)語
敦煌樂舞藝術(shù)是一種承載人類美好愿望與情感的抽象性符號(hào),它是對人類命運(yùn)與生活的美好向往,石窟造像、壁畫用藝術(shù)的表達(dá)手法向人們傳遞生命的活力。文殊山石窟中的飛天伎樂圖像采用粗獷的線條進(jìn)行勾勒,以西域的繪制手法向人們傳達(dá)了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特殊風(fēng)格。飛天樂舞人物形象是敦煌石窟文化藝術(shù)的標(biāo)志性建筑,是我國古代民族藝術(shù)的瑰寶。“飛天”這一形象源自與印度佛教藝術(shù),隨著佛教的不斷傳播,它被賦予了新的文化藝術(shù)內(nèi)涵。它與嚴(yán)肅的佛教形象形成鮮明對比,將動(dòng)與靜進(jìn)行有機(jī)結(jié)合,使得石窟中原有的嚴(yán)肅、呆板景象與格局得以緩解,在視覺傳達(dá)上得到有效調(diào)和,使石窟中的壁畫更加富有生氣與活力8。
本文通過對文殊山石窟與敦煌石窟飛天樂舞形象的比較研究,將兩種風(fēng)格迥然不同的造像、壁畫進(jìn)行對比研究,從線條勾勒與色彩搭配的角度研究不同風(fēng)格壁畫帶給人們的視覺沖擊,深刻探討了“敦煌樂舞”與“飛天伎樂”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和作用,真實(shí)反映出了人類對靈魂的寄托,傾注了人們對理想的追求與審美的認(rèn)知。通過對兩個(gè)石窟壁畫中飛天伎樂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中國古老的傳統(tǒng)文化,更能充分彰顯出佛教文化與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魅力。“敦煌樂舞”與“飛天伎樂”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孕育出了我國古代的音樂、舞蹈、繪畫、書法、佛教藝術(shù)等,其偉大超凡的藝術(shù)與文化創(chuàng)造力對未來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有著深遠(yuǎn)影響。
注釋:
1.張曉鈺.淺析莫高窟61窟《五臺(tái)山圖》與五臺(tái)山巖山寺文殊殿壁畫研究[J].大眾文藝,2019,(20):70-71.
2.趙慧,許棟.鎮(zhèn)國與消災(zāi):曹氏歸義軍時(shí)期敦煌地區(qū)的五臺(tái)山文殊信仰研究[J].五臺(tái)山研究,2016,(4):26-32.
3.張小剛,郭俊葉.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觀音圖》與《摩利支天圖》考釋[J].敦煌研究,2016,(2):8-15.
4.趙曉星.莫高窟第361窟的文殊顯現(xiàn)與五臺(tái)山圖——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二[J].五臺(tái)山研究,2010,(4):36-47.
5.王艷云.河西石窟西夏壁畫中的彌勒經(jīng)變[J].寧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3,25(4):16-21.
6.張海娟,楊富學(xué).蒙古豳王家族與河西西域佛教[J].敦煌學(xué)輯刊,2011,(4):84-97.
7.王百歲.甘肅省西和縣法鏡寺石窟調(diào)查與研究[J].敦煌學(xué)輯刊,2017,3(3):154-167.
8.王艷云.河西石窟西夏壁畫中的界畫[J].寧夏社會(huì)科學(xué),2007,(1):11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