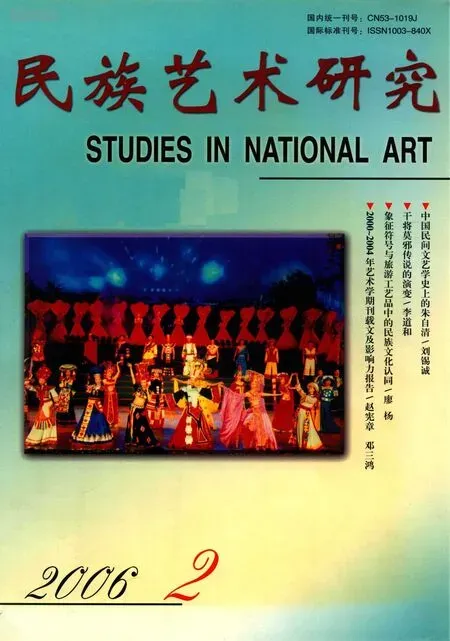形式演變視野中的文藝高峰
劉涵之
藝術形式是藝術品的符號呈現方式,任何藝術品首先都是通過形式觸動人們的感官,令其“興起”,從而引發人們借助它去探討藝術的奇妙世界。“藝術作品要存在,必須是有形的。”①[法]福西永:《形式的生命》,陳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頁。我們無法想象離開形式表達的藝術終究會怎樣。事實上,藝術的主題、內容只有轉化為形式,成為具體可感的藝術樣式,人們對藝術的領悟與接受才有可能。一幅畫作之所以為一幅畫作,一尊雕塑之所以為一尊雕塑,一首詩歌之所以為一首詩歌,它們的價值何在?人們在開展藝術活動時首先便面臨著對藝術品與非藝術品的區分,對藝術品的具體種類、樣式的區分,對精妙的藝術與粗俗的藝術的區分。而做出這一甄別、判斷的基礎乃在于形式標準,正是通過形式的確認,人們不僅表現出對藝術的認知能力,而且表現出對藝術的欣賞和理解能力,從而利于藝術活動的常態開展。
作為文藝發展史的特殊現象的文藝高峰顯然也存在著這樣的形式標準。中外文藝發展史上若干時段的文藝高峰無不證明形式標準和尺度的辯證關系。即是說,文藝高峰的標準和尺度需要恢復到歷史總體性和具體性的關系面得到理解。沒有形式的不斷變化和創新,便沒有藝術發展,更沒有文藝高峰的筑就。比如,在中國文學史上,韻文文體形式的發展就先后呈現過楚騷、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元曲的格局,造成了一代有一代的文學、一代有一代的文體形式盛出的景觀,又比如藝術形式的革新還通過由俗到雅的文體轉換這一環節為文藝發展輸入新鮮的血液:《詩經》“國風”采自民間,后在漢代被尊為儒家經典,格調逐漸雅致化;南朝民歌被引進梁陳宮廷,促成宮體詩的產生;詞在唐代本是民間通俗曲子詞,宋代文人加以改進從而登上大雅之堂;戲曲本起源于市井勾欄,有元一代蔚為大觀,至明清形成高峰……
一、形式變遷與文藝高峰
在論述“美的定義”的歷史淵源和具有標志性的文藝現象時,美學家鮑桑葵指出:“在古代人中間,美的基本理論是和節奏、對稱、各部分的和諧等觀念分不開的,一句話,是和多樣性的統一這一總公式分不開的。至于近代人,我們覺得他們比較注重意蘊、表現力和生命力的表露。一般來說,這就是說,他們比較注重特征(the characteristic)。”①[美]鮑桑葵:《美學史》,張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9頁。自藝術的誕生期開始,藝術品的實用目的決定了藝術的存在價值,形式因素顯然不完全構成藝術品和非藝術品的區分標準,但隨著人們審美意識的深化、對藝術創作認識的加深,基于對理性力量確證的形式之美常常成為藝術創作和美學理論的關切點,這從古代希臘人建筑、雕塑、悲劇等文藝杰作崇尚比例、和諧、秩序感、規律性和寧靜之美可以看出,同時從畢達哥拉斯學派的 “宇宙諧音”說、蘇格拉底的“合式”說、柏拉圖的 “理式”說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質料”說可以看出。至古羅馬時期,有關建筑物外貌布置、比例等形式的思考已經非常成熟,如神廟、劇場一類經典性公共建筑柱廊的設計等等,如當時羅馬宮廷的御用建筑師和工程師維特魯威所著的《建筑十書》就因從形式方面立論并總結建筑藝術成就而成為該領域的經典之作。在中世紀,神學美學也宣稱美的要素取決于完整、和諧,取決于光和色彩的鮮明等等,其時占主流的哥特式建筑對比例和幾何結構的突出,宗教題材繪畫對整體之美和因靜觀而致生的超感官的美的突出就是明證。文藝復興繁盛期意大利著名畫家達·芬奇將人體解剖學和透視學用于繪畫,更注重藝術創作物體空間布局、運動、形態和內部構造關系等方面,更注重知覺對形式的把握和形式在知覺中的反映,他在討論詩畫之別時就指出繪畫的美妙在于和諧、整體地“模仿”自然:“繪畫替最高貴的感官——眼睛服務。從繪畫中產生了協調的比例,猶如各個聲部都齊唱,可以產生和諧的比例,使聽覺大為愉快,使聽眾如醉如癡;但繪畫中天使般臉龐的協調之美,效果卻更為巨大,因為這樣的勻稱產生了一種和諧,同時射進眼簾,如同音樂入耳一般迅速。”②[意]列奧納多·達·芬奇:《芬奇論繪畫》,戴勉編譯,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4頁。17世紀在荷蘭興起了以倫勃朗為代表的風景畫畫派,這個畫派將普通人的生活置入畫面,農民、牲口、工場、客店、街道無不成為繪畫的表現對象,逼真地還原出荷蘭的社會風俗和精神風貌,而其藝術形式則在挖掘和諧之美,以至于著名的藝術哲學家丹納如此評論道,“這些作品中透露出一片寧靜安樂的和諧,令人心曠神怡;藝術家像他的人物一樣精神平衡;你覺得他的圖畫中的生活非常舒服,自在。”③[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33頁。18世紀的英國著名畫家荷加斯在其享有盛譽的《美的分析》一書中則論證了藝術形式的六大原則:適應、多樣、統一、單純、復雜、尺寸。荷加斯認為這幾大原則“都參與美的創造,互相補充,有時互相制約。”荷加斯以繪畫領域的線條、色彩、構圖、面部、姿態、動作等方面的處理為例詳細分析了美術創作形式因素的本質和各種不同組合方式,在他看來形式因素的組合與藝術品的總體意圖相適應。如果不合意圖不合目的,也就失去了美;反之,如果沒有美的形式的呈現也就談不上藝術品的總體意圖。整體而言,荷加斯結合自身創作經驗總結藝術形式創作原則并沒有超出“多樣性的統一”這一核心觀念,用荷加斯自己的話來說,他感興趣在于“究竟是什么促使我們認為某些東西的形式是美的,另一些形式是丑的,某些東西的形式是有吸引力的,另一些東西的形式是沒有吸引力的。”④[美]威廉·荷加斯:《美的分析》,楊成寅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頁。不僅在美術領域,古典時期的表演藝術領域也有對藝術形式“多樣性的統一”的思考和實踐,法國宮廷戲劇家、理論家布瓦洛和戲劇大師高乃依、莫里哀就是代表。對于布瓦洛來說,詩歌的創作需要借鑒古代希臘人的法則,既要合理又要合適,“處處能把善和真與趣味融成一片”⑤[法]布瓦洛:《詩的藝術》(增補本),范希衡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頁。,從而實現美、真和藝術快感的三者同一。對于高乃依、莫里哀來說,戲劇創作合乎“三一律”規則是不二選擇,時間的一致、地點的一致和情節的一致能保證戲劇在形式上緊湊嚴密、完整統一和平穩妥當。據說1624—1642年間曾任法國首相的黎塞留還親自操刀悲劇 《米拉姆》的寫作和演出。《米拉姆》一劇僅用一堂布景,五幕戲分別選擇不同的燈光來標明時間,第一幕戲發生在日落時分,第二幕為月夜時分,第三幕是太陽初升之時,第四幕則在正午,第五幕則為傍晚, “在一晝夜里發生在一個地方的一件事,規整的內容產生了規整的布景”,①余秋雨:《世界戲劇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頁。完全吻合亞里士多德《詩學》對悲劇時間、地點、情節一致性的規定。西方藝術發展史表明,無論在“古代人中間”美的定義內涵體現對“多樣性的統一”原則的傾斜,還是中世紀到新古典主義藝術體現出對這一原則的偏至,因而“比較注重特征” “多樣性的統一”這一形式美學觀念實際扎根于藝術實踐中和文藝杰作的創作,重和諧、重秩序感的審美意識貫穿了自古典時期至18世紀的藝術創作、藝術理論發展過程,帶有很強的理性色彩。
與西方重和諧、重秩序感的形式美學類似,中國藝術形式美學的智慧主要集中在對“文”的作用、功能的突出上。文與紋相通,意指文身,源于對身體的修飾,它帶有很強的原始宗教色彩,后又用于戰爭圖騰、宴會以及成年禮儀中。文的主要特點在兩個方面。一為修飾性。飾,單一不行,錯彩成畫,寓成于和。二為規定性。規定性意味飾最終服務于禮制的規定性,結果倫理承擔為其本義。②此處借鑒張法《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一書第七章“文與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審美對象結構理論”的觀點。 (見張法《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4頁。)孔子在《論語》“雍也”篇里將古代關于文的思想表述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就人的學“文”而言,孔子把禮樂修養視為文的主要內容,質則當作人的固有品質,孔子因之強調君子之學對兩者關系的制衡;就藝術創作而言,孔子提出的“文質彬彬”標準大體反映了政教禮樂之文(包括制詩、制樂之類的藝術創作)需要考慮到形式因素的本來面目,是對文的創作經驗教訓的總結。孔子還以文為標準來肯定堯舜和西周,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稱西周“郁郁乎文哉”。③于民主編:《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頁。從先秦對包括禮樂之制的文的實踐來看,如 《左傳》記載的季札觀樂、臧僖伯諫觀魚等典型事例,無不注重文藝風格的表現形式和文物昭德的倫理功能,所以章太炎在《國故論衡》總結孔子的這一做法時,會認為“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蓋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謂之文;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文章者,禮樂之殊稱矣。”④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頁。在孔子的啟發和影響下,中國藝術對文的考究和對文所蘊含的質的考究便成為中國形式美學的主要特色,文、質關系的平衡可謂一以貫之,其中尤以作為中國文學最高成就的韻文、格律詩為甚。劉勰的《文心雕龍·情采》提出過“文附質”“質待文”的觀點,并以此為標準檢討歷代詩文創作實績。李白則在《古風五十九其一》中高呼: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的藝術理想,并身體力行。朱熹從他的理學視角出發,認為道和文有著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申明“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李漁基于自己的戲劇創作經驗,以為戲劇傳奇有三美: “曰情,曰文,曰有裨風教。情事不奇不傳。文詞不警拔不傳。情文俱備不軌乎正道……亦終不傳……三美俱擅,詞家之能事畢矣。”而思想家王夫之在《尚書引義》中則通過文與質之間關系的辯證,文與象之間關系的比照,將這一形式美學闡發得更為系統,帶有總結的意義:
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質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則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無有無象。視之則形也,察之則象也,所以質以視章,而文由察著。
……
辭之善者,集文以成質。辭之失也,吝于質而萎于文。集文以成質,則天下以達質,而禮、樂、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質不昭,則天下莫勸于其文,而禮、樂、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敗鼓,而莫為之興。蓋離于質者非文,而離于文者無質也。惟質則體有可循,惟文則體有可著。惟質則要足以持,惟文則要足以該。故文質彬彬,而體要立矣。①于民主編:《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217、302、426—427、459—460頁。
在中國藝術史上,“文質彬彬”作為藝術的形式標準一提出便得到連續持久的貫徹,這和儒家主張情感內斂、含蓄的中庸美學取得了一致,決定了藝術史中和之美形式表達的總體風貌和形式、意蘊并重的藝術主潮,當然也決定了中國文藝高峰的“儒雅風流”的整體姿態和標準。朱自清在《文學的標準和尺度》一文認為:“我們說‘標準’,有兩個意思。一是不自覺的,一是自覺的。不自覺的是我們接受的傳統的種種標準……自覺的是我們修正了的傳統的種種標準。”并且稱“不自覺的種種標準為‘標準’” “種種自覺的標準為‘尺度’。”朱自清考察中國文學史的傳統,得出結論:即便整體上, “儒雅風流”是標準,但這個標準在不同時代因為文學發展有著許多變化就有了新的尺度,因為尺度伸縮的長短不同、疏密不同,因而不同時代的文學呈現出各自的特色。文藝發展史表明,文藝史一方面內蘊某種一致性的審美特質,一方面這樣的特質又具體化為分殊的審美崇尚。如果說前者意味著有關民族性的某些總體性的文藝實踐,那么后者則說明文藝實踐是貫徹到具體的、差異明顯的包括時代精神、藝術創作、藝術表達在內的文藝現象之中的——從歷史主義的角度去看,這便是連續性和相對性的統一,中國文藝高峰的形式離不開“文質彬彬”的標準,但也因為具體實踐的差異而賦予“文質彬彬”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形式意蘊: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藝)”,其實也可以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藝)形式。
二、文藝高峰的形式理論舉隅
近現代藝術形式相對古典時期來說獲得了更大的發展,與其說古典時期藝術創作集中“多樣性的統一”之于藝術形式表達的重要性,促進了藝術形式或模仿或反映世界自身的和諧性,不如說近現代藝術標舉對這一和諧性的反動,進而引發藝術創作更注重提升形式的內蘊,從而解放了形式,說這個時期藝術形式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也不為過。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以他獨有的方式清晰地勾勒出形式之于審美判斷的意義:“在繪畫中,雕刻中,乃至在一切造型藝術中,在建筑藝術、園林藝術中,就它們作為美的藝術而言,素描都是根本性的東西,在素描中,并不是那通過感覺而使人快樂的東西,而只是通過其形式而使人喜歡的東西,才構成了鑒賞的一切素質的基礎。使輪廓生輝的顏色是屬于魅力的;它們雖然能夠使對象本身對于感覺生動起來,但卻不能使之值得觀賞和美;毋寧說,它們大部分是完全受到美的形式所要求的東西的限制的,并且甚至在魅力被容許的地方,它們也只有通過美的形式才變得高貴起來。”②[德]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頁。在康德看來,人們對美的事物的欣賞取決于其形式,在繪畫領域主要集中于線條、輪廓等抽象外形。康德的形式主義美學突出審美判斷的客觀性,突出這種客觀性的普遍適應性,突出審美判斷通過訴諸理性而不是直接經由感性給出,因而他會將“魅力” “感覺”和美對立起來,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肯定經過理性過濾的形式表達與美的表達。康德形式主義美學給予德國、英國浪漫主義文藝極大的影響,浪漫主義運動時期的文藝巨子紛紛重視想象力、重視文藝形式的新奇性和異國情調的表達都與康德美學注重形式有關。
19世紀中后期,藝術對新標準的尋找又促發了現代主義運動的產生。現代主義藝術對藝術形式、藝術手段所產生的藝術效果和獨立性的關注無與倫比。這里我們試結合抽象主義的開創人俄國著名畫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的繪畫及其理論加以描述。康定斯基將繪畫分為兩類,一類是重物質的藝術,另一類是重精神的藝術。前者通過視覺的刺激來影響欣賞者,它是外在的;后者則訴諸欣賞者的心靈共鳴,它是內在的。康定斯基又認為藝術家的創作源于藝術家的內在心靈,對于藝術家來說“所有的手法都是神圣的,假如它們是內在必需的話。所有的手段都是荒謬的,如果它們不是出自內在必需的話。”所謂“內在必需”是指藝術的表達手段充分尊重心靈法則,結果藝術形式只能以藝術精神的內在需要為依據:“最精確的比例、最精確的計算和砝碼都不會用頭腦計算和演繹衡測的方法得出正確的結果。這種比例不可能計算出來,也找不到那樣的衡秤。比例和砝碼不在畫家身外,而在他的心里。它們可以稱之為尺度的感情、藝術的節拍——這是畫家天賦的物質;激情可以使他們升華到天才發明的高度。”康定斯基的畫作極為注重點、線、面藝術元素在構圖中的作用,以為三者作為藝術的基本要素可以得到“純”科學式的把握,而這種把握動力在于“無目的的或超目的的知識渴望。”①[俄]康定斯基:《藝術中的精神》,李政文等編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123頁。康定斯基的畫作通常有色彩和構圖的并置,但幾何構圖在畫面中的地位更為突出,點、線、面的連綴使得畫面充滿動態,這一動態又頗能折射精神的自由,其作品《幾個圓形,323號》《黃·紅·藍》就是這方面的佳例。前者選擇以幾何圓點為構圖的支配力量,后者非規則幾何圖聚、散結合,突出的都是顏色對比中的點、線、面動態呈現,從而充分表現了畫家內心的靈動之感。
20世紀上半期,對藝術的形式從理論的高度做出全面總結的主要有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等文藝思潮流派。在被標舉為形式主義宣言書的《藝術作為手法》(1917)一文當中,形式主義者的代表人物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反對從形象思維、形象因素著手研究藝術時便順手指出了藝術研究的真正對象:
各種詩歌流的全部活動不過是積累和發現新的手法,以便安排和設計語言材料,而且安排形象遠遠超過創造形象。形象都是現成的東西,而且人們在詩歌里回憶起的形象,比用來進行思維的形象要多得多。
形象思維無論如何也不是聯系所有藝術科學的紐帶,甚至也不是聯系文學藝術各個學科的紐帶,形象的變化并不是詩歌發展的本質。
既然不承認形象是詩 (藝術)的本質,那么只有從詩歌 (藝術)創作的本質屬性“積累和發現新的手法”“安排和設計語言材料”著手了。為了清晰地闡明這一新手法并檢驗其效果,什克洛夫斯基將藝術對形象的“回憶”表述為 “為了恢復對生活的感覺,為了感覺到事物,為了使石頭成為石頭。”藝術創作類似于“為了使石頭成為石頭”,這表明“藝術的目的是提供作為視覺而不是作為識別的事物的感覺;藝術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變得模糊、增加感覺的困難和時間的手法,因為藝術中的感覺行為本身就是目的,應該延長;藝術是一種體驗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東西對藝術來說是無關重要的。”“奇特化”(亦翻譯為“陌生化”)造成的陌生、間離效果顯然目的在于“增加感覺的困難和時間”,延長審美感受,這顯示了形式主義從鑒賞心理的滿足方面考慮藝術審美屬性的獨特視野。什克羅夫斯基以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創作為例,認為其小說的“奇特化”手法主要表現在“他不直接呼事物的名稱,而是描繪事物,仿佛他第一次見到這種事物一樣;他對待每一事件都仿佛是第一次發生的事件。”②[俄]維·什克洛夫斯基:《藝術作為手法》,載[法]茨維坦·托多羅夫編:《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蔡鴻濱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6頁。在1921年寫就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結構》一文當中,他仍以托爾斯泰為例,指出“奇特化”手法“另有一種不同的表現手法,就是在一個圖景的細節上耽擱許久,并加以強調,這樣便產生常見的比例的變形。”③[俄]維·什克洛夫斯基:《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結構》,載[法]茨維坦·托多羅夫編:《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蔡鴻濱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頁。托爾斯泰小說的奇特化表現效果證實了“增加感覺的困難和時間”在形象塑造方面的創舉,它不但有助于展現小說細節刻畫的逼真性,而且有助于推動情節布局的創新,從而確證形式新變之于藝術效果的意義,而托爾斯泰作為俄國文學的高峰也能在這里得到理解。
三、文藝高峰的形式意蘊與文藝范例
英國著名藝術理論家克萊夫·貝爾曾說過:“欣賞藝術品,我們不需要帶有什么別的,只需要帶有形式感、色彩感和三度空間感的知識。”①[英]克萊夫·貝爾:《藝術》,周金環、馬鐘元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7頁。貝爾雖然著重探討人們對繪畫作品的欣賞條件,但他指出“形式感”之于藝術欣賞(當然也包括藝術創作)的基礎地位,的確是肯定了形式因素在藝術活動中的首要性。藝術形式總是指向藝術品本身,創作新的藝術便是創作新的藝術形式,反之亦然。形式因素的確立意味著藝術的確立,藝術形式原本就是藝術品的存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它對藝術起到規范、整飭的作用,藝術并非一個隨便是什么和隨便做什么的自由王國。換句話來說,無節制的形式和不完美的形式意味著藝術創作的非完美,因此,對形式的考究是藝術創作和藝術欣賞的關鍵環節。比如,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就以藝術形式的合目的性標準劃分藝術類型的等級序列為:詩的藝術→音的藝術→造型藝術;再比如,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在康德的基礎上以意志的客觀化為標準將藝術類型進一步等級化:建筑藝術→花園藝術→雕塑→繪畫→詩歌→悲劇。
就具體的藝術品來說,它內在的組合、部分和部分之間的關系、部分和整體之間的關系構成藝術的樣式,即藝術形式。藝術形式是藝術品的形式,離開形式也就沒有藝術特征可言、沒有感性整體可言,因而藝術的特征在于形式,形式是藝術品的存在方式,“由于形式使對象成形并賦予對象以一種存在,因而完全可以說形式既是意義又是本質。它是體現在外觀中的理念,并賦予外觀以某些永久性。”②[法]米·杜夫海納《審美經驗現象學》(上冊),韓樹站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頁。藝術品不同于一般自然物質在于它是藝術家創作的產物,藝術美不同于自然美在于它是通過藝術家的創作呈現出來的美,因而藝術品是人工之物,藝術美是人工之物的美。藝術家作用于自然物質也就是為一般物質賦予形式、賦予形式之美。藝術天才為藝術立法,往往是為藝術形式立法。藝術家的創作始于形式又終于形式,他必須圍繞著素材、對象運用有力的手段去突出某種形式、建構某種形式,以便讓欣賞者通過對形式的體驗來理解形式的功能。
形式永遠是活著的。托爾斯泰就把形式傳達看作情感體驗效果的標志,他這樣認為:“藝術起源于一個人為了把自己所體驗的情感傳達給別人,就重新喚起自己心中這份情感,并用某種外在的標志表達出來”。托爾斯泰以受狼驚嚇的男孩講述自己經歷為例來論述這種“外在的標志”的內在構成, “一個遇見狼而受過驚嚇的小男孩,在講述這件事情時,為了使別人也感受著他所體驗的情感,于是在描寫他自己遭遇到狼之前的情況、所處的環境、森林、自己的無憂無慮,隨后描述狼的樣子、狼的舉動以及他與狼之間的距離,等等。所有這一切——如果男孩子在講述時再次感受他所體驗過的情感,感染著聽眾,讓他們也體驗到講述者所體驗過的一切——這就是藝術。”③[俄]列夫·托爾斯泰:《藝術論》,張昕暢、劉巖、趙雪予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頁。顯然,小男孩講述自己遇狼經歷的故事感染效果取決于他所描述的故事的布局,在故事內核中,小男孩遇狼的即時狀況被安排進受狼驚嚇的環節,這涉及故事如何敘述、以何種方式及結構層次敘述等形式要素,小男孩不僅僅是在向他的聽眾講述自己遇狼的經歷,他需要考慮到自己如何喚起聽眾體驗到他所體驗過的一切,他的描述意圖決定他的故事的感染力度。
對于形式的講究,在一些執著于新方法、新手段的實踐的天才藝術家那里可能走得更遠,以至于不難想象:愈是藝術杰作愈是講究藝術形式的突破,愈是藝術形式取得偉大突破愈是藝術杰作。試以印象主義繪畫宗師凡·高的《夕陽和播種者》為例。就像凡·高許多具有標志性特征的風景畫一樣,“播種者”的畫面內容很簡單:已經翻耕的土地呈現藍褐色,一直蔓延到地平線;播種者邁開士兵式矯健的步伐,昂首前行,他的身后是一片火紅的麥地,上空一輪夕陽低懸天空,光芒耀眼。正如有的論者指出, “凡·高的畫,看很多細部,會發現顏色與筆觸糾纏成一片如火焰的顫動,這種形式,不再是客觀的形式思考,已經是凡·高內在主觀形式的再現了。”①蔣勛:《藝術概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00—101頁。在畫面的右上方,播種者邁開士兵式的雄闊步伐,從田野的這一端撒播開種子直到田野的盡頭,他有可能只是一個盡義務的勞動者,有可能是一個負債者,有可能是一個家庭的承擔者,他的當下狀況模糊不清,人們只能從他矯健的身姿去辨明他是一個熟練的體力勞動者。人們從翻耕的土地,從落山的太陽還可以體會到播種者緊張繁忙的一天即將結束,盡管這個勞動場面不很壯觀。而他身后的成片麥地約略構成這么一種景致:等待收割的麥子,翻耕的土地。這是一個播種到收獲的過程的濃縮,播種承繼著收獲,收獲承繼著播種。這個今日的播種者在昨日可能是一個收割者、一個翻耕土地的人,若干日過后,他又可能是一個翻耕土地的人,一個收割者、播種者。他所有的勞動就這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繼續,他可能為土地歉收傷神,可能為病床上的妻子擔憂,也可能為償付不了債務犯愁,但所有的這一切都不曾阻礙他勞動的步伐。他是一個勞動者,在開始勞動的時候就被選擇了勞動者的身份,仿佛親近土地是天賦予他的權利,他不會去尋思這種身份確立得合不合理,他也不會去反抗什么,更不會去計較重復勞動帶來的單調乏味。他僅僅為填飽肚皮而勞動,為治好妻子的病而勞動,為付清沉重的債務而勞動。他穩健的步伐表明他有信心解決好這一項項的困難,用勞動的雙手創造一個休養生息的家園。只要他的勞動有所收獲,他的汗水隨著撒播的種子飄落在干涸的土地上,希望的種子就一定能生根、發芽,長成茂盛的莊稼。他如果看到一線生機尚在,他的步伐就會加快,而歡暢的歌聲也就會從空曠的田野上空升騰。這種田園風光和勞作場面因為凡·高印象主義的濃墨重彩而層次分明,它雖不恬淡但很質樸,它靜幽卻充滿著剛健的力度,尤其是地平線上方太陽光芒的橘黃色與土地的藍褐色對照強烈、交相輝映,幾乎讓人產生眩暈的感覺,給欣賞者心理極大的刺激。而剛翻耕過的土地是新鮮的,日落西山意味著新的一天即將來臨,這兩者相互承接,在主題蘊涵和形式表達方面又融合為一。土地上的播種者就是這個主題和形式的闡釋者:他用自己的勞動和智慧氤氳了自然和人工的生長點。土地因孕育生命而偉大,他因點播生命而偉大。作為早期印象派的奠基者,凡·高的畫作,如《向日葵》 《鳶尾蘭》《夕陽下的柳樹》《星月夜》等,對顏色的強調和構型顯示了他一貫的美學趣味,凡·高的星空、大地、靜物無不著染上他個性化的風格, “在大地所擁有的各種各樣的美中,凡·高只選擇了一種:顏色。大自然那種總能使色彩對比得無懈可擊的特性,色彩所擁有的無窮無盡的中間色,以及土地那種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而又不論在什么季節,不論在什么緯度都同樣美麗的色彩,總是使凡·高驚喜不已。”②[俄]康·帕烏斯托夫基:《金玫瑰》,戴驄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頁。可以說,凡·高畫作給人造成的感染力正是取決于因顏色調配而生發的形式美,它讓畫家驚喜不已,也讓每一個觀賞者驚喜不已,正如貝爾推崇畫家塞尚,稱他為 “發現 ‘形式’這塊新大陸的哥倫布”,塞尚“創造了形式,因為只有這樣做他才能獲得他生存的目的——即對形式意味感的表現”,③[英]克萊夫·貝爾:《藝術》,周金環、馬鐘元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41、143頁。凡·高也是形式新大陸的發現者,他的畫作同樣是“對形式意味感的表現”。
當然,形式是相對藝術品的主題和內容而言的,說到藝術品的形式,很難不與內容相聯系。藝術品因為內容的意義呈現而富有價值,因為形式的表達而定型。當我們說藝術形式是就藝術品的形式而言的,它意在突出藝術形式的獨立性,而藝術品乃其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內容與形式辯證地內蘊于藝術品之中,故談論藝術形式又需回到兩者的關系方面。在藝術品中,內容的真實價值和意義對整體效果來說至關重要,它涉及形式表達的作用和目的,因而不存為形式而形式的藝術創作,同時,形式的美學效果最終助益于內容和主題的呈現,因而不存在為主題(思想)而主題(思想)的藝術創作。“在美學和藝術理論中,談到內容與形式問題,通常包括下列幾個層次的含義:其一就任何一部具體藝術作品而言,其內容與形式都具有與別的作品不同的個性;其二就一類作品而言,即通常所說的藝術的種類和體裁,是指某些藝術作品就其在反映的對象、表現方式和傳達手段等方面具有共同點,因而在這些藝術品之間不論內容與形式都存在著共性,而與其他類型相比,又具有特殊性;其三就一定歷史時期內的藝術作品而言,或者在一種藝術類型內部,或者在幾種藝術類型之間,存在著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風格的類似性或一致性。”①王朝聞主編:《美學概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200頁。有人將藝術形式與非藝術形式的區別認定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見的一致性”②[美]F.大衛·馬丁李·A.雅各布斯:《藝術導論》,包慧怡、黃少婷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頁。,其實亦可從“個性”的形成、類型的特殊性、風格的一致性三個方面來理解,藝術品形式的“可見的一致性”并非什么神秘之物,需要就其服務對象而言,而這個對象自然也能將藝術品和非藝術品區別開來。藝術形式“可見的一致性”說明,藝術形式服務于藝術品的整體效果,不可將形式和內容割裂開來談論。至于具體的藝術創作領域,如詩歌、音樂、繪畫、舞蹈、雕塑、建筑等等,因為素材、質料的差異可能形成不同藝術的內容和形式,但即使同樣的主題在不同的藝術種類中也存在不同的形式表達,比如,德國美學家萊辛在《拉奧孔》中指出的“拉奧孔”雕塑和維吉爾《埃涅阿斯紀》史詩對祭師拉奧孔的恐懼情形的不同刻畫方式;比如,我國唐代敦煌“變文”和“俗講”在處理佛經故事上的形式差別,它們的藝術史地位與其說來自神話傳說、佛經教義,不如說來自形式的獨創性和藝術表達的變革。藝術形式通過致力于整體效果的實現而獲得相對的獨立性,這樣相對獨立于主題和內容的形式要素獲得自身的審美特質,藝術成就愈偉大審美特質因此愈突出。這是我們選擇從形式演變及其歷程的角度探討文藝高峰現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