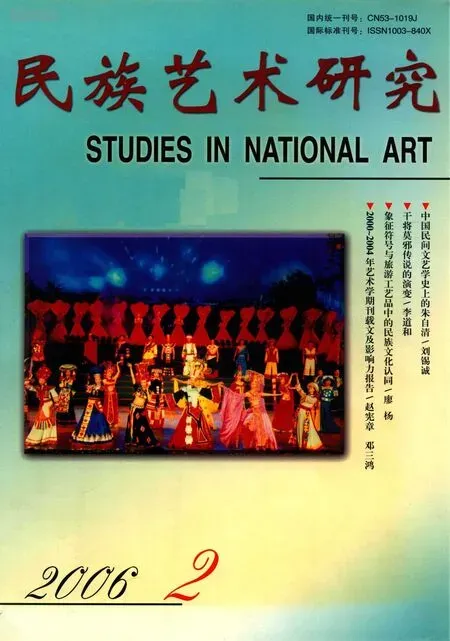文藝高峰評價標準及其三重張力
吳 鍵
作為整體的 “文藝高峰”現象涉及藝術品、藝術家 (創作者)、藝術公眾 (接受者)與前三者身處的社會與歷史境遇(世界),通過四個藝術要素之間的復雜互動,生成了決定文藝高峰形態的客觀關系網,也即王一川先生提出的 “藝術高峰場”。①王一川:《論藝術高峰場》,《民族藝術研究》2019年第2期,第5—15頁。無論是從反映論、發生論、創作論、鑒賞論抑或規范論的視角,都可以從中解讀出豐富的意涵與啟示。而從規范論視角的展開,也即確立文藝高峰的評價標準,以此選取文藝高峰的典型案例,正是其中起著基礎性作用的核心路徑之一。本文由此展開分析,通過對 “文藝高峰”概念的細讀,抽繹出評價標準中所蘊含的三重張力,并以問卷調查為案例,探討當代中國藝術公眾是如何在這一張力結構當中,對文藝經典加以接受與認知的。
一、哪種“文藝”,何以“高峰”:概念細讀與準則抽繹
對于“文藝發展史與文藝高峰”這一研究對象,其中關鍵詞匯的指涉范圍十分宏大,正需要進一步厘清其范圍、邊界和邏輯,從概念細讀之中抽繹其題中之義。比如說中文語境中“文藝”的現代語義有著怎樣的生成脈絡與概念層次?古往今來的歷史長河中,文藝究竟擁有哪些質素才稱得上“高峰”?同時這些“文藝高峰”又是如何排布,從而形成文藝發展史的脈絡?這些問題正有待我們一一叩問。
首先只有清晰界定“高峰”所屹立的文藝版圖范圍,才能更為清晰地探明聳立于這一版圖之上的諸文藝狀況,因此要對“文藝”語詞所包含的內在層次加以辨析。而這一今日常言常談的“文藝”語詞,實際上是在中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對于西方現代“藝術”觀念加以吸收,所形成的頗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近代造詞。在近代西方“美的藝術” (fine arts)傳入中國之后,逐漸形成了兩套總名來加以指稱,一是貼合西方原意的“藝術”,二是中西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的“文藝”,兩者都可以對各藝術門類加以指稱,但同時兩者也有著重要的不同。①張法:《中國現代學術語匯的困局——以藝術學為例》,《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3期,第61—65頁。依照含義上由廣至狹,現代意義上的“文藝”概念,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文藝”作為“文化藝術”而言,也即在思想文化典范意義上的諸藝術成就,這是“文藝”最為寬泛的范圍意涵。這一近代以來所形成的“文藝”概念,包含了文字文章、文采文藻、禮儀文明等多個層面上的含義,指向傳統的“文教”整體,而非僅指現代審美體制中的“文學” (literature)。第二,“文藝”作為“文學”與“藝術”的合稱,中國藝術體系 “以文為主”,也使得“文”在各門類“藝術”之外被單拎出來與“藝”并置。第三, “文藝”作為 “文學藝術”而言,這是“文藝”最為狹窄的意涵。這一語義層次強調“文學”作為門類藝術之一,強調其審美質素與藝術特性。
在歷史中積淀而成的上述三個層次“文藝”概念,一方面在指稱范圍的廣度上不斷集中,同時也對審美質素的強調不斷加深。但在實際指稱中并非涇渭分明、截然分開,在確認其藝術審美性的同時,更在傳統“文”(文字文章、文采文藻、禮儀文明)的總體概念上加以觀照。習近平總書記在論及“文藝”問題時,正是在此大處著眼,強調 “文藝”與文化傳統的密切聯系。例如,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就引述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的論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并在引述各民族文化軸心時代的文藝高峰時,列舉“老子、孔子、莊子、孟子”一脈而來的中國 “文藝源流”,也列舉了“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形成了 《梨俱吠陀》《阿達婆吠陀》《娑摩吠陀》 《夜柔吠陀》四種本集”等,這些著作都有溢出現代 “文學”與“藝術”范疇的地方,是塑造了民族文化與文明的重要經典之源。②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頁。從文化發展的整體之中來把握文藝態勢,強調文藝的社會責任和倫理屬性,通過如上對于“文藝”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到這里的相關論述是與傳統文化的理路一脈相承而來的。
其次是“文藝高峰”中的“高峰”應該如何界定,“文藝”符合怎樣的標準才能稱為“高峰”?對于這一問題,無疑需要更為詳細深入地研究才能得出較為圓滿的答案,在此只能初步地加以申說。文藝 “高峰”之為“高峰”,而非 “洼地” “平原”或是 “高原”,正在于文藝作品的經典質素高大深廣、木秀于林,如壁立千仞,似高山仰止。同時文藝“高峰”之為 “高峰”,而非 “秀峰”“奇峰”或是“險峰”,還在于文藝作品擁有充分的體量、涵納足夠的人性深度與歷史廣度,恰如“高峰”不僅在高度上卓出儕輩,但也必須擁有足夠的體量、堅實的基礎。如在《西方正典》之中,美國文學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指出的,莎士比亞作為西方現代文藝群峰之中的“主峰”,其歷史地位的確立不僅在于其文藝作品的造詣深湛,也在于其作品的充實體量,這為文藝史發展貢獻出一系列鮮明突出而又吟味不盡的藝術形象,如其所言:“莎士比亞終以一系列大作超過了他的前輩和競爭者:《仲夏夜之夢》《威尼斯商人》和兩部《亨利四世》。鮑通、夏洛克和福斯塔夫等在《約翰王》中的福爾孔布里奇和《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墨柯修之外增加了新型舞臺形象。這些已略微超出了馬洛的才情和興趣……在莎士比亞創作福斯塔夫之后過了十三四年,我們又看到了他寫出的一系列杰出戲劇形象:羅瑟琳、哈姆萊特、奧賽羅、伊阿古、李爾、愛德蒙、麥克白、克莉奧佩特拉、安東尼、科里奧蘭、泰門、伊莫根、普洛斯佩羅、卡力班及許多人物。”①[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
最后我們還必須叩問 “文藝”與 “高峰”所棲身其中的“歷史”整體。 “文藝”是在怎樣的歷史結構之中獲得其意義?文藝的諸“高峰”又依照怎樣的邏輯脈絡排布?如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序》中所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每個時代往往都有匯聚其“時代精神”的“文藝高峰”,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諸文藝高峰之間依循著某種固定的發展線索,如王國維就視之為文體之間衰退更生、周而復始的線索脈絡:“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②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三卷》,謝維揚、房鑫亮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但文藝發展史,必然有其主體、起源與目的,并非對文藝高峰的簡單羅列,而是需要堅定地從當代視點之中回望傳統與歷史,使得“歷史”在當代中國這一主體的回望之中得以成立,將文藝高峰排布在發展的脈絡之中,并延伸至當下,才能為當代文藝創作由“高原”走向“高峰”提供有益的歷史鏡鑒。
二、由頡頏對立向深化統一:文藝高峰評價標準的張力結構
通過上文對 “文藝高峰”概念的細讀,其規范標準的確立至少存在著如下三重張力,分別是文藝性質上的社會性與審美性、歷史向度中的永恒性與時代性、空間向度中的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張力。每一重張力結構都包含彼此之間頡頏沖突的兩極,文藝高峰或者說經典之作,其成功的一大標志,正在以獨特的方式成功地保持這一張力結構的同時,又能在更高的層面上使之升華為一。
首先是文藝性質上的審美性與社會性(或倫理性)的張力結構。在上述對“文藝”意涵的考察之中所言,中國“以文為主”的藝術體系,如曹丕《典論》:“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③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頁。以及影響深遠的“文以載道”論,都強調“文”的社會介入與倫理教化功能,這也影響到現當代文學態勢。在作為中國現代啟蒙運動的 “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是其中的關鍵一環,這也使得在現代中國,邏輯上應該屬于“藝術”門類之一的“文學”被單提出來,冠于藝術之前,成為獨具特色的中國藝術體系的總稱。這一語詞在現代語境中的生成,實際上是將“審美自律性”為基礎的現代“藝術”架構,安置在中國傳統文教體系的基礎之上。但這兩者之間并非能夠全然統一,在其內部就具有審美性與倫理性的張力存在,而具有文藝高峰地位的經典之作的重要性,正體現以宏富的意涵溝通了這種張力的兩極。如政治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強調經典之作的倫理意涵時說道:“那些書包含著許多對人的自然最深刻的反思,與它們的接觸是富于啟發的知識和道德經歷,它們對那些被帶進來的人有巨大的解放作用。”④[美]A·布魯姆:《巨人與侏儒:布魯姆文集》,秦露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頁。而哈羅德·布魯姆則在著名的 《西方正典》一書中,指出文藝經典的這種力量正來源于審美的力量,“只有審美力量才能透入經典,而這力量又主要是一種混合力: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及豐富的詞匯。”⑤[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在其看來,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少數必讀和牢記之書,乃是因為它們是達到審美巔峰的佼佼者。經典的力量和權威是美學的力量和權威。
其次是作為文藝高峰的經典之作,在時間向度中的時代性、與超越歷史的永恒性之間的張力。“經典”之為“經典”,正在于其閃耀著穿透歷史塵埃的永恒光芒,如何在歷史關系之中理解文藝高峰的這一永恒性?文藝高峰超越歷史的普遍價值又是如何在歷史之中生成的?正如馬克思所感到困惑的:“困難不在于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頁。對于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對經典的“永恒性”做一番去神秘化的理解。首先,這一“永恒性”深刻地寓于其“時代性”之中,在其所凝聚著的深而廣的“時代精神” (Zeitgeist)之中,正是在于每一時代最為深刻的血肉聯系之中,才能鑄就一時代的文藝高峰。其次,經典之作的“永恒性”在歷史當中的生成,還有賴于一種“發展眼光”,將文藝高峰放在歷史脈絡之中加以勾連,同時又有賴于明晰的“當代視點”來加以透視。正是從當下中國這一主體的視角出發,過去的文藝高峰山巒相接、逶迤而來,為鑄就當代的文藝高峰提供借鑒。正是在每一時代的“時代性”之中,文藝高峰得以拔地而起、峰岳聳峙,過去造峰運動中生成的文藝高峰同時又在“當代性”的回望之中,為當下貢獻出自己的價值與意義。作為文藝高峰的經典之作,由此溝通了歷史與當下的聯系,使得傳統映現于當代,又使得當下的不斷生成為新的傳統、新的 “高峰”。
最后是作為文藝高峰的經典之作,在空間向度中的民族性、與超越民族的世界性之間的張力。雖然作為文藝高峰的典范之作,其產生必然有其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產生于一時一地,但卻有超越一時一地的普遍性。如哈羅德·布魯姆推崇莎士比亞戲劇的經典特質時所言,“作為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一位文學巨匠,莎士比亞卻經常給我們相反的印象:他讓我們不論在外地還是在異國都有回鄉之感。他的感化和浸染能力無人可比,這對世界上的表演和批評構成了一種永久的挑戰”,這樣一種突破了文化與國界的“回家”之感,正是對于經典之作超越民族的世界性魅力的貼切描述。文藝與文化絕非空中樓閣,而是在各民族發榮滋長過程之中自然生發而來的,作為精神力量源泉的文藝與文化必然有其“民族”的血肉身體。因此需要我們在浩瀚廣淼的世界文藝經典海洋之中,在 “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張力之中,選擇根植于世界各民族共同體發展歷程之中、同時又具有普世性啟發的“文藝高峰”范例。
三、經典傳承與記憶形塑:文藝高峰認知的代際偏向
承前所言,文藝高峰評價標準之中至少存在著三重結構張力——審美性與社會性、時代性與永恒性、民族性與世界性。這不僅是評價文藝高峰或者說經典之作的標準,同時也是文藝杰作的接受者們借以認識傳統、建構認同的三個基本向度,也即在對文藝經典的接受與欣賞之中,藝術公眾在處理著個體(審美性)與群體 (倫理性)、過去與當下、民族與普世三者之間的關系,并在這三個維度之中雕琢自身的身份認同,處理著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系。正是這一活態化的接受語境使得藝術高峰的評價標準保持著不可化約的張力。對此,我們將結合當代“文化記憶”理論,進一步闡釋藝術公眾對文藝杰作的接受與自身認同的形塑之間的關系。
法國歷史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雖然每個個體都認為自己的記憶是精確無誤的,但實際上“社會卻不時要求人們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現他們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還要潤飾它們,削減它們,或者完善它們”②[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頁。,正是這種“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將我們的個體思想置入其中,并匯入到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中去。③[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而當代德國歷史學家揚·阿斯曼(Jan Assmann)發展了這一思想,并且將關注點由日常生活與交往的記憶,進一步轉換到對于“文化記憶”的關注之中。在阿斯曼看來,更為重要的是活生生的日常交流如何通過客觀化的文化形式結晶下來——無論是通過文本、意象、儀式、建筑物、紀念碑等等,從而形成穩定的、延續的、影響廣泛的“記憶的形象”,從而為塑造群體傳統、構建文化認同奠定了基礎。而文藝高峰或者經典之作無疑正是其中最富于魅力的 “記憶形象”,處于“文化記憶”的核心地帶。在阿斯曼看來,“文化記憶”最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重構能力”,也即“文化記憶通過重構而發揮作用”,雖然它和固定的記憶形象(如文藝杰作)穩定地聯系在一起,但是,“每一個當下的語境都有差別地聯系于這些記憶形象。”①[德]揚·阿斯曼:《集體記憶與文化身份》,陶東風譯,《文化研究》2011年第11輯,第3—10頁。以文化記憶的“重構能力”來反觀文藝高峰,絕非質疑經典之作的某種永恒性,而是指出一種更為復雜的現實情境。文藝杰作——無論是達·芬奇的《蒙娜麗莎》,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固然有著諸多客觀的屬性,但只有聯系于一個時代情境,并在其中為藝術公眾所接受之時,才最終能在一個時代迸發出新的魅力。由此也引申出一個饒有興味的話題,在當下中國,藝術公眾對于文藝高峰的概念認知與評價標準有著怎樣的具體差異與偏向,是否體現了上述經典接受與身份塑造的三重向度呢?這其中無疑有著復雜的機制與多樣的問題,筆者對此收集了兩次小規模的調查問卷,在此嘗試從調查結果出發來做一個初步分析。
2019年6月,在國家機關干部專題研修班上,由王一川教授主持進行對文藝高峰認知的問卷調查,收取了53份樣本(以下稱A組)。2019年12月,筆者在本人所開設的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藝術理論”課程上,也進行了相同問卷的調查。參與者包括廣播電視、美術、音樂、舞蹈與藝術學理論各專業的2019級研究生新生,收取了87份樣本(以下稱B組)。前者調查對象的年齡段以60后、70后為主,而后者則以90后、特別是95后為主。這年齡與境遇差異頗大的兩代人,對于文藝高峰的概念意涵與評價標準的認知有著怎樣的共識與差異呢?
首先在多選題“‘文藝高峰’就其內涵而言應該包括如下哪些層面”中,無論是A組還是B組,“取得最高藝術成就的整個藝術時代,如‘魏晉風度’‘盛唐氣象’‘文藝復興’等”這一選項都取得了最高票數(A組38人贊同,占A組總人數比約為72%;B組76人贊同,占比②此處及以下所說的“占比”,除特別說明外,皆指該組選擇人數占該組總人數的比例,百分比取約數,四舍五入至個位。約87%)。而A組的次多選項為“取得最高成就的藝術家及其藝術品,如曹雪芹及其《紅樓夢》”(A組64%;B組69%);B組的次多選項為“取得最高藝術成就的藝術流派及其藝術風格,如明代由沈周、文徵明、唐寅等名家組成的吳門畫派”(B組78%;A組55%)。在選項 “體現最高美學成就的藝術體裁或藝術門類,如唐詩、宋詞、元曲等”中,A組選擇人數占比約為58%,B組約為69%。可以看到兩組對于“文藝高峰”各指涉層面的普遍共識,都對“取得最高藝術成就的藝術時代”最為贊同,或許因作為整體的“藝術時代”,在體量上最為卓越龐大,往往涵蓋燦若群星的藝術家或藝術經典、藝術流派與藝術體裁,因而也最為藝術公眾所普遍認同。
在對文藝高峰的外延指涉有著普遍共識的基礎上,問卷調查所涉及的兩類人群也有著各自的認知偏向,體現出評價標準之中存在的審美性與社會性、時代性與永恒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三重結構張力。
首先,調查結果體現了文藝高峰評價標準中審美性與社會性之間的張力,從中可以看到藝術公眾在經典接受之中斡旋著個體認同與群體認同之間的關系。在單選題“衡量‘文藝高峰’最重要的指標是如下哪一項”中,A組和B組的最多選項都是“藝術作品對現實生活的深切關注與呼應”(A組42%,B組55%)。但A組的次多選項為“眾多藝術史著作稱頌記載”,占比約為21%,B組則約為3%。B組的次多選項為“藝術語言與藝術技巧的純熟精湛”,占比約為20%,A組則為6%。對于“作品主題內容的宏大高遠”,A組選擇人數占比約為17%;B組則約為8%。對于“受眾群體的龐大廣泛”,A組占比約為13%,B組約為7%。如上四個選項,A組與B組差異懸殊。從中可以明顯看出對于文藝高峰指標這一問題,A組更偏向于從藝術體制與內容主題等社會性因素來判定藝術高峰,而B組則傾向于關注藝術語言與藝術形式等審美因素,認為受眾廣泛和藝術史權威與文藝高峰判定之間的關系微乎其微。
其次,調查結果體現了文藝高峰評價標準中時代性與永恒性之間的張力,從中可以看到藝術公眾在經典接受之中協調著過去與當下之間的關系。在多選題“古今中外哪些時代出現了文藝高峰”中,兩組選擇“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唐宋時代”“五四時代、新中國成立以來” “西歐文藝復興時期”三個選項的比例相差不大,但對較為晚近的時代是否出現了文藝高峰,如“改革開放及新時期以來”(A組13%,B組39%)、“19世紀英法俄德美國” (A組26%,B組37%)、“兩次世界大戰之間”(A組2%,B組39%)兩組有著顯著不同的看法,可以明顯看出B組更為認同晚近時代也出現了文藝高峰,特別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當代文藝狀況抱有更為肯定的態度。與此相應,在多選題“下列哪些中國現當代文藝作品算得上是‘文藝高峰’”中,兩組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小說《紅旗譜》《青春之歌》《創業史》《保衛延安》”(A組64%,B組36%),電影《芙蓉鎮》《大決戰》 (三部曲) 《焦裕祿》 《鴉片戰爭》(A組34%,B組52%),小說《紅高粱》《廢都》《活著》《欲望的旗幟》(A組26%,B組90%),電影《生死抉擇》《我的1919》 《唐山大地震》 《芳華》 (A組11%,B組47%),小說《受戒》 《大淖紀事》 《異秉》(A組0%,B組22%)。可以看出A組認為《紅旗譜》等革命歷史小說更能代表當代文藝的高峰成就,而B組則認為 《紅高粱》等新時期以來的文藝作品更是當代文藝杰作。對于這一文藝高峰認知的代際偏向,還可以從當代傳播媒介狀況的角度加以考量。在多選題“結合上題回答,您是通過何種途徑與這一‘文藝高峰’相遇的”中, “學校教育與老師教授”(A組57%,B組80%)、“書籍報刊等印刷品推薦”(A組60%,B組67%)是最經常與文藝高峰相遇的渠道,同時A組選擇“朋輩推薦”選項為13%,B組為31%。可以看出,書籍報刊等傳統媒介的推薦固然是公眾認識文藝杰作的重要方式,但受到“電視與互聯網傳媒資訊”的推薦而與經典相遇的比例,兩組有著懸殊的差異,A組選擇人數占比32%,B組則達到了72%,無疑新一代對文藝杰作的接受是與影視、互聯網等當代媒介緊密聯系的。
最后,調查結果也體現了文藝高峰評價標準中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張力,從中可以看到藝術公眾在經典接受之中協調著民族與普世之間的關系。如在單選題“造就文藝高峰最為重要的因素是如下哪一項”中,A組和B組的最多選項都是“特定時代的社會歷史條件”(A組51%,B組54%)。而A組的次多選項為“民族文化傳統的積累”,占比約為34%,B組則約為18%。B組的次多選項為 “藝術家的敏感與天才”,占比約為21%,A組則為13%。選擇“杰出文藝批評家的引導” “接受語境的恰切適當” “科學、媒介與技術條件”等選項的人數微乎其微。可以看出兩組在共識的前提下,A組明顯地偏向從民族文化傳統的角度看待造就高峰的條件因素,而B組則傾向于從無分國界的藝術家的天才與敏感看待文藝高峰的形成。與此相應,“下列哪些外國文藝作品算得上‘文藝高峰’”這一問題上,兩組對于晚近時代的外國文藝狀況也有著明顯不同的看法,特別體現在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組“《追憶逝水年華》《等待戈多》 《變形記》 (卡夫卡) 《麥田里的守望者》” (A組38%,B組60%),當代電影作品組“《泰坦尼克號》 《阿甘正傳》 《肖申克的救贖》 《黑客帝國》” (A組36%,B組66%),可以看出新的一代對國外現代影視經典與現代主義文藝經典有著更多的接納與喜愛。
綜上所述,在文藝高峰評價標準的三重結構張力——社會性與審美性、永恒性與時代性、民族性與世界性,對應著藝術公眾在經典接受中群體與個體、過去與當下、民族與普世之間的協商與偏向,而問卷調查A組所涉及的60后、70后中國藝術公眾正傾向于對立項中的前者,而B組所涉及的新一代中國藝術公眾則傾向于后者。指出這一對立與偏向絕非質疑文藝高峰的普遍魅力與光輝,而是要說明每個時代的藝術公眾都是在身處的語境中與之相遇,從中汲取價值、鍛造自我與形塑生活,正如艾倫·布魯姆所言,這些“位于偉大傳統中的著作”,其永恒魅力也正在于能給人們以“嚴肅的而非假冒的整全性的模型”,將“它們與生活的關聯作為一個整體來呈現。”①[美]A·布魯姆:《巨人與侏儒:布魯姆文集》,秦露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8頁。本文力圖描摹文藝高峰評價標準的這種張力結構,而非確立某種條框約束的 “硬指標”,正是相信藝術杰作得以“傳世的秘密”②陳雪虎:《“傳世的秘密”解析:試探文藝高峰的內在規定性》,《當代文壇》2019年05期,第64—71頁。所在,在于經典與人在現實語境中的鮮活相遇,寓于文藝經典與藝術公眾“生活關聯”的整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