窺探“真實”
石翔
我們偏執得去要求通向真實的方向,并且試圖不斷地走向更遠的方向。可是對于真實本身的討論,卻又是一個極為虛無的概念。如今對于生活在社交網絡里的一代人而言,真實又被加上了一層濾鏡,在網絡環境之下,爆發的情感把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塑造成了極為強烈的符號。這些符號真實存在著,卻又遠離了生長符號的土壤。
這樣的真實并非由那片土壤帶來,所以順著茂密向下窺探,搞清楚土壤成分的意義在某些程度上被削弱了。這是在新聞報道里遭遇的困境,我們可以花很多經歷去描述“uzi”這個符號背后簡自豪真實的生活狀態,但當這些內容開始被傳播的時候卻在遭遇困境。
在社交網絡上,大家不愿意看到土壤的樣子,有些時候是因為營養里摻雜著污濁,但更多的時候只是因為并不在乎。我們說那片土壤是絕對的真實,這是必須清楚的,在歷史的沉淀中不會褪色的東西,無論風吹雨打,冬去春來,這些土壤的樣子當然值得被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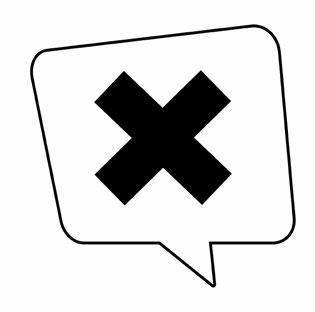
可是土壤之外的枝繁葉茂,同樣也是“真實”的,只是來自于集體狂歡而形成的真實,一群人基于不真實而創造的真實。
可能在當下這個時代,這個創造的過程也同樣非常值得被記錄,可又是一個困難的過程。記者不僅要找到一些節點,以這些節點出發去那“一群里”里尋找答案。在篩選節點和篩選某些個體的時候,難免會有主觀的判斷存在。
這些判斷會成為報道的一部分,這是真實性相悖的,卻又不得不面對的情況。也正是因為如此,如今基于網絡去尋找更多的人,來豐富報道的樣本量和角度,從同一個話題出發。同樣通過社交網絡的能力來形成對于這個話題的討論,讓更多的人參與其中,最終為深度報道的完整性所服務。

從枝繁葉茂的表面,到連接這一切的根莖,記者從最初的獲取信息的能力改變為在篩選信息和獲取信息之間不斷優化路徑,在有限的條件之下獲得“真實”的全過程與全剖面的分析能力。
當獲得了最夠的信息之后,通過更多角度共同得到的真實會讓整個過程變得更為完整。這次關于簡自豪的報道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而設立的,從最初的社區調研,到第一輪決定方向的采訪,再到一輪完整的問卷調查,再到下一輪的更為深入的采訪,再到糾偏似的的補采。
這個過程本身是實驗性質的,索性結果獲得了一些不錯的答案。我們通過轉換角度,逐漸了解了簡自豪過去五年時間里,是如何從一個真實的人轉變成了一個虛擬的符號。
這些喜歡他的人又是如何把這個符號和自己的生活勾連在一起的。通過這樣的聯系,我們試圖找到一些可以推而廣之的東西,最終并沒有成功。回溯這個枝繁葉茂的過程本身的意義仍舊重大,當人們試圖了解簡自豪的時候,一本自傳可能是更好的選擇。而當人們試圖了解“Uzi”的時候,這篇報道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這次嘗試也有額外的收獲,把一部分放到一個小環境里,讓討論加劇,進而獲得更多的信息。我們試著把簡自豪的粉絲和黑粉各自組成了一個群,粉絲們在尋找共同記憶的過程里為報道豐富了很多有效的信息,作為旁觀者,尋找共同記憶的方式也非常有趣。
作為一直堅信真實性是新聞報道生命的媒體,在有限的條件之下,去利用社交網絡的獨特性來尋找出路,這樣的嘗試還會繼續下去,也許會遭遇更大的困擾。本社但本身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