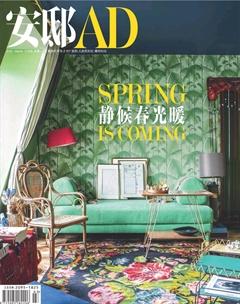相離相合





搬進這里前,兩位藝術家的工作室和住所一直是分開的。即使是兩點成一線的來回跑,就北京的現實交通而言,也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時間大多消耗在路上了。擁有一個居住、工作合一且安靜的空間一直是他們的愿望。幾年前,他們和幾位藝術家朋友聚集聊起,在遠離城中心的地方建立藝術園區,這個想法逐漸現實起來。于是,兩位藝術家在這里建造新生活空間的任務就交給了做建筑師的女兒劉焉陳。
在開始設計之前,夫婦二人對工作室提出了許多功能需求:兩個畫室的距離.作品運輸的方式、空間凈高、光照要求等。也因此,設計師與藝術家的討論往往會具體到每一扇窗戶的位置、每一扇門的高度。作品的運輸往往是藝術家工作室的痛點,也是劉焉陳對整體流線考慮的重點,連續的展廳坡道、一個貫通三層的運輸畫槽都是藝術家的“剛需”。大幅作品難以通過日常樓梯、電梯解決搬運問題,而有了畫槽,不僅方便作品運輸,還可以替代藝術家創作大幅作品時常用的爬梯。兩位藝術家因為各自創作的特點,又有不同的需求:劉慶和的國畫創作需要大幅的墻面,而陳淑霞的油畫創作需要柔和穩定的自然光線。這就決定了兩個工作室不同的空間處理方式。藝術家對于自己的創作需求清晰且細致而如何讓每一個特殊的要求和整體建筑的空間排布與建筑立面和諧統一就是設計師要操心的事了。
工作室里的坡道和走廊并不是最高效的選擇,卻能讓人在緩慢行走中完成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的過渡。



多功能空間在條形天窗的處理下顯得明亮而柔和。

1.主人工作室場景。

2.工作臺細節。

3.國畫室空間。
劉焉陳為這個家取名“垣宅”,因為墻是整個建筑空間中最重要的邏輯構成要素。從東到西一系列的墻體分隔也定義了每一處空間,在人口的中庭,一左一右兩面墻呈扇形相夾。這里是整個建筑重要的過渡空間,將工作區和生活區分開。一邊是圍繞著一處內庭院的日常起居、健身空間,另一邊則是兩位藝術家時常對外開放的展廳。藝術家工作室有定期的開放日、朋友拜訪等,這都意味著整個空間必須是隱現相間的,于是,這個扇形中庭成了整個工作室最常使用的公共區域。中庭一側的旋轉門可隨時開啟、關閉,保護居住區的私密性。一家人可以各自忙碌,也可以一起在這里享受交流和寧靜。
劉焉陳熟悉父母的生活細節,知道媽媽很喜歡種植,于是“垣宅”的很多墻體是用專門定制的花盆磚砌筑的。這些磚是中空的,可以填上土,種花種草。在劉焉陳看來,父母雖為親密夫妻,但作為藝術家從來都是完全相互獨立的。因此,讓兩個工作室相隔的距離在有限的空間里達到最遠的感受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設計目標。兩個工作室雖然看似直線距離相隔不遠,但沒有直接的通路,只有穿過起居的空間或者通過屋頂的露臺,才可彼此探訪。陳淑霞的工作室在二層,向上可以直接通到自己的露臺,走下來直接就是廚房,讓她在工作與生活的角色中時常切換。地下的工作坊和書庫是共用的空間,抬頭可以透過玻璃天窗,看見游在院子中的魚。采訪那天,劉慶和恰好也在家,正忙忙碌碌地做著自己的木工活兒。墻把劉慶和一家的生活分成了很多片段——是一天中的不同片段,也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不同片段。

1.入口中庭的設計從光線.材料和氛圍上都描繪出冬季花園的形象。

2.建筑內庭院立面留有大面積開窗。

3.工作室外部視圖。墻是這個工作室建筑的最主要空間元素。

內庭院空間。
劉焉陳自本科畢業以后一直在外求學,當從抬頭可見的微距里抽離,隔半年或一年時間回來時,父母新的創作上劉焉陳發現他們或許進入了一個新的狀態她會意識到父母作為藝術家永遠都有一個自己的內心世界,這個內心世界就像茶室的公共空間和工作狀態一樣,時而開啟時而關閉,想要去了解沒有捷徑。先抽離,再去看,“你會看到隱藏更深的一些情感,有時候是憂傷,有時候是孤獨”,劉焉陳說。這些難以名狀的感受在房子里被轉譯成一種行走的狀態:不論是通向展廳的坡道,還是房屋北面的過道,或者樓頂的步道,這些路徑其實并不是效率最高的安排。“但希望讓人能在這樣一個行走的狀態中,在工作與生活的不同狀態之間完成一種過渡和緩沖。”墻在“垣宅”中并不是完全封閉的,有很多空間貫穿過墻,有些空間垂直于墻。其中的相離相合也成了一家人獨立工作、獨立生活和溝通交流狀態的映照。
就藝術家的工作室來說,這個展廳算是“奢侈”了,地下一層空間十分寬敞且獨立。在那里還可以找到“垣宅”的模型。“垣宅”地塊的方向其實并不是正南正北的,劉焉陳特意為居住一側安排了一個12°的轉角,讓整個居室旋轉到采光最佳的狀態。房子剛蓋完的那個冬天,一直對劉焉陳的平面圖沒太多感覺的劉慶和一個人從頭到尾把房子走了一圈,一邊走一邊想著女兒處理每個地方的理由一突然發覺剛剛路過的那個轉角,確實一下好像換了一種心情,進入了一種新的狀態,這才更能體味相離相合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