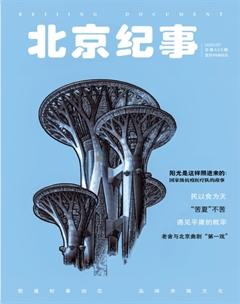民以食為天
陳雙媚

陳雙媚,筆名語霜,劇作家,戲劇深度嗜好者。作者說“茶是泡來品的,戲也是演來品的。一出戲搬上舞臺,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有人關注思想性,有人考究藝術性。我呢,除了自己寫的幾筆,大多數時候就是一位觀眾,不妨扯扯可看性。”
演戲的,自然是“逢場作戲”,但幕后逢場作戲就糟了。幕后入戲得深,臺前“假戲”才有得“真做”。
挑戲看的,不及觀影“幸運”,觀影常有片花和大量影評可看。可戲劇呢,雖偶爾來點“劇透”,但自媒體時代,劇情簡介就像網紅臉,長得都差不多,哪里看得出子丑寅卯?
難為看戲的人了。怎么辦?!人生本就是一場戲。沒戲的已經散戲,繼續演著的,真的有戲。
這些年,看了不少戲。首先看劇名,線頭穿進針孔里,對上眼了就看唄。《陳奐生的吃飯問題》我一眼就對上了。
生命一誕生,就需要食物來維系。人類為了生存和繁衍,也是千思百想。據說先人們在6000年前就研究出了水稻的人工種植方法,由此推算,光是米飯咱就已經吃了6000多年。在21世紀的今天,大人愁孩子不愛吃,孩子愁吃著不香;胖子愁一吃就胖,瘦子愁怎么吃都不胖;懶人愁怎么吃著方便,領導愁怎么吃得有效率。只要還能吃,還要吃,吃飯的確依舊還是一個大問題。想想自己也算半個吃貨(飯量有限),對于吃飯說上一二也不是難事。嗯,就是它了。

1
《陳奐生的吃飯問題》是江蘇省常州市滑稽劇團創排的一出滑稽戲,全劇場景設置簡練,一個家庭幾十年的變遷濃縮在一桌一椅一宅之中。場景的切換采用時間滾軸,一敲一翻就是時間穿梭歷史輪回。表演幽默風趣,造型夸張滑稽,舞美動漫化,語言方言化,形式上很有看頭。但光有形式不行,好的戲里外都得有看頭。
編劇的高明之處在于把背景放在一個特殊的年代——改革開放前后四十幾年,把這么個宏大的主題濃縮在一碗飯里,放到一個由光棍、傻妹、三個同母異父的孩子組成的特殊家庭里。劇情更是滑稽荒誕,一個要飯的傻妹因為一碗飯嫁給了光棍,光棍用一碗飯討了個老婆還附送了三個孩子。嘿,這可都是占便宜的事啊?沒那么簡單!

這碗飯可謂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它是沉甸甸的責任,它是波瀾起伏的命運,它是良知與人性的角逐,它是道德與欲望的對抗。吃與不吃,編劇把勝利的天平最后偏向了人的良知。我覺得與其說是對人性本能的不自信,不如說人的本能里就有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肉體需要五谷雜糧提供營養,靈魂也需要精神食糧滋養,這就注定人性的內核是復雜的。編劇把這種復雜性化作一粒粒米飯,裝在一個碗里,變成了戲劇的種子,構筑起人物的心靈空間和情感空間,為戲提供了內在的看頭。
2
戲的種子萌發于編劇,人性的種子卻會在觀眾的心里發芽。
種子只有生根發芽之后,才能看出基因有沒突變,是變得更完美,還是變得殘缺。但若要種子發芽,得有陽光,得有雨露,再不濟也得有盞燈。只是如陳奐生所說,有的人心急火燎,忘了開燈;有的人一肚子心機,心里根本沒有燈;有的人心黑了,有燈也沒有用。所以,長出來的苗千差萬別。
民以食為天,這是陳奐生心里的種子。他對家庭責任的理解是讓家里人吃飽飯;他對未來的規劃是有一兩省著吃,有一斤論斤吃,有一噸放開吃;他的信仰是人不虧地皮,地不虧肚皮,只要有種就能活出個人樣來。
這樣的種子最為普通,常常被淹沒在籮筐里。可它的基因最穩定,哪怕不能變得更完美,起碼不會變壞,所以我們的飯才得以吃了6000年,盡管花樣日日翻新,卻仍將繼續吃下去。
3
老二陳斤的飯,是怎么方便怎么吃。
他基因在不斷蛻變,呈現在他性格上的美和丑是搖擺的,欲望隨著他的生存狀態的改變而改變。他不會固守成規,在改革開放之初,他放棄土地,敢于做時代發展的弄潮兒。但是他在隨波逐流中失去自我,被浪打得鼻青臉腫的時候,又想起當初放棄的土地,撒潑耍賴也要弄到手。“人可以自私,但不能影響別人自私”的歪理讓人大跌眼鏡。真是基因突變后的一朵奇葩!
可陳斤這樣的人卻不是特例。
如今的飯,許多人不就是為了吃得方便嗎?在哪兒吃,吃什么,都不是問題,問題是和誰吃才方便,怎么吃才方便。不方便的吃到方便,已方便的吃了更方便。你不吃,讓他人不方便;你吃了,大家都方便。所以,吃飯就是為了方便。你方便也要讓別人方便,別人方便也不妨礙你方便;你要只顧自己方便而不讓別人方便,那別人為了自己方便就會耽誤你方便;你不方便也不讓我方便,我不方便我也不讓你方便;你不方便我不方便大家都不方便,你方便我方便大家都很方便。繞得你暈頭轉向,最后發現確是真理。
4
老大陳兩的飯不在于吃,而在于形式。
在饑餓中長大的孩子,為饑餓狼狽過痛苦過無助過,不在饑餓中沉默就在饑餓中爆發。老大爆發了,人窮志大,從蒼蠅慢慢長成老虎。老大說,他最初只是想要一雙皮鞋,可是不斷壯大的“志向”,讓他逐漸模糊甚至忘記如何等價換算。如果他能像父親陳奐生一樣嫻熟于換算,知道稻谷收購價是每斤一塊錢,就會知道兩百多萬塊錢需要賣多少糧食,需要多少農民多少土地多少年才能種出來。或許,他的“志向”還沒長大就被嚇回去了。

曾聽某教授講過一堂課,說有一次老母親從老家來到他工作的城市,朋友們知道后很熱情,非得請老太太出去好好吃一頓。吃完飯回到家,老太太問他,那頓飯吃了多少錢?他答三千元。老太太脫口而出,一頭豬啊!陳奐生對糧食的換算讓我想起教授母親對豬的換算,這樣的換算讓我對吃飯產生了敬畏,吃與不吃,怎么吃,吃多少,吃誰的,不算算清楚,還真不敢輕易起筷。
有些飯,良苦用心地做,哪怕一開始夾生,但火候一到,飯香是蓋不住藏不了的。而有些飯,從淘米開始就精挑細選,絲毫不敢馬虎,可卻吃出了問題。有人慌忙反思,找出了錯漏環節,亡羊補牢,及時止損。而有人卻只怪吃飯的人不懂飯香,浪費了一番心血。
5
看完《陳奐生的吃飯問題》,余興未消,我把它講給父親母親聽。聽罷,父親說,我們家的命運也是吃飯吃出來的。9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大潮涌到了農村,父親母親在爺爺房間商量到半夜,第二天通知我們,他們要進城。我們來不及反應,來不及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乘坐的中巴車已經駛向遠方的城市。我們成了留守兒童,等他們再回來,我們已是法律上的成年人。十年缺失,多少遺憾無法彌補,多少罅隙夾雜其中,幻化成一道看不見的墻,讓彼此無法真正親近。父親繼續說,當年中巴車半路在一個小鎮歇腳,母親下車后卻再也不肯上去,無論父親生拖硬拽,她就是一手死死抵住車門。僵持了半天,司機催促,乘客抱怨,父親生氣,母親都不為所動,只有一句話,我不能丟下孩子們。而最后讓母親乖乖上車的是父親一句話:要想你的孩子將來有碗飯吃,就必須讓他們讀書;要想交得起學費,你就必須上車。父親說完,母親偷偷抹眼淚。瞬間,阻斷親情的那堵墻轟然倒塌。背井離鄉,拋家舍子,十年缺失,半世疏離,只為孩子的一碗飯。如今,我已端著飯碗安然度日,尚矯情什么?我起身,輕輕擁抱了母親。這是二十幾年來,第一次。
至此,我忽然有幾分感悟,這哪里是在看戲,這就是透過一粒米一碗飯在看世態人生啊。你道是“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可你哪里知道,戲劇伴隨人類走過了多少艱難歲月,正是那種看似的瘋癲,讓你的人性還保留了可貴的傻氣?戲劇也許無法改變某種生態,但于演者、于觀者,是困頓的傾訴,是情、愛的宣泄和共鳴。如此,足矣。
有戲的繼續著,假裝有戲的在死撐著,沒戲的已經散場。
我依然目不轉睛盯著舞臺,因為那兒真的有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