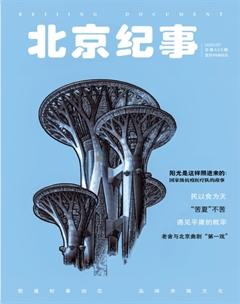遇見平庸的概率
王徹之

王徹之,2016年本科畢業于北大中文系。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牛津大學文學博士。曾獲北京大學王默人小說獎、第五屆北京詩歌節年度青年詩人獎、第一屆新詩學獎等。作品入選數種國內外選本。著有《詩十九首 19 POEMS》(紐約,2018),《獅子巖》(海南,2019)。作者說“良好的教育環境塑造人并不是單憑它的優點,而更多的是通過它隱藏不露的非常之處,它鮮為人知的缺陷和混亂,它里面的人孤單或者怪癖的個性,甚至它一草一木枝干扭曲的姿勢和河水在深夜奔流的凄涼。要認真去想的事兒。”
長期以來,規律一直告訴人們,在任何地方,遇見平庸事件的概率,要遠大于遇見偉大事件。因為愚蠢、魯莽和野蠻深藏在人的天性里,至于真理,鮮有人能對其始終保持好奇心和探尋的勇氣。基于這種考慮,作為嚴格意義上的職業學術追求者,和“業余不學無術者”,我很早就放棄了對于任何偉大學府的美好想象。這種想象不能帶給我一丁點的心靈收益。一個人需要對人類智慧保持狂熱的好奇心,但同時必須抽身在一旁,用魯迅的話說,冷眼旁觀。
我的某位詩人同行,某名校本科畢業,很早就公開宣稱,他本科四年所受教育的最大收獲,就是以后一定不會讓孩子在他的母校讀書。這句話可以分兩個層面理解:一個人在他所待的地方越久,就越會對這個地方感到厭倦,不管這個地方有多好或者多糟;在多數人艷羨的地方,常常有不為人知的、無法讓人忍受的現實存在。但無論是哪種,不能否認的是,當你厭倦或者無法忍受,你實際上已經帶有你所在地方的缺陷的烙印。
由此說來,牛津也并不是我來之前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各種背景、文化、膚色、階層、知識教養、政治態度各異的人在此地混雜而居,并且似乎沒有誰愿意主動妥協。入學牛津第一天,有一位好心的學姐,拉著我轉了差不多整個校園。我還能記得的是,她咯噠作響的高跟鞋,就像訴說著此地人們很長時間以來的,聽上去臭美而無害的傲慢。

牛津市中心是大學所在之地,東西向的主干街只有兩條,一條叫寬街,一條叫高街,但實際上不高也不寬,并且被一條更短小而且游人密度更大的商業街相連——多半是因為這條街上的肯德基和星巴克,這些英國人其實夢寐以求的文化象征。
而肆意穿行其間的游客、小販、提琴手、玩火藝人、攝影師、高定禮服的模特、放浪嬌嗔的夜店女孩、游行示威人群、懷揣著羅馬史教程的大學教授和詐騙犯,會讓你明白當地老年人排外似乎也有一分理由。誰會在這里尋得片刻寧靜?

據我的經驗,這片土地的逼仄和混亂程度遠遠超過了北大或者哈佛這類學校。你盡可以去市中心以外的濕地去看綠頭鴨打架,看牛和小矮馬怎樣在人們好奇的打量中淡定地吃草,就像學生們吃學院的正餐,也可以去南部公園在草地上睡它一個下午,但這一切遠不如對這一切的無暇顧及和審美疲勞更能占據留學生活的主流。或者說,在這里生活是一個在審美驚奇和審美疲勞之間不斷搖擺的過程。一個人無法取得平衡常常是因為,很大程度上他在牛津過的生活是其他人的生活,或者其他人以為他會過的生活,甚至是他極其有限的影響圈子內,聚光燈下人們想要看見的生活,但這種生活有很大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并和他的習性脾氣并不搭調。
為了擺脫混亂和失衡的危險,我很早就提醒自己多參加體育運動,為此剛開學就加入了擊劍社。以前我有這方面練習的經驗,但技術不足,完全憑身體的本能。在這個社團內無論你打的是好是壞,周圍人都差不多會言不由衷地贊嘆:你之前是不是練過,你打得真好!但這種虛與委蛇就像擊劍者身上的白衣,并不會真的讓你感到厭煩,就像老師對你的鼓勵,或者別國學生對你膚色和文化的好奇一樣。其實很多學生來這兒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拍照,但他們又為擊劍房骯臟的陳設和凌亂的布局感到失望,因為這看上去沒有一點貴族氣質。如果說擊劍是為了磨煉勇氣,那也絕不是單身漢或者起義軍的勇氣,而是貴族的,在體面的基礎上的勇氣,并且講究禮數。這似乎能解釋為什么拜倫年輕時熱衷運動,或者奈保爾在牛津為什么過得并不順利。一個和我同齡的,以前沒有參加過任何運動的中國女孩以前也會來這個社團。她不好意思地說自己是博士。我似乎也能看出她的害羞靦腆已經與牛津的氛圍格格不入,而同時我又明白這種格格不入,在某種程度上,卻又是這個學校長期以來的特性之一。
為此我更愿意和她說話,有一次在雨天甚至聊了一路,發現她對學術和生活的熱忱要遠勝過我——而這正是以前我在芝加哥的同學常常對我說的。這種投身研究事業的生活時常讓我感到害怕,但是它所暗示的寧靜又讓我能在雨后的街頭加快步伐,感受到所謂生命之輕。女孩周圍的博士明顯分為兩個極端,一種和她一樣日夜埋頭工作,另一種則喜歡在各種行政事務中,或者公眾場合內拋頭露面。但她感到不解,因為其中的多數人聲稱,他們能很好地在兩種角色中穿梭自如,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某個實驗或者某項考試做得好,并不能說明一個人的天分或能力,而在社交中游刃有余同樣如此。這種自以為能兼顧的人,她說,到頭來你會發現,人生收獲最多只是社交平臺上幾張慶功照,給人們留下春風得意的印象,但實際上很可能沒辦法在任何事務中做到真正出色。

聊了兩次之后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這并不奇怪,在牛津遇見的人時常會在未來幾年內,在你的視線內滅絕。但她說的話很明顯在遵從自己內心的某種原則,像是按照既定尺寸在給衣服或者鞋畫線,容不得閃失,否則某些東西很可能會失控。但她口中所說的這種人毫無疑問是無聊的,因為其數量龐大,又讓人感到壓抑。這種實質上的平庸和對這種平庸的趨之若鶩,不僅影響學生們的日常生活,也體現在教學體系對各色活動的熱忱中,就像蜘蛛對它網上的各種昆蟲垂涎欲滴卻不明就里。
因此我很長時間以來只愿意參加有實質性內容,并且觀光客心態比較少的小型學術聚會。與那些更擅長和別人交談的老師和學生相比,喜歡自說自話的倒更顯得很有說服力。我曾在哲學系維特根斯坦的課上見證一個老師長達5分鐘的自言自語,端著下巴,厚玻璃眼鏡后的小眼睛對著面前的小白板,仿佛在給愛人相面。而往往正是在這種時候,我腦子里本就迫切想飄到窗外的狂亂安靜了下來,回歸到自我沉思的狀態,感到之前一些不得其解的知識明朗了許多。但在與人爭論時,要么是我的英語不夠好,要么是對方的腦子不夠好,要么相反,我們為之面紅耳赤的議題會更加模糊不清,最后往往以對多元主義的認可不歡而散或轉移話題。
在東方研究中心,歷史系和英文系,很多學生學者都不特別擅長與人打交道,在這方面我自認為比他們有優勢得多,但激情和對所專注之物的確信不疑卻遠遠不如。這是一群吃火鍋也會和你扯兩小時阿爾都塞的家伙。但由于我對理論熱情的逐漸冷卻,我還是斷然以吃飯為主。不過這種飯桌上的喧鬧如今已經越來越少,和街頭調門日益升漲的薩克斯,以及忙著做直播的學生和游客越來越多的聒噪形成對比。但是我卻時常奇怪地想到,拉金或W·H·奧登很可能會在這種情況下依然保持創作的熱情,混亂和喧囂的土壤可能恰是培育疑似思想之物的溫床,如果我們認可迄今為止人類還保有思想的概念的話。
如果這個前提得到確立,我確實慶幸在那些“全城一片黑,沒有奶油的日子” ,我從沒有忘記學習在這種黑暗中與自己相處這件事,盡管之后我慢慢明白,我付出的代價要遠比我預想中的多。
編輯 馬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