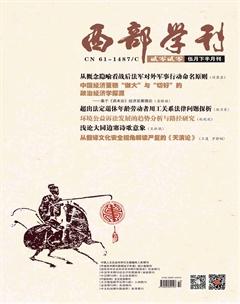淺論大同邊塞詩歌意象
摘要:大同既是歷代軍事重鎮,也是中國古代無數激昂壯麗的邊塞詩歌的誕生之地。而唐代詩人以大同邊塞的自然意象、地名意象、樂器意象為主抒發豪情,構起了大同邊塞詩歌靈動的詩魂,體現了戰士們忠勇壯烈的豪邁情懷、為國征戰的無畏精神。詩中諸多邊塞意象的借用,使得詩歌的空間延展更為開闊遼遠,情感詠嘆更為生動傳神,風格上呈現出雄奇壯美,增強了詩歌本身的承載力。
關鍵詞:大同;邊塞詩;意象
中圖分類號:I22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20)10-0146-03
意象在詩歌中尤為多見,它是作者主觀情感與客觀事物融匯的產物,帶有深遠的蘊意。意象可以跨越語言 本身的局限,拓寬文學藝術發展的空間。《周易·系辭》云: “圣人立象以盡意”,《莊子·外物》篇提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主張。可見,“意”與“象”“言”之間 存在密切的關系。意象是作者思想情感的凝聚,作者不 便直接表露的情感會通過意象傳遞給大眾,使那些承載 著作者情感的詩歌變得更為生動傳神。“夫詩者,不可以 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1]? 詩中作者所表達的情感需要我們用心去體會,同樣地,詩歌中使用的意象也需 要深刻地研究考察其深意。大同邊塞詩諸多意象的使用, 使得詩歌在空間延展上更為開闊遼遠。
大同位于山西省最北端,古稱“平城”,北魏在此建都,亦是遼金陪都,它處在中原地區與西北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帶上,歷史上這里發生了多場戰役。長期的戰爭環境,為邊塞詩歌的創作營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孕育了獨特的邊塞文化。詩人們通過入幕、出使,或以奉命參戰的方式來到這里并產生了深厚的感情,隨后又將這樣的情感訴諸筆下,創作出大量有地域特色的邊塞詩歌。
一、自然意象
大同邊塞詩以其宏闊高遠、豪邁灑脫的藝術特色嶄露頭角。這類詩歌同是敘述自然景觀和異地風情,卻不似山水詩的溫潤典雅、田園詩的閑適舒朗,它帶有強烈的軍事色彩,讓人讀起來心生澎湃之感,滿懷壯志之心。同是書寫山川、草木、云雨,卻與平靜祥和境遇時所寫不同。如虞世基《出塞》云“:窮秋塞草腓,塞外胡塵飛。征兵廣武至,侯騎陰山歸。”[2]51 孤秋塞外枯草萎,胡地塵沙漫天飛,將這樣的自然景物渲染上邊塞之色,多雄奇之感。有的詩人也將“草”寫成“邊草”,這是地域景物與自我情感的再度結合,使得詩歌中的自然意象更突顯地域性。除了邊草殘陽、朔風等。這些意象都不再僅僅是語詞的簡單組合, 而是帶有邊塞色彩的語匯,承載著詩人的情感。
大同邊塞詩中自然意象最為常見,這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有一定關系。大同地處黃土高原,受氣候影響,冬季干燥并時常伴有大風天氣。這里的景物相對于他處,有其獨特性。詩人選用當地的自然景物作為意象寫入詩中, 既選取了眼前可見之物,又寄托了自我情感,使得大同邊塞詩歌有了生活的氣息,更為靈動。而且自然景物本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與我們的情感聯系最為緊密, 所以自然意象最易為詩人所用。晚唐司空圖在《詩品·縝密》中論述過“意象”,這樣寫道:“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3]26 自然之美何等奇妙,是我們無法測透的,縝密的詩歌何嘗不是這樣呢,詩人若用自己的情感去觀照現實的事物,這樣形成的意象就會顯得縝密, 以此在詩歌中產生神奇的功效。同樣地,詩人們在選擇使用自然意象時,也是反復琢磨,苦心編纂,如此這樣才使得邊塞詩歌迸發出絢麗的色彩。
大同邊塞詩歌自然意象繁多,與詩人親身過經歷邊地生活也有關系。在那些寫邊塞詩歌的詩人中,有的也曾親自到過邊塞,他們經歷過邊塞環境的嚴峻,也看到過邊塞將士奮勇殺敵、視死如歸的戰斗場景。詩人們將這樣的自然風光刻畫在詩歌中,并借用抽象的意象來表達自我情感,寫成有獨特地域特色的邊塞詩歌。詩人們有寫送別親友征戰沙場的詩歌,如“寒風動地氣蒼茫,橫吹先悲出塞長。”(韋應物《送孫征赴云中》)這句詩用語蒼勁,寫出了塞外冷峻嚴寒的自然環境,意境空曠蒼茫, 讀者的視線也被遷入了當時清冷寒涼的環境中。環境雖然苦寒,但作者在尾句用期待孫征凱旋歸來作結,將詩歌激昂奮進的氣勢彰顯了出來。武元衡《度東陘嶺》通過描寫邊地的自然環境,襯托戰爭局勢的緊急。詩中寫道:等自然意象,具有塞外特色的意象還有黃沙、塞云、寒風、 “暮角云中戍,殘陽天際旗。更看飛白羽,朔馬在封陲。”
作者用“暮角”“殘陽”二詞點出時間,繪出塞外傍晚的風光,同時把自然意象“殘陽”與“天際旗”組合,將暮色中飄揚的戰旗刻畫在詩歌中,蒼涼之感隨之而生。飛傳的軍事文書、朔野嘶鳴的戰馬則直面地寫出了邊關的緊張局勢,也傳達出詩人對戍邊戰士苦守邊關、盡忠職守的關切之情。喻坦之《代北言懷》則寫出了大同邊地環境的惡劣。“路行沙不絕,風與雪兼來。”行路途中,風雪與沙俱來,在這樣的環境中,詩人所表達的羈旅之苦躍然紙上。大同邊塞詩中多寫秋冬之際,秋冬天氣日漸轉冷, 詩人們感知環境變化,情感也較易觸發。如薛道衡《出塞》有這樣的詩句,“秋高白露團,上將出長安。塵沙塞下暗,風月隴頭寒”這里的“塵沙”“風月”等意象所表現出的不再是平日的景物,而是一種塞下塵沙,隴頭風月。雖是邊塞之景,卻寫出一種清奇之風。“凜凜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虞世南《出塞》)塞外冰天雪地、邊風凌冽,戰士為報效國家奮勇出征。詩中“邊風”、“征馬”等詞語,邊塞色彩十足。正是這些自然意象在詩歌中的使用,使得大同邊塞詩中的景物更具張揚力。大同邊塞詩歌中除了自然意象的使用,也多提及地名,這些地名如自然景物一般,也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
二、地名意象
在大同邊塞詩歌中,詩人常會將當地的地名寫入詩歌中,一方面是因為實際存在這樣的地名,為詩人所見。另一方面是由于這些地名本身帶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聽 其名知其地。隨著詩人們在詩歌中不斷地選用這些地名 意象,它逐漸定格為固定的意象符號并寫入詩歌。比如“玉門關”“雁門關”“狼山”等邊地意象。在唐代詩人所寫的大同邊塞詩中,“云中”意象多次出現。唐置云 州,后改為云中,復又改為云州。云中作為重要的邊鎮據 點,在此發生了很多戰爭。故此“云中”多次作為地名意象出現在詩人的詩歌中。關于云中,詩人們寫了很多 的內容,其中有涉及與匈奴征戰的,有寫云中景致的,還 有抒寫戰亂給人民帶來苦難的等等。李益在其《塞下曲四首(其四)》中寫道:“為報如今都護雄,匈奴且莫下云 中。請書塞北陰山石,愿比燕然車騎功。”讀此詩,壯心志。“且莫”二字反映出立志保衛國家的信心,絕不讓匈奴有任何的可乘之機。李益除了有詩人這層身份,他也曾多 年親自在邊地作戰,熟悉邊地的作戰環境,他的邊塞詩歌 豪放灑脫,為人們所欣賞,這首詩歌更是為人所稱道。劉 灣《出塞曲》也曾提到與匈奴作戰。“汗馬牧秋月,疲卒 臥霜風。仍聞左賢王,更將圍云中。”詩句表達了戰士雖 正經歷著飲霜臥風、身疲力乏的殘酷環境,但聽到敵人侵 略邊地的消息,依然不會放棄征戰,也會立即進入戰斗狀態。在有大量戰爭之作的邊塞詩中,也不乏有抒懷憶舊之作。如薛奇童詩中所寫“云中小兒吹金管,向晚因風一川滿。塞北云高心已悲,城南木落腸堪斷。”(薛奇童《云中行》)憶當時,此地曾被作為北魏都城,有多少人艷羨當時的繁華,如今卻是荒蕪之地,蒼涼之景,已是另一番景色了,詩人不禁感嘆時光匆匆。施肩吾《云中道上作》也有類似的詩句。“羊馬群中覓人道,雁門關外絕人家。昔日聞有云中郡,今日無云空見沙。”昔日云中郡現今已風沙層積,再無往日的輝煌。除此之外,詩歌也有寫戰爭之苦。如常建《塞上曲》“翩翩云中使,來向太原卒。百戰苦不歸,刀頭怨秋月。塞云隨陣落,寒日傍城沒。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征人戰死寡妻痛哭,寡妻的聲聲哭訴表現了她對赴邊丈夫長年留居邊地的思念之情, 同時也寫出了作者對戰士久居塞外、戰死沙場的同情之意。張蠙《云朔逢山友》則寫的是久別朋友相見時的畫面。“會面卻生疑,居然似夢歸。塞深行客少,家遠識人稀。戰馬分旗牧,驚禽曳箭飛。將軍雖異禮,難便脫麻衣。” 塞外孤寂,少有人煙。漫游之時,遇到了昔日的老友,頗生感慨。這些詩歌中的“云中”意象不再只是一個地名, 它本身代表著那些曾經存在過的戰地故事,記載著邊關戰士無謂生死寫下的生命篇章。
在大同邊塞詩中除了提及云中意象,亦有平城意象。大同這片地域,在北魏時期稱為平城,在當時是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詩人們常用平城意象,也多是憶舊感懷之作。胡曾詩歌多評歷史人物和事件,有其獨到的見解,他所寫的《平城》就是憶舊之作。“漢帝西征踏虜城, 一朝圍解議和親。當時已有吹毛劍,何事無人殺奉秦。” 寫的是漢高祖當時征戰匈奴,卻被匈奴所圍困,最后接受建議同意“和親”之事,這首詩則傳達出作者對高祖當時決策的不平之義。李賀《平城下》中有這樣的詩句,“饑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別劍無玉花,海風斷鬢發。…… 惟愁裹尸歸,不惜倒戈死。”李賀有過戰地生活的體驗, 他曾到過雁門、平城之地,更能體會戰士們生活的艱苦。他的這首詩歌渲染出凄清荒涼的意境,寫出了邊疆戰士不畏生死,志在報國的情懷,但又有一絲哀傷、幽怨之情, 短短數筆,將人物內心的掙扎寫了出來。“云中”和“平城”是與邊地景物結合使用的情況下成為意象的,如果單出現在詩歌中,它僅指代地名,沒有邊塞色彩,亦不能夠稱之為地名意象。“任何作家與作品以至于任何文學現象,都產生于特定的地理環境,并且是特定時間里的地理環境。”[4] 正是這樣的環境鑄就了地名意象,并將其定格在詩歌中。地名意象是歷史精神的凝聚,地域性的延續。地名意象的使用展現了大同邊塞詩歌的歷史意蘊, 使詩歌表達更具有歷史性和深遠性。
三、樂器意象
大同位于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界處,地理位置優越,在魏晉南北朝時曾被鮮卑統治。唐朝時,這里依舊與突厥有征戰。陳子昂《送魏大從軍》寫道:“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悵別三河道,言追六郡雄。”他的另一首《感遇》中也有“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的詩句,都可見當時常與少數民族有交戰。同樣地,也正是由于這樣的社會環境,讓各族人民有了互相交流的契機,引進了很多種西域樂器,如羌笛、胡笳等。這些樂器被詩人寫入詩中,成為邊塞詩歌中的樂器意象, 豐富了詩歌的內容,促進了文化的多元化發展。
在大同邊塞詩歌中,也多處出現了羌笛、胡笳等樂器意象,這些樂器傳入后常被人們使用,尤其是出現在塞北邊地中。羌笛作為一種西域樂器,本身制作不難且易攜帶,深受戍邊將士的喜愛。戍邊生活單調,吹奏羌笛也就成了將士們抒發自我感情的途徑,羌笛逐漸成為了邊關的抒情寫意符號,常為詩人所用。羌笛本身帶著悲涼之色,吹出來的音低沉悠長,士兵們又常年遠離故土、戍守邊關,內心早已積淀了深深的鄉愁,將這樣的音樂與將士們深切的思鄉之情纏繞在一起,有一種蒼涼之感。詩人們常將有悲涼之音的羌笛寫入邊塞詩中,以此體現塞外將士的寂寥孤苦。如“寒沙迷騎跡,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李世民《飲馬長城窟》)這首詩歌,將塞外悠揚凄清的格調表現了出來,渲染出塞外孤寂無人,空闊遼遠的氛圍,通過書寫羌笛與金鉦,將聲音的悠長與環境的空曠結合在一起。李頎《塞下曲》用不多的文字寫了一位征人一生的故事。“少年學騎射,勇冠并州兒。直愛出身早,邊功沙漠垂。戎鞭腰下插,羌笛雪中吹。膂力今應盡,將軍猶未知。”少年時候就開始征戰殺場,年紀老邁無力奮戰時,領兵將軍還不知有這樣一位將士,寫出了邊關將士的感慨之情。這兩首詩歌中都使用了“羌笛”意象,將邊關那種空曠寂寥、凄清幽深的情境表現出來。
大同邊塞詩歌中除了常出現“羌笛”樂器意象外, 還有“胡笳”。胡笳的聲音空曠深遠,初聽深覺處于幽遠的環境中,它悲涼而又哀怨的聲音常會與征人思歸的情感融為一體,深沉而又纏綿。詩人們也常把胡笳作為邊塞之物寫入詩中,常把它與風、云、月等自然意象相搭配, 融合將士的邊塞生活,在詩歌中將這蒼涼之魂盡興表達。
如李頎《塞下曲》寫道:“金笳吹朔雪,鐵馬嘶云水。帳下飲葡萄,平生寸心是。”金笳意為金色的胡笳,也屬于“胡笳”意象的使用。這首詩歌中將胡笳的悠揚之音與朔北的風雪相應襯,給人一種蒼茫悲壯之感,將讀者帶入塞北風情之中。“帳下飲葡萄”則寫出了羽林子將士得勝歸來飲酒慶祝的豪邁情懷。“胡笳”意象將離愁別緒放入蒼涼悲壯的詩歌意境之中,在平淡的景物描寫下,增添了清麗的英雄氣概。如明余慶《從軍行》云:“風卷常山陣,笳喧細柳營。”普通的景物描寫,加上低鳴的胡笳聲,就呈現出了蒼涼悲壯、清遠深幽的意境美。
大同邊塞詩歌中“羌笛”和“胡笳”樂器意象的出現,讓詩歌更具有融合性,它將音樂與將士的自我情感以及邊關環境相互融匯,增強了詩歌本身的承載力,使得詩歌帶有邊塞詩的剛勁,又有音樂的柔美。詩人們將這幽怨的羌笛聲、低沉的胡笳聲通過文字的方式寫入詩歌中, 后世詩人讀來,頗有解鎖蒼涼樂音之感。
大同作為歷史上極其重要的軍事重鎮,自然環境雖苦寒,但卻有無數的戰士在這里守衛疆土,為國征戰。詩人們更是將這里獨特的地域文化寫進詩歌,傳揚后世,他們把邊塞詩中的自然意象、地名意象和樂器意象巧妙地相互搭配組合,更好地表達了自我的感情,寫出了對這篇土地的熱愛以及對無數奮戰沙場戰士的欽佩之意。大同邊塞詩歌的意象研究在邊塞詩歌的發展歷程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值得我們去思考和探究。
參考文獻:
[1] 傅三星注 . 大同邊塞詩注析 [M].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2]( 北宋 ) 蘇軾 . 蘇軾文集 [M]. 孫凡禮點校 . 北京 : 中華書局 ,1986.
[3]( 唐 ) 司空圖 . 詩品集解 [M]. 郭紹虞集解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63.
[4] 鄒建軍 , 黃亞芬 . 文學地理批評的十個關鍵詞 [J]. 安徽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2).
作者簡介:王杜鵑(1994—),女,漢族,山西省長治人,單位為青海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
(責任編輯: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