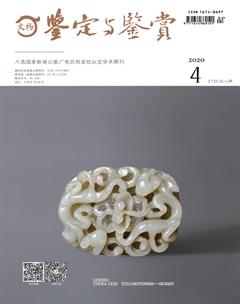云南省博物館館藏水月觀音像鑒賞
許悅



摘 要:1979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隊從大理崇圣寺主塔千尋塔中清理出133尊佛教造像,大理國銀背光漢白玉雕水月觀音像(簡稱水月觀音像)就是其中之一,現藏于云南省博物館。與同時清理發現的其他觀音造像相比,該像在選材、做工、藝術設計上顯示出獨特的審美價值和佛理禪意。
關鍵詞:水月觀音;大理國;云南佛教;造像藝術;禪宗
20世紀70年代末,云南省文物工作隊對大理崇圣寺三塔進行維修加固,在此過程中清理出一批文物,大理國銀背光漢白玉雕水月觀音像就是清理出的文物之一,現藏于云南省博物館。1961年3月4日,崇圣寺三塔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6—1979年,經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批準,云南省文物工作隊對三塔進行維修加固,同時實測和清理了藏于主塔千尋塔塔頂及塔基中的文物。這次清理共出土各類文物680余件,主要文物都出自塔頂,其中567件文物集中在塔剎中心柱基座內部。塔剎中心柱基座呈筒形,筒內存放一個八角形木制經幢,本次清理出土的佛教造像、塔模、刻文銅片、法器等文物,絕大多數都是在經幢內部及經幢上下方發現的。大理國銀背光漢白玉雕水月觀音像原始編號為TD下∶10,發掘者將其分式為VI式觀音像,這一式的觀音像特征為倚坐像。①原始的報告材料除了告訴我們這是本次清理出土的唯一一尊漢白玉質造像外,沒有再對這尊觀音像進行更多的描述。這件頗有人間趣味的觀音像藏著樸素的審美價值。
1 大理國銀背光漢白玉雕水月觀音像外形特征
TD下∶10觀音倚坐像后藏于云南省博物館,被定名為“大理國銀背光漢白玉雕水月觀音像”(圖1)②,是宋代文物。整尊觀音像通高16.2厘米,分為像、基座、背光三部分。像與基座都由漢白玉即大理石雕成,基座分上、下兩部分,上部與像為一體,根據館內相關資料介紹,下部與上部之間有一竹扦,將二者相連。背光為銀質,以一塊金屬片和它的邊角摳附在像的背后(圖2)。③可以看出工匠在雕鑿此觀音像時,基本保持了自唐代畫家周昉創造的水月觀音藝術樣式。觀音發髻高聳但不夸張,未戴佛冠,似用發帶盤發,顯得蓬松舒適;神態悠然自若,略帶喜悅之色;身貫瓔珞,披巾;觀音身材苗條,肩部線條頗有現當代時裝模特的構架感;觀音結游戲坐,左腿盤曲于身下,右腿支起,身體微向左倚,左手杵在座上支撐身體,右手持巾,自然放松地搭在支起的右腿膝蓋上。座的上部為一塊保持自然形態的石臺,下接山字形鏤空座,下部則呈壘石狀。像的身后緊貼純銀背光,其邊緣特別是頂部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被擠壓得變形了,但仍然可以看出其樣式并沒有照搬“周家樣”的圓月形,而是整體呈舟形火焰狀,內部飾曲折光太陽紋,周邊裝飾忍冬紋和火焰紋。背光非常生動地隨著觀音向左倚靠的身體而向左傾斜,使曲折太陽紋正照在觀音腦后,火焰紋的最高點正落在觀音發髻的頂端。
2 大理國銀背光漢白玉雕水月觀音像的審美價值
仔細對比崇圣寺同時出土的其他文物,這尊水月觀音像在千尋塔清理出的眾多佛教文物中,尤其在佛教造像中,它既不算保存最完好的一件,也不算做工和用料最精良的一件。保存方面,觀音的銀質背光中部有斷裂,頂部和邊緣因遭到擠壓而變形,以致火焰紋的尖端不再銳利飄逸,變得圓鈍向內彎折。值得注意的是,背光的變形并沒有影響觀音像整體的美感,向內摳折的火焰狀邊緣與下部的壘石狀基座,出人意料地構造出一種觀音身處鐘乳石洞窟中的畫面感。云南普遍分布著喀斯特地貌,鐘乳石洞窟是該地貌中具有代表性的地質景觀,這一歷史的巧合恰恰生動地反映出觀音在云南獨特的湖光山色中愉快修行、傳播佛法、普度眾生的形象。
用料方面,古代工匠使用漢白玉塑造了這尊體量不大的水月觀音。漢白玉就是純白色的大理石,是一種石灰石形態,內含閃光晶體,主要由碳酸鈣(CaCO3)、碳酸鎂(MgCO3)和二氧化硅(SiO2)組成,也包含少量氧化鋁(Al2O3)、氧化鐵(Fe2O3)等成分。云南大理是我國開采大理石最早的地區之一。大理石因盛產于大理而得名,大理也因生產大理石而增輝。大理的大理石主要有彩花、云灰和蒼白玉三種。①雕刻這尊水月觀音的漢白玉應是就地取材,珍貴程度遠不及金、銀、銅、水晶材質的其他造像。漢白玉的莫氏硬度為3,是一種易于雕刻的石材,蠟質光澤,非常適合用于表達人物溫潤細膩的肌理,但同時也很容易被劃損和腐蝕。這尊水月觀音之所以沒有普通漢白玉雕的光澤,是因為它所在的千尋塔塔頂在1925年的地震后,歷經50余年的雨水浸蝕,筒內十分潮濕②,加上云南酸性的土壤和空氣環境,于是瑩潤的光亮被消蝕了。不過這自然的變化卻造成了一種奇妙的因緣巧合。《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通過佛祖世尊之口,描述觀音是一位最貼近人民群眾,并幫助世人解決現實問題的菩薩。③這尊消逝了光澤的水月觀音像仿佛被大自然磨去了神性,恰好與它精美燦爛的銀質背光相對,將觀世音菩薩表現得正如佛經描述的一樣,用樸實無華的外表,向眾人揭示他背后如太陽火焰一般光明的大智慧。
做工方面,紋飾刻畫細膩的銀質背光與略顯潦草的漢白玉雕觀音本身形成了對比。特別是觀音的面部及服飾的細節,相較同期發現的同時代其他觀音造像都顯得相對模糊,甚至有人認為觀音看起來喜悅是因為他的嘴邊有兩撇小胡子。④這些對于觀音具體之“相”的爭論在佛家看來倒是毫無意義,所相非相,執著于表象之人只會越來越遠離真相。正如《金剛經》所說:“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⑤這尊水月觀音看似潦草的一些細節,恰恰耦合了佛家對于表象與真相之間的論述。我們在對這尊水月觀音進行審美時,如果糾結于觀音面貌、服飾上的具體細節,就會形成了一種“執著”,忽略了整尊觀音像所表現出的一種自然美感。塑造它的工匠似乎悟得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佛理智慧,將更多的雕塑功力用在了表現觀音的體態特征和雕塑整體結構的和諧上。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整尊觀音像看似歪斜,但不失構圖的平衡。這尊觀音像的畫面比例基本為9∶16,我們給畫面打上網格后(圖3),就能發現背光的最高點、觀音的發髻、鼻子、下巴、胸口及重心所在的左臀都在畫面中軸線的右側,它們都在同一條直線上,并且緊貼畫面中軸線,構成了畫面的穩定軸心。觀音的腰部為畫面的中心所在,其余所有觀音像的構成部分都均勻分布于畫面的四個部分當中,形成了合理的人體比例和平衡的畫面感。觀音的服飾雖然模糊,但巾帶的垂墜感被表現得恰如其分,不拘小節又不失嚴謹的服飾,使觀音整體上更顯簡潔質樸,突出了觀音“自在”的特質。古代工匠用簡樸的服飾結合塑像自然穩定的結構,為觀音像整體帶來了和諧感,也表達了佛家追求“真我”、忘卻“物我”的精神內涵。
另外,這尊水月觀音像銀質背光上太陽紋與火焰紋的組合,與重慶安岳石窟毗盧洞水月觀音像(圖4)背光上的裝飾圖案頗有相似之處,由此可以推測,云南佛教造像與成都平原地區的佛教造像在形式與風格上存在某種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