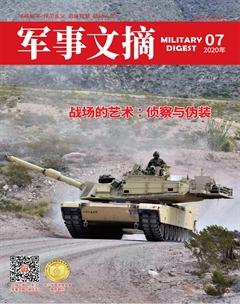薩多瓦戰役:德意志“內戰”
鴻漸
1866年的普奧戰爭是德國(普魯士)崛起過程中的3場戰事之一,和另外兩場戰爭不同,普魯士同奧地利的對抗堪稱德意志的“內戰”,決定著兩個中歐大國誰將成為德意志的主宰。在持續了7周時間的普奧戰爭中,最具決定性的戰斗發生在7月3日這一天,普魯士人稱此戰為科尼格拉茨戰役,奧地利人的表述則是薩多瓦戰役。
分進合擊
普魯士和丹麥在1864年打了一仗,獲勝的普魯士從后者手中攫取了兩個北方省份荷爾斯泰因和石勒蘇益格,此舉引發奧地利的強烈不滿,從而為兩年后的普奧戰爭埋下了導火索。普魯士的首相,杰出的外交家奧托·馮·俾斯麥對此早做準備,他同意大利人締結了盟約,規定一旦普魯士和奧地利發生戰爭,意大利有義務進攻奧地利的南部。

普魯士的威廉王儲

奧軍統帥本尼德克
普魯士軍隊同樣做好了準備。在另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普軍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的統籌下,普魯士軍隊在1866年春季充分動員,到了6月便主動采取了行動。除一部兵力攻擊奧地利的同盟漢諾威公國之外,普軍的主力向南直取奧地利的波西米亞地區。
毛奇的作戰意圖是三路并進,分進合擊。具體來說,赫爾瓦特·馮·比滕費爾德將軍的易北軍團通過薩克森指向西南,構成普軍右翼;腓特烈·卡爾親王的第1軍團在中路挺進;腓特烈·威廉王儲的第2軍團向東面進發,是為普軍左翼。
分路行動的目的是要實現快速進軍,爾后,這三路軍隊應該合力面對奧地利軍隊的主力,以實現“共同打擊”。毛奇的意圖是要搶在奧地利實施充分動員之前,便把足夠多的士兵投送到他們最應該去的地方。
作為拿破侖戰爭學說的崇拜者,毛奇倡導分道行軍,合力打擊,充分運用速度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如果一切照計劃進行,普魯士人將以近25萬人的兵力來執行一次大會戰:中路部隊將鎖定當面的奧地利人,而右翼的易北軍團和左翼的王儲軍團將取包抄之勢,從而實現一場現實意義上的“坎尼包圍戰”。
當然在敵前分道并進也有著顯而易見的風險,分散開來的三路部隊都要冒著遭到奧軍主力搶先攻擊的危險,也就是說普軍在“合擊”之前就有在“分進”過程中被各個擊破的可能,更不用說三路大軍之間還存在著聯絡與協調不便的情況。
毛奇并非沒有意識到這些危險,但他深信自己的總參謀部可以憑借出色的參謀工作來化解上述風險。同時,毛奇也一直注意在普魯士軍事體系中培養各級領兵主官的靈活性和主動性。這位總參謀長始終鼓勵下屬做“進攻性思考”,在總參謀部設定的框架范圍內做出自己的決定,毛奇的一句名言是,“沒有哪一項作戰計劃能夠在與敵人的第一次接觸中幸存下來。”
奧軍布陣
不過,分路進軍的危險性似乎超過了毛奇的預計。當普魯士部隊穿越幾處山口進入波西米亞地區時,他們在多處地段都提前遭遇了奧地利軍隊,并在6月的最后幾天里進行了一連串情況頗為混亂的遭遇戰。

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麥(左)
雖然普軍總體上取得了成功,奧地利軍隊從多處退卻,但是普魯士人隨后就失去了與敵人的接觸。到7月2日這一天,毛奇等人并不知道奧軍主力在哪里,而與此同時,三路分進的普魯士部隊仍未能完成會合。當時,右路易北軍團的部分兵力已經與中央的第1軍團建立了聯系,兩者合成了一支約有13.5萬人的部隊,但是左路王儲第2軍團的10萬大軍仍不知在什么地方前進著。
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如果統領著奧地利大軍的路德維希·馮·本尼德克將軍果斷地發動進攻,那么普奧戰爭的結果很可能會大不相同。匈牙利貴族本尼德克在奧軍中曾以果敢善戰而聞名,但他卻不是面對普魯士人時的理想帶兵將領。
1866年的本尼德克飽受悲觀主義和消極情緒的困擾,在受命出征之前,他就多次預言“災難降臨”,而且還上書建議他的皇帝弗朗西斯·約瑟夫一世“謀求和平”。有了這樣一個統帥,奧地利軍隊在開戰后過分謹慎的表現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本尼德克一直表現得很遲疑,更別提抓住主動進攻動的機會了。
當普魯士人兵分三路進軍時,本尼德克就拒絕了下屬發起進攻的建議,他的回應是要保留實力,“以絕對優勢擊敗入侵者”。然后在7月2日,當他對卡爾親王的第1軍團占有近2:1的兵力優勢時,他仍然選擇結陣固守,而把戰場的主動權拱手讓給了普魯士人。

普軍步兵沖擊奧軍炮兵陣地
奧地利大軍面朝西方,對著卡爾親王的軍隊布陣,本尼德克把軍隊放在了兩條河流之間的丘陵地帶,其西側是比斯特里茨河,東面是易北河。這不是一個理想的選擇,首先本尼德克對于普魯士王儲可能從北面發起的側翼進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其次,一旦戰況不利,易北河將成為阻礙奧軍撤離的障礙。客觀上來看,缺乏信心的本尼德克,已經給其對手提供了實現坎尼式包抄的可能性。
當然了,奧軍的陣地主體還是很強大的。奧地利人的戰線布設在連綿約9千米長的低矮山丘上,其間分布的樹林和村莊增強了奧軍固有的防御優勢。本尼德克還下令開挖了多處戰壕,并放倒樹木以構建障礙。
王儲對他的部將們下令,“看著遠處的那些大樹,那里就是奧地利人的右翼。鼓噪而進吧,讓卡爾知道我們在這里!”
這正是毛奇希望第2軍團做的事。也許當時普魯士王儲尚未完全理解毛奇計劃的大膽性,但是普軍所奉行的軍事學說使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假如無從判斷局勢,就主動發起進攻。
希勒·馮·加特林根將軍的第1近衛師首先投入戰斗,并且在下午13時沖上了霍倫諾韋斯高地。前面說過,這是一處對奧軍側翼來說至關重要的地方,本尼德克選擇無視這里,現在普魯士人控制了高地。
奪取高地后,第1近衛師又居高臨下地沖擊附近的楚爾姆村,同奧軍在那里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一名普魯士的戰地通訊員寫道:“這是一個可怕的時刻。勇士們看到了自己的優勢,立即沖向楚爾姆的中心地帶,奧地利人的抵抗徒勞無功,他們跑向后方,希望得到大炮的幫助。我們的軍團從四面八方而來,頭盔閃閃發光,炮隊迅速上前,開始轟擊斜坡上的奧地利主陣地和預備隊。四下望去,滿眼都是我們的人。”
政治成果
王儲軍團的加入確實成了薩多瓦之戰的關鍵點。在首次接到相關報告之后的兩個小時里,本尼德克都幾乎沒有采取什么行動去增強受到威脅的側翼,這讓他的軍隊陷入了他曾經預言的“災難降臨”狀態。
直到楚爾姆村以及鄰近的羅斯貝里茨村相繼陷落,本尼德克這才想到要在側翼發起反擊,以免普魯士人徹底沖垮奧軍的陣形。于是在一番猛烈的炮擊之后,奧地利第6軍的步兵發動了規模浩大的反攻,然而這支部隊遭受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卻沒能取得進展。
本尼德克隨后派出第3軍發起第2次進攻,他們同樣也未能打退普魯士第1近衛師在楚爾姆和羅斯貝里茨的抵抗。最后,本尼德克向自己的右翼派出了最后一支預備隊第1軍,希望這支生力軍能夠沖垮威脅著自己的普魯士人。

雙方騎兵在戰場上廝殺的場面
奧地利步兵在反擊中保持著緊密的隊形,這讓他們在普魯士近衛軍針槍的齊射下死傷相繼。第1軍是在奧軍反擊中表現得最英勇的部隊,也是反擊各部中損失最大的,整個奧地利軍隊在薩多瓦之役中傷亡人數的1/4都來自第1軍。
但即便是這種程度的努力也無法打退普軍。普魯士第1近衛師打得很艱難,同樣損失很大,但是王儲軍團的后續部隊正不斷上前,這就鞏固了近衛軍所奪取的陣地。在得知身后出現了友軍之后,第1近衛師英勇的加特林根將軍號召部下發動反擊,就在那一刻,他被一片飛來的炮彈彈片殺死了。
戰役的進程已不可逆轉,普魯士人在奧軍側面施加的攻擊分量變得越來越重。下午16時30分,本尼德克確信大勢已去,現在他的首要任務不再是戰勝敵人,而是在為時已晚之前撤出他的主力。他留下部分炮隊繼續轟擊對手,同時派遣奧地利和匈牙利騎兵發起沖鋒,以此來掩護大規模的步兵撤退。
面對著以針槍為主的普魯士火網,全歐洲40個一流的騎兵中隊發了一系列自殺式的沖鋒,騎士們損失慘重,不過有效延緩了普魯士大軍的行動。這是值得奧地利軍隊自豪的時刻:奧地利后衛部隊的技巧和勇氣,確保了大多數部隊得以從戰場上離開,他們雖然打輸了,但是薩多瓦畢竟沒有成為毛奇的坎尼。
薩多瓦戰役以普軍的勝利而告終。根據戰役結束后的清點,普魯士軍隊損失了9000余人,而奧軍則折損了4.3萬名士兵,其中一半是傷亡人員,另一半則成了普軍的俘虜。
薩多瓦之戰后,奧軍仍保有相當數量的部隊,具備同普軍再戰的實力,但是奧地利上下已經很少有人對第二次戰役的結果抱有信心了。而在精明的普魯士統治者看來,他們也不想要第二場戰役。
不少欣喜若狂的普軍將領主張趁勝追擊,但是眼光長遠的俾斯麥主張克制。他知道,假如徹底擊垮奧地利,俄國、法國和英國都不會坐視中歐的力量天平失去平衡,如果多國干涉,普魯士并不具備與之對抗的能力。
于是普魯士人巧妙地將薩多瓦的軍事勝利轉化為政治成果:奧地利承認失敗,就此讓出了在德意志世界的領導地位。1866年7月3日清晨,普魯士還是一個歐洲二流國家,而到這天的日落時分,她已經躍居為一等強國,以普魯士為主導的德意志就此強勢崛起。
責任編輯:張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