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證和參與的大運河文化帶蘇州段建設
施曉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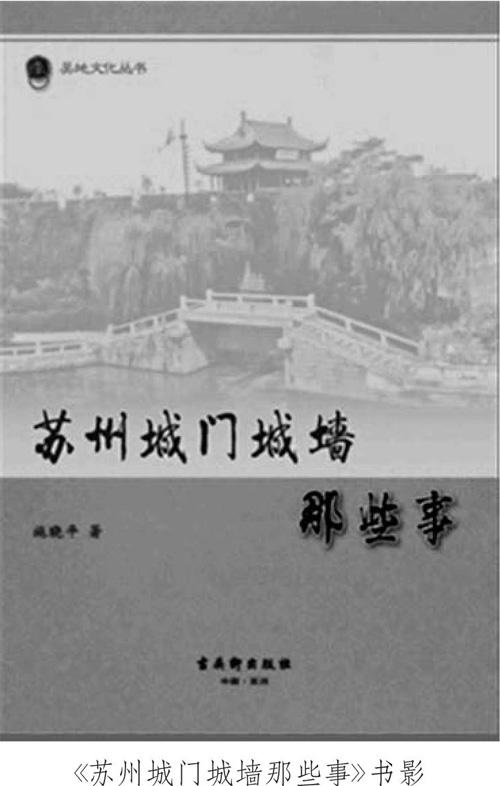
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正在如火如荼推進,蘇州段也不例外。作為一個在寶帶橋附近出生、喝運河水長大、長期和大運河打交道的蘇州人,我見證了40多年來大運河蘇州段的發展變化,并參與了大運河文化帶蘇州段建設的報道和文化挖掘工作。
見識運河
1972年我生于蘇州葑門外小集鎮郭巷。這里離葑門直線距離只有6公里,相傳系蘇州外城(郭)所在地,因此得名“郭巷”。集鎮一帶是典型的江南水鄉,東南面有尹山湖,東北面、北面有獨墅湖、黃天蕩,西面約1.5公里處就是大運河,運河水通過集鎮北面的斜港河(東西走向)、東港河(南北走向)、西柵口港(東西走向),流到我家老屋后面的郭巷街河里,再向東注入尹山湖。
斜港河向西穿過大運河,就是舉世聞名的寶帶橋,以及因孔子弟子澹臺滅明而得名的澹臺湖,再向西則是東太湖湖灣。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東太湖湖灣水域寬闊,大量運河水通過這里,或通過胥江、吳淞江等江河流入大運河。因此,斜港河送至郭巷集鎮的大運河水,實實在在流淌著太湖水的“基因”。
我小時候,郭巷街河水體清澈,魚蝦眾多,從一個側面見證了當時太湖和大運河的水質之佳。此外,每年汛期,郭巷街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清代石拱橋泰安橋橋洞段,從東向西的手搖船往往過不了橋洞,盡管船夫們已經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由此可見當時的大運河水量之充沛。
受大運河寬闊的水面阻隔等因素影響,郭巷集鎮一直到1983年3月15日才通上公路、公交。在此之前,郭巷的對外交通以水路為主,出行基本靠坐船,連辦理婚喪喜事也是如此。要坐公交車的話,必須向西行走到一個叫“紅旗渡口”的地方,擺渡到運河西岸十蘇王公路公交站點(位于寶帶橋南500余米處)搭乘,返回時亦是如此。郭巷集鎮通公路后,由于到蘇州城需要向南繞道尹山橋,多走約3公里路,因此許多騎自行車去蘇州城里的郭巷人,仍喜歡選擇到紅旗渡口擺渡。
我還清楚地記得,十來歲時的一個夏天,祖父帶我到蘇州城里白相(蘇州方言“玩”的意思),晚上去觀前一家影院看了場電影,散場的時候已經沒有到紅旗渡口的公交車了。這時祖父恰好碰到一個熟人,是在電影院附近一家單位看門的。祖父跟熟人說明情況后,熟人將我們帶到他的宿舍,安排住下。當夜因為蚊子叮咬,我和祖父沒睡好,凌晨3點多就迷迷糊糊起身了。告辭熟人后,我們才發現,這個時間點也是沒有到紅旗渡口的公交車的。但我們不想白白浪費時間,于是就摸黑行走。走了一個多小時,到了寶帶橋北端,這時天已經放亮。我一見宛如臥波長虹的寶帶橋就興奮起來,想在上面走走,但同時又想知道這座古橋一共有多少個孔,就央祖父走西側的十蘇王公路橋,邊走邊點橋洞,我自己則直接在寶帶橋上走過。會合時祖父告訴我,古橋一共有53個橋孔,我這才第一次知道了這座舉世聞名的橋梁的“家底”。
1987年9月至1990年6月,我在大運河以西10余公里處的木瀆中學求學,平時住校,休息日則騎自行車回家,紅旗渡口、寶帶橋、十蘇王公路都是我的必經之處。這段經歷,讓我多次飽覽了寶帶橋一帶大運河的優美風景,看到了十蘇王公路兩旁成蔭的梧桐樹、榆樹,也看到了波浪滾滾的大運河水。當然,由于當時沿河建有化工廠,加上來往船只眾多,螺旋槳不斷卷起水底泥沙,大運河的水質已經不盡如人意了。
就在木瀆中學求學期間,蘇州開始了城南運河的改道工程。根據《吳中區志(1988—2005)》記載,改道工程讓大運河從蘇州古城西南面的橫塘鎮大慶橋直接向南,到石湖北側后向東直達寶帶橋,再向南回到原有航道,全長9.3公里。這樣,大運河就繞過了蘇州古城區,減少了輪船噪音對護城河兩側居民的影響。整個工程歷時5年有余,1992年6月25日竣工,同年7月16日通過驗收并正式通航。工程同時對十蘇王公路改線7.342公里,1991年10月8日十蘇王公路蘇州城南改道段暨長橋正式通車,寶帶橋北側河口同時破土開壩,至此,蘇州城區至郭巷之間的來往需要向西繞道東吳塔,圈子兜得更大了。直到1996年9月,大運河東岸吳東路通車,這種現象才得以改變。
1999年5月我成家后,就住到了吳中區城區,但單位在蘇州工業園區一所中學,上班時仍要經過大運河原有河道旁。記得有一天大清早,我路過運河西側某化工廠時,看到工廠通過閘門向外排放污水,導致運河西半側河水和東半側河水顏色一灰一白,像兩塊不同顏色的布南北向并排延伸,空氣中則彌漫著一股刺鼻的酸味。
解讀運河
我和大運河蘇州段的第二段因緣始于2002年。當時,我已成為蘇州日報報業集團《城市商報》的一名記者。因為工作需要,我對運河蘇州段進入了“了解她、解讀她、傳播她”的新階段。
那時候,蘇州啟動了環古城風貌保護工程。這是蘇州市第九次黨代會確定的“十五”期間中心城市重點建設的十大工程之一,也是一項集城市交通、防洪、生態綠化、景觀、旅游等功能為一體的綜合性工程,全長約17公里,基本沿護城河及滅渡橋至北干河之間的大運河故道展開。從現在的情況看,此舉完全可以看作是國家啟動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之前,蘇州以高度的文化自覺開展的一個先行先試行動。
環古城風貌保護工程于2002年5月24日正式啟動,分三期實施。到2005年12月,經過一、二期的建設,蘇州已基本形成一條沿護城河兩側各100米、凸顯歷史文化底蘊、展示園林和東方水城特色的景觀帶,“覓渡攬月”“金門流輝”“舊城堞影”“耦園櫓聲”“煙霞浩渺”等48個景點布局其間,以水系和城墻體系串接,構筑起以“金閶十里、盤門水城”為主的西部功能區、“吳門商旅、都市驛站”為主的北部功能區、“城市山林、枕河人家”為主的東部和南部功能區。如果把古城比作蘇州的頭部,那么,經過整治而變得一年四季常綠的環古城地區,就是繞在頭部的一條綠色項鏈。護城河上的巍巍橋梁、岸邊的斑駁城墻經過整修,顯得傳統而典雅,讓這里文化味十足。從此,環古城地區成為蘇州人漫步休閑的自然生態圈,也成為蘇州古城又一張景觀名片。環古城風貌保護帶三期工程于2011年1月起進場施工,當年完工。
配合環古城風貌帶工程建設,蘇州文物部門2004年還開展了閶門遺址搶救性考古調查,發現了一批漢代遺物,既為重修閶門提供了依據,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蘇州古城歷史的悠久。
凡此種種,我都進行了持續的關注和報道。
這期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私人紀念品埋入重修城墻一事。那是2004年初,姑胥橋東北堍一段城墻開始修復。我報道這一消息后,報社總編輯突發奇想:能否埋一些紀念品在這段城墻內,讓后人見證這段歷史?為此,我查閱了資料,發現把紀念品埋入地下、留給后人的做法,國內外都有先例。于是,《城市商報》4月18日以《讓后人見證古城滄桑巨變? 重修城墻能否埋入私人紀念品》進行了報道,引起當時蘇州市領導的高度重視,見報當天(星期日)就得到批示:“可批準有關方面研究”,并提出了有關紀念方式的設想。5月初,環古城風貌保護工程指揮部對“重修城墻埋入紀念品”一事進行了討論。考慮到其他紀念品不易保存,而將創意刻入城磚則可較好解決這一問題,也更有紀念意義,指揮部決定遴選55句有創意的話刻在城磚上,鋪砌在姑胥橋東北側或閶門段的城墻上。之所以遴選55句,主要是因為當年蘇州正好解放55周年。
創意語句通過《城市商報》進行了征集。入選的句子中,我記得最牢的是蘇州市民族民間文化保護辦公室(后改名為市非遺辦)主任龔平的一句:“親愛的未來市民,相信蘇州將來以加好。”這段文字下面還用國際音標進行了注音。“以加好”是吳語,意思是“更加好”,所以一些專家稱贊:這句話不但可幫助未來市民用古老的吳儂軟語讀出先輩的祝福,也可為未來學者提供一個研究吳文化發展的實例。
2012年3月31日,我從《城市商報》轉崗到《蘇州日報》。從此,我對大運河蘇州段的解讀就更多了。
此前的2008年3月,大運河申遺工作已作為國家戰略正式啟動。換崗第一天,我就接到任務,采訪來蘇考察大運河申遺準備情況的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一行。勵部長一行先后考察了山塘街、虎丘、盤門、寶帶橋、東山鎮陸巷古村等文物推薦申報點,對蘇州的準備工作表示滿意,并接受了我的獨家采訪。
2012年9月28日,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資深顧問、世界內河遺址首席專家米歇爾·科特也來考察大運河蘇州段申遺工作。由于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業咨詢機構,也是古跡遺址保護和修復領域唯一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負責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名單的審定和評估,因此,此次專家考察對大運河蘇州段申遺乃至中國大運河申遺都具有重要意義。對此,我又進行了報道。
配合申遺工作,我還以主力記者的身份,參與了2014年6月11日至22日《蘇州日報》開展的“一條河·一座城”行走蘇州運河遺產系列報道。整組報道既涉及蘇州大運河歷史沿革、變遷、蘇州對大運河遺產的保護,還有列入申遺名錄的蘇州段運河遺產情況,最后以《中國大運河入列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蘇州古城申遺夢圓》終結,前后共10篇稿子,幾乎每天一篇。稿件除刊登在《蘇州日報》上,還提前在蘇州日報APP、官方微博、微信、蘇州日報文藝部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上發布,滿足了不同年齡、不同閱讀方式讀者的需求,為申遺工作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
這組采訪報道節奏快、強度大,而且碰到了不少困難,但我們樂此不疲,也收獲頗豐。比如寫歷史上的虎丘塔時,我們多方尋找,找到了家住虎丘山下、時年95歲老人郁文劍、81歲老人夏友良,得知他們小時候去虎丘塔時,塔身外面裂縫和窟窿隨處可見,塔頂還出現了大窟窿,嚇得他們不但不敢爬上去,就連靠近塔身都很緊張;寫寶帶橋時,因周邊村民已經動遷,我們在當地社區干部的帶領下,趕了好幾公里路,到紅莊新村才找到了88歲老人馬永昌,采訪到了日軍當年在橋上開汽車的內容;在寫吳江古纖道的時候,我們又多方打聽,終于在吳江區平望鎮梅堰三官橋村找到了老纖夫朱根林,聽他講述拉纖情況,還拍下了他模擬的拉纖動作……這些鮮活的資料,讓我們的報道吸引了眾多讀者。
蘇州納入大運河遺產的范圍,包括山塘河、上塘河、胥江、環古城河四條運河故道,山塘歷史文化街區、虎丘云巖寺塔、平江歷史文化街區、全晉會館四個運河相關遺產和盤門、寶帶橋、吳江古纖道三個運河水工遺存,遺產區面積6.42平方公里,緩沖區面積6.75平方公里,比原先設定的蘇州古城申遺范圍還大。因此,大運河申遺的成功,也意味著蘇州古城申遺的成功。這是蘇州的智慧,也是上上下下不懈努力的結果。為幫助人們了解這一情況,2014年7月4日,我又以《大運河蘇州段入遺比當初古城申遺范圍還大》為題,在《蘇州日報》“文化訪談”專版進行了闡述。
與此同時,我還受邀在蘇州圖書館的“蘇州大講壇”上主講蘇州城門城墻歷史、故事,每月一次,連續9次。因為蘇州城門城墻和護城河密不可分,所以我講課中涉及了許多大運河的內容。事后,我在講稿的基礎上進行充實、調整、補充,形成書稿,于2015年3月出版個人首部著作——《蘇州城門城墻那些事》。
參建運河
2017年5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打造展示中華文明的金名片——關于建設大運河文化帶的若干思考》的報告中作出重要批示:“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這一批示,為推進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指明了方向。
此后,全國相關地區開始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我則被蘇州市吳中區文聯引進,從事文藝交流、管理等工作。從此,我從原先的“販賣式”解讀、宣傳大運河蘇州段,轉向“自產式”參與大運河文化帶蘇州段的建設,開啟了我和運河的第三段因緣。期間,我深入挖掘大運河蘇州段沿線鮮為人知的歷史文化資源,并參與規劃方案編制,積極提交政協提案……這些舉措雖然不是直接參加建筑工程,卻是推進建筑工程的基礎,也助推了大運河文化帶蘇州段靈魂的塑造。
其中,2017—2018年我承接了蘇州高新區《文蘊高新》系列叢書之一《運河流芳》的撰寫任務。那段時間,我利用晚上和休息日,對大運河蘇州高新區段的歷史、文化進行了系統梳理,包括滸墅關八景和蠶桑文化、楓橋街道的賀九嶺和寒山嶺、橫塘的驛站和亭子橋、玉雕高手陸子岡、跨越三個世紀的人瑞李阿大等,并多次前往實地踏訪、采訪知情人士,多方征集老照片,最終勝利完成撰稿任務。2019年,在蘇州市第十二屆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評選活動中,《文蘊高新》系列叢書成功入選。
2019年,我又根據吳中區文聯主席團要求,擔綱大運河文化帶吳中段歷史人文特輯《吳運流長》的編撰工作。吳中區委宣傳部、區大運辦對此書高度關注,將其列入區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五個一”文化活動(“五個一”中的“一本書”)。
由于大運河吳中段的文字記錄相對較少,名門望族外遷較多、后人難以尋找,而且動遷啟動早,特輯的撰稿工作面臨很大困難。幸而經過召開座談會、區作協微信群發布信息、吳地歷史文化研究會會議發布信息、約請文史作家等途徑,最終有10余位作者(包括本人)參與到編撰工作中來。大家深入實地反復調查,在寶帶橋畔尋覓詩情,在大運河邊采擷珍聞,并從浩如煙海的書籍中尋找線索,加上以往的積累,辛勤筆耕、反復修改,最終如期交出了文稿、端出了特輯。此書在2020年元旦的“新年走大運”第三屆大運河江蘇段沿線八城新年行走活動(蘇州地區活動)上首發。
我還受邀參與了《大運河文化帶(吳中段)規劃設計》的編制。2019年初,規劃方案在向吳中區領導匯報時,區領導要求加強大運河吳中段的資源挖掘、特色挖掘,并建議設計人員找我“取經”。于是,我義務參與到設計方案的編制中,為設計人員提供了不少獨家資料和建議。隨后,方案進行了調整、完善,目前已基本定稿,將作為指導性規劃,指導全區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工作。
2020年初的吳中區兩會上,我作為區政協委員,又在區政協領導們的指導下,以《大運河文化帶(吳中段)后續建設和發展的建議》為題,參加大會聯組發言。由于內容較多,規定發言10分鐘,我實際發言15分鐘,但會后多位領導、委員說,這個發言是全場發言最精彩的一個。
鑒于大運河文化帶吳中段核心監控區位于吳中經濟開發區、吳中高新區,開發和保護之間的矛盾較為突出,為了將更多歷史文化信息留存給后人,為大運河文化帶吳中段建設添磚加瓦,2020年兩會期間,我還提交了《關于加強蠡墅、郭巷集鎮歷史遺存保護的建議》,最近被確定為2020年吳中區政協領導督辦重點提案。
如今,每次經過寶帶橋,看著水質越來越好、環境越來越美的大運河,我就會想到,流淌不息的大運河哺育了我,也給我提供了學習和施展身手的舞臺,我應該感恩大運河、回報大運河。
(責任編輯:巫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