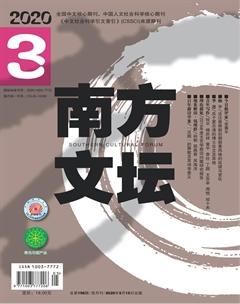錢理群貴州時期的學術道路考察

一
錢理群在自述中說:“我的生命只有兩個空間,這就是貴州和北京大學,我和這兩個空間建立了血肉般的聯系。”①這為自己思想成長劃了時間段,也可以于此窺見其精神變遷之跡。貴州時期(1960—1978)和北京大學時期(1978—2002)纏繞著他復雜的情感和認知形態,也多少折射了一代知識人復雜的情感體驗。前一階段是精神突圍時期,也正是這一階段的探索,為后一階段的學術道路奠定了根基。在貴州時期獨特的革命經歷、動蕩的民間思想村落歲月中產生了錢理群極其充滿個人創見與時代痕跡的思想言說,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錢理群的魯迅論——這不僅是“錢理群魯迅”的起點,而且也是錢理群學術生命的一段真實的寫照。
1960年,錢理群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被分配到貴州安順衛生學校教書。因了其家庭背景非常復雜,很快遭遇種種挫折。1960—1970年代持續不斷的運動為錢理群提供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他在那時經歷了命運的大起大落。外在于自己的風潮與自己的期許差異很大,他的命運隨著政治運動的走向而改變:從“右派”、“反革命”到“革命群眾”而獲得“解放”;但隨之多有受挫,被逐出革命隊伍。多年后,錢理群總結自己的經驗道:“造反,在某種意義上,不就是這樣的‘卑怯的反抗嗎?我們曾受到壓抑,心中郁積著‘怨憤,‘文革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泄的機會,但我們這‘萬丈怒火,‘除了弱草之外,又真的‘燒掉了什么?問題在于,在底層百姓和知識分子受到‘強者的蹂躪而產生的‘怨憤里,除了‘憤怒,還蘊含著‘怨毒,前者可以引發出光明正大的反抗,而后者卻是一股邪氣,很容易被利用,引發出瘋狂的破壞。因此,魯迅提醒‘點火的青年:‘對于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余,還需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勵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需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②他從現實中感受到魯迅思想的深層隱含,而在象牙塔里的讀書人是不易意識到這些問題的。
對于錢理群在三十年后的回憶、反思,無法斷定他在1970年代是否具有魯迅那樣對社會、歷史理性的認識,但當時他的確因為“怨憤”“憤怒”“怨毒”而反抗,自覺參與了群眾造反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錢理群相對認同當時的造反精神。在這場政治運動中,他是從自身所處地位以及命運轉變的角度來理解革命,并形成了自己的革命史觀。錢理群對革命者身份的執著以及受到打擊、壓制的憤怒,對體制造成的“新的社會歧視和不平等”③的抵觸促使其積極擁護革命,參加各種運動。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確實是有群眾基礎的”——是1949年之后社會矛盾、怨憤情緒的大爆發,因而存在著歷史的合理性。對于錢理群這樣“具備雙重身份、不可靠的人”④,參加造反運動不僅意味著可以提高政治上的地位,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而且也是遵從革命領袖的號召反抗體制,受到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驅動。錢理群等一代青年的歷史宿命就是“在自己的身份認同中突顯革命認同……在各自個體的身份結構體系(如民族、文化、職業等)中,他們所突顯的是政治認同,在整個社會的身份結構體系中,所突顯的又是顯然屬于政治認同的革命認同,而在革命者的身份譜系之中,又以對黨的認同最為急切與強烈”⑤。對于革命的認同,既是意識形態的內在要求,也關乎個人身份、地位以及前途命運。他的許多看法,在那時候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歷史卻和他開了個玩笑,三起三落之后依舊無法成為革命者隊伍中的一員,只能作為革命之外的邊緣者、旁觀者。在他的政治激情消退之際,轉而開始從文化思想角度思考中國的歷史、前景以及自我的責任、命運。作為在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大學生,他是名副其實的“毛澤東時代”培養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對于革命有著由身份認同所帶來“堅實的內在同一性”⑥。對于自己來到貴州安順小城的命運,他真心服膺于最高領導人的指示,決心扎根農村從事思想文化建設。錢理群認為知青下鄉運動是“一次移民,既減輕城市負擔,又把城市文化帶到農村去”,“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形成的一種‘把農村作為社會與文化創造力的真正源泉。才是革命勝利后的正確發展路線的核心的民粹主義理念”⑦,因而,“知青下鄉運動達到了毛澤東的部分目的,既消弭了年輕人繼續造反的危險,又確實通過知青以及同時下放的知識分子,將現代文化傳播到了農村。……‘文革完全打亂了原來文化、教育體系中,城鄉隔絕、上下隔絕的等級結構,在向社會底層傳送教育、文化資源上,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內含的矛盾與問題,都很值得研究。”
這段錢理群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建立在對毛澤東思想相當程度上的認同基礎之上,也正是這種人民史觀使得錢理群找到了扎根安順的思想和心理依據: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經歷了‘文革的狂熱之后,終于把自己的腳落實到中國這塊土地上,他們獲得了真實的中國體驗,真正了解到中國的國情”⑧。因而“建立了他們和底層人民的一種深刻的精神聯系和感情的聯系”。這也使得“他們由此出發重新思考中國的問題,思考中國的改革,就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他們的思想就跟前期造反派有了不同,“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就達到了新的深度”⑨。身處民間的體驗與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培養了知青一代追求與底層相接觸,立足于民間,思考中國本土歷史與問題的特點,這種立場決定了他們的思想、文化基點。在遠離北京的地方,他開始體會到中國社會的一些核心問題,對于存在、本質、歷史與個體等問題,有了感性的體驗,從這些感性體驗出發,他開始尋覓自我的意義和社會發展的規律。那些現象之謎深深地吸引著他。一種在主流之外打量主流的思維方式,漸漸呈現出來。
二
貴州時期的錢理群“感受到的更是物質與精神的雙重饑餓”⑩。不過那時候在他的腦海里,精神危機、信仰危機遠比物質的匱乏更為嚴重。處于時代中心的邊緣、外圍,雖然在一段時間內被“解放”,加入革命群眾組織,但隨之被隊伍所驅逐。政治熱情的減退所帶來的是對社會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國家、民族、個人前途命運的思考。錢理群精神結構中的革命意識形態和共產主義理念建立在對革命、政黨、民族國家的高度認同的基礎之上,即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共產主義的前途等同起來。所以,錢理群對民族、國家、革命等宏大命題的探討帶有對個人命運的思索的意味。換言之,他關于個人命運的思索,是在民族、國家、革命等宏大命題的框架下進行的。貴州時期(1960—1978)是錢理群的“學術準備期”11,正是通過民間思想村落時期的探索,錢理群對革命意識形態進行了反思,形成了批判性、反思性、否定性的思維方式與精神氣質。所以錢理群在思想村落經歷的思想操練與道路探索對其精神結構的形塑有著深遠的影響。
考察1960—1970年代錢理群的思想軌跡,需要關注錢理群與民間思想村落的關系。1950年代以來政治運動此起彼伏,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知識分子、學生離開了賴以存在的城市、學校等單位,來到農村等偏遠地區插隊。通常來說這個時期知識分子已經遠離了從事專門學術研究、自由思考與表達的平臺,成為“五七”體制12外的“零余者”和“落難者”。“零余者”意味著開始脫離嚴密的“單位”體制的束縛,擁有一定思想、活動的自由和空間。“落難者”身份則促使其產生了反思、批判意識的動機。在從城市向農村遷移的過程中,產生了一批民間思想者,延續著尚有微弱氣息的民族文明的血脈。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曾經響應號召的紅衛兵,充斥著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革命激情與青春想象,起初的春風得意與因“上山下鄉”而到農村插隊的落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落難者的遭遇以及林彪事件的沖擊使得他們率先沖出既定的思維之網,開始進行獨立的思考與探索。體制外的身份和遠離權力中心的處境毫無疑問提供了學習與思考的絕佳機遇,而年輕知識者的相對集中也為思考與探索提供了便利,這些以農村的青年人為主體的民間思想者形成了松散的知識者的集合,構成了可以稱得上是自發組成的文人社團。
錢理群所在的貴州是民間思想村落的重鎮,按照朱學勤的提法,這群人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失蹤者”13。民間思想村落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初,林彪事件發生后輿論界出現的變化,為村落的形成提供了契機。民間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產物,其自身的非官方色彩與聚集功能突破了多年以來對民間自由結社的限制,在某種程度上銜接了自五四以來自由結社、獨立思考的傳統。“村落”雖然是屬于文學社團性質的民間組織,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地下的民間政治團體:不僅僅是依靠文學來滿足精神的饑渴,而且尋求與探索著國家與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民間村落的形成既是彼時思想界集體失聲后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自覺,也是在特定歷史時期所形成的文化現象。根據錢理群的敘述,1970年代貴州安順地區以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民間思想村落:“并不是很嚴密的組織,就是一群朋友有同樣的想法聚集在一起,讀書、討論問題、交換思想筆記、寫信、記日記,偶爾也有刻寫油印通訊的,還有就是互相訪問,當時叫‘串聯,從一個村到一個村,還有跨省的交流,假期間回城時就有更多的交談、辯論。”14這個群體其實是當時中國大陸眾多民間思想村落的一個范例,由此可預見彼時中國大陸思想界的走向。正是在社會、歷史轉變的關鍵時刻,一群“準知識分子”登上了歷史舞臺。總體而言這一代知識青年的精神狀況大體上處于一種蒙昧狀態:
和共和國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從小被灌輸了滿腦子似懂非懂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觀念、理論。“文革”中,他們中很多人變得語言粗暴,行為乖張,喪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們普遍缺乏個性,完全被一統的極左話語所包圍和左右,成為被政治野心家們操縱的傀儡。15
民間思想村落群體的探索正是從擺脫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開始,通過閱讀各類書籍而開始自己獨立的思考。錢理群在“村落”歲月所接觸到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以及左翼方面的理論、文學書籍。他后來回憶了當初村落成員的閱讀情況:
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以及我們所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著作,熱烈的討論著中國與世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事實上,我們正在經歷著與當年的魯迅類似的精神探索的歷程;有意思的是,我們所得出的結論,與魯迅也是類似的:我們經過自己獨立思考與選擇,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16
錢理群等“村落”民間思想者的思想路徑是“沿著馬克思、列寧的思想蹤跡,追溯從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歷史,由此進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視域”“進而深入下去,進一步接觸到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布哈林、盧森堡……”以及“啟蒙時代以來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思潮”17。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以及毛澤東、魯迅著作的閱讀、研究,精神的天地異常開闊起來,這些對他早年學養的積累以及批判、反思意識的覺醒具有重要作用。錢理群認為他的“思想與學術研究的理論基礎與方法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所奠定的”18。通過閱讀馬列原典,錢理群與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一種緊密的關聯,進而形成了自己批判、反思的思想能力。他在閱讀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時對于絕對真理與最終絕對狀態的反思,對于最終、絕對、神圣觀念的否定,從辯證哲學中學到了徹底的批判精神;通過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堅定了對個體精神自由的信念;而通過閱讀列寧晚期著作,確立了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信仰,深化了對專政/專制,民主集中/民族集權等概念的認識;“青年毛澤東”以及魯迅也是他的主要思想來源,錢理群在《魯迅與毛澤東》一文中詳細地論述了魯迅同毛澤東之間的思想關聯。最為重要的是錢理群對魯迅思想資源的汲取:“于是,我就在這樣一個荒誕的瘋狂的時代,處于一種屈辱的地位,以及一個混亂的、迷惑的、扭曲的心靈,與我的兩個‘精神之父——毛澤東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了。”“當時我感到是一次從未有過的思想大解放,被‘贖罪意識、‘改造意識強壓下去的‘反抗意識終于引發出來,我幾乎是第一次恢復了知識分子思考的本能。”正是在走出精神迷誤的過程中,魯迅的思想為錢理群所接受:“魯迅的懷疑主義否定精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魯迅的〈狂人日記〉里的歷史性質問:‘從來如此,便對嗎?以及他引述的屈原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以后漫長的精神困惑里。成了我和我的一些年輕朋友的座右銘。”19
顯然,那時候他對于魯迅的認知還僅僅限于革命的語境里,豐富復雜的魯迅并未能被其描述出來。魯迅的知識結構、思想轉變的內因,在他那里被列寧主義的話語限定著。在魯迅著作中,錢理群發現了“精神界戰士”和“永遠的革命者”,其實質就在于魯迅的批判精神。這種批判性、革命性的思想對于錢理群來說“這幾乎決定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選擇與學術道路”20。毛澤東、魯迅等人當時是左翼文學、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錢理群對其的認識也主要著力于他們思想上的批判性、革命性以及反抗性。恩格斯、毛澤東、魯迅等左翼、“共產主義”思想在錢理群早期思想中留下了重要痕跡,其中有民族主義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以及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情懷。由于當時他們所處的歷史境遇以及地位,這些“村落”的知識者一方面被排斥于體制之外,有著俄國知識分子的懷疑意識,但是他們自我定位為“永遠‘不滿足現狀的批判者,非正統的民間的馬克思主義者”21。他們通過閱讀共產主義理論,以反抗當時教條的意識形態。很顯然,雙方之間的分歧并不是思想上的,而是對原理的不同理解。這種思想上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反思的不徹底性烙上了鮮明的“民間”色彩。青年時代的錢理群還僅僅在左翼資源內部討論左翼文化的問題,不免同義反復,甚或存在幻影,知識背景限定了自己的思考,于是定格在較為簡單的邏輯線條里,這些無疑影響到他在貴州時期乃至1980年代的思考方式與反思的深度。
三
根據錢理群自述,貴州時期研讀魯迅著作對于他的意義在于“在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機,尋找自己的人生之路,思考中國的發展道路的艱難探索中,終于和魯迅相遇了,而且有了自己的‘魯迅觀,并且產生一個到大學講臺去講我心目中的魯迅的強烈愿望”22。考察錢理群1960—1970年代的魯迅論23是了解其貴州時期思想精神狀況的重要途徑,同時也體現了他當時的精神思想狀況:“從這些幼年之作里依稀辨認出某些‘個人性的模糊印記,似乎存在著某些前后相聯系的東西。”24其實,錢理群這四篇魯迅論帶有很濃厚的時代色彩與革命意識形態痕跡,并沒有擺脫瞿秋白、馮雪峰、毛澤東等人魯迅論的理論框架。但其具有錢理群鮮明的個人精神色彩,主體介入式的研究方式也非常突出,錢理群獨特的“魯迅觀”已經初見端倪。
1960年代錢理群通過對魯迅、毛澤東著作的閱讀形成了其首個魯迅觀。這一時期錢理群關于魯迅的論述借鑒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理論框架。在《魯迅與毛澤東》一文中,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理想主義,與農民的關系等命題是對當時革命文藝史觀的借用,但錢理群從毛澤東、魯迅思想中找到了精神的支柱。錢理群從毛澤東關于魯迅韌性戰斗精神的論述角度展開了對魯迅的認識:“這種性格,我以為表現在毛澤東同志身上最為鮮明的,就是毛澤東稱贊魯迅先生的那種沒有絲毫奴顏和媚骨的‘硬骨頭性格,那種對無論什么窮兇極惡的敵人都絕不屈服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疾惡如仇的反抗性格。”25錢理群對魯迅性格的把握是準確的,他對魯迅“硬骨頭”性格和反抗性格的強調,無疑與其貴州時期的身份與命運聯系在一起。“魯迅一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他始終立足于反抗權威性話語的立場上為各種受壓抑的思想爭取著表達空間。”26在這種“壓迫—反抗”的文化心理機制下,錢理群為自身尋找到了反抗現實政治和文化的理論依據。錢理群與魯迅的相遇,無疑有著現實政治與文化傳統的基礎。魯迅的思想文化傳統同毛澤東思想文化傳統并不是完全契合的,而“對‘文革運動本身的獨立思考與獨立意識的萌生,必然以掙脫‘文革話語的羈絆為其向導”。錢理群對“硬骨頭”精神的強調,建立在當時“閉關鎖國”的背景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向往、期待之上,但是這種帶著對流行意識形態的抵抗態度也使得錢理群開始通過接觸、感知魯迅而開始獨立的思考。他在貴州時期對魯迅著作的閱讀,所帶來的是和魯迅所代表的五四傳統的銜接:“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是在對人的精神需要的強烈感受中建立起來的,它直接關聯著對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的思考,是通過激活人的內在精神而激活中國人的生命活力、實現中國國民性改造這一根本目的的一種精神學說。”27
與那些從既定的理論框架討論魯迅者不同,他的文字有著自己特有的痛感和問題意識,一切都與自己的生命體驗有關。錢理群在《讀〈野草〉、〈朝花夕拾〉隨筆》中展開了對魯迅心理、藝術的研究。他后來在編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引用章衣萍對《野草》的評價:“《野草》是心靈的煉獄的魯迅詩,是從‘孤獨的個體的存在體驗中升華出來的魯迅哲學。”28在這篇隨筆中,錢理群嘗試接近魯迅精神的核心,這樣理所當然地接觸到了五四新文化傳統。從魯迅帶有自己生命印記的文字里,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精神之火,在凝視前輩遺產時,也融入了青年錢理群自己的生命。
《野草》中“孤獨的個體”意味著魯迅獨特的精神世界。不同于《魯迅與毛澤東》中理論模式的僵硬,在《讀〈野草〉、〈朝花夕拾〉隨筆》中錢理群充分展現了自己的魯迅觀。他認為魯迅的“彷徨”是戰士的“彷徨”,其中既有消極的部分,也有積極的部分。魯迅的“彷徨”是由于他“為著克服,為著更快、更徹底地與糾纏著自己的可詛咒的‘古老的靈魂決裂,與‘舊我告別”。“他一方面‘無情面地解剖別人——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進行深刻的剖析,總結歷史和現實階段斗爭的經驗”,“另一方面,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29。魯迅寫作《野草》的1920年代與錢理群所處的1960—1970年代的社會環境與人生困境是相似的:都處于一種人生、思想的過渡期、轉折期,思想是蕪雜而矛盾的。而錢理群正是通過對《野草》的閱讀,對魯迅思想發展軌跡的考察,找到了精神思想上的向導,這也是對歷史、社會的反思與展望,就是“要為必然(也必須)到來的中國思想與社會的歷史性大變動作思想的準備,鑄造新的理論武器”30。作為尋路者,面對多變、復雜的歷史、現實,魯迅為錢理群提供了克服思想危機的精神資源。
與同代的許多關于魯迅的陳述不同,錢理群關于魯迅的描繪是在“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社會主義文藝觀的框架下,從思想性與藝術性兩方面展開了對魯迅著作的探討。除了對魯迅復雜的精神世界的發掘,他也描述了魯迅藝術世界的多樣性、豐富性。顯而易見,錢理群通過閱讀魯迅著作而做出獨立思考后所獲得的不僅是思想的自由,也是藝術的自由。錢理群在對《朝花夕拾》《野草》的藝術分析中通過對《野草》世界中“奇人”“奇事”“奇景”“奇境”意象的描繪,發現了魯迅作品中的聲音美、色彩美、音樂美,進而認識到魯迅藝術世界的瑰麗,而《野草》文體與風格的復雜多變體現了藝術的多樣性。在《朝花夕拾》中,錢理群發現了魯迅散文藝術天地的開闊,思想的自由,內容的豐富以及散文筆法的嫻熟。魯迅的藝術世界帶給讀者的是思想的自由馳騁,內容的馳騁,是想象力和情感的飛騰。
在《魯迅與進化論》一文中,錢理群借用列寧、毛澤東、瞿秋白的理論模式,討論了魯迅與進化論的關聯。雖然整篇論文沒有擺脫流行的革命話語與意識形態色彩,對魯迅思想的描述依舊是從進化論到階級論,最終成為共產主義戰士的敘述模式,但對魯迅思想的認識卻有一定程度的深化。錢理群強調魯迅主體的獨立性,即對于進化論、階級論有自己的選擇、轉化、創造,這樣在某種程度上深化了關于魯迅思想轉變的復雜性的認識。同時,錢理群借用魯迅的話語,提出了“立人”這一啟蒙主義式的話題。在錢理群的魯迅論中,人并非擺脫了民族國家話語的獨立個人,而是人民、革命者。“立人”的意義就在于啟蒙人民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從而成長為合格的革命者。其次錢理群提出了魯迅的反封建思想。他認為魯迅所批判的舊事物的范圍在從《文化偏至論》的“封建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舊習慣”到五四時期的“整個封建制度和整個封建階級”31,在提出魯迅對舊事物的否定精神之后,他提出了啟發農民覺悟的重要性。
大致說來,錢理群貴州時期的學術思考已經顯示了他的才華,其“我的魯迅觀”可分為三個方面。
一是魯迅思想的批判性。錢理群在《野草》中所思考的一系列問題,如“敵人”“群眾”“友人”“自己”“過去與未來”是既屬于魯迅,更屬于他自己的人生體驗。錢理群認為魯迅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32,他反對“瞞和騙”,既認識到“敵人”的兇殘和欺騙,也看到了群眾的弱點,其中既有寄予希望、報以同情的群眾,也有需要批判的群眾。錢理群認為,魯迅有自己獨特的愛與憎:對群眾中的“猛士”“英雄”是寄予希望;對弱小者是報以同情,但是對“旁觀者”卻深惡痛絕。他主張要對敵人和群眾的“不覺悟”狀態進行復仇,不能妥協退讓。在“人民史觀”的框架下,錢理群認為魯迅“改造國民性”是一個“啟發人民群眾的覺悟”的啟蒙式的命題。這個命題其實是對五四傳統的延續。同時,錢理群認為魯迅對群眾不覺悟的狀態“批判如此嚴峻,鞭撻如此沉重”里“包含著多么深切的、烈火一般的愛”33。而魯迅擺脫“彷徨”的方式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后,走上了與工農結合的道路,從此結束了‘孤寂”34。這樣錢理群的思想又帶有某種局限性。
二是魯迅思想的復雜性。在毛澤東評價中魯迅是完美的共產主義戰士。錢理群的魯迅論表述了對主流魯迅觀的批判、反思。錢理群從魯迅作品中引申出“中間物”的概念。他認為“魯迅不是那種站在一邊指手畫腳,教訓群眾的‘導師,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群眾斗爭中,和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并在群眾斗爭實踐中,去發現(甚至是發掘)、尋求群眾中蘊藏著的革命力量。而每一個發現,都引起魯迅最強烈的反應,給他帶來無限量的歡喜”35。魯迅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不是十全十美的,魯迅思想也不是解決社會前進、個人成長所有問題的萬能理論。魯迅也是“背著因襲的重負,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是生活在光明與黑暗之間,而最終會在黑暗中所沉沒。錢理群從《希望》《影的告別》《死火》《墓碣文》中看到了魯迅思想的“黑暗面”36:魯迅在“一切彷徨、矛盾、痛苦斗爭中掙扎”37,而這種言說已經溢出了革命樂觀主義式的表述。
三是魯迅思想的獨立性。對魯迅的局限性的認識意味著對魯迅本體的接近,并進而認識到魯迅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價值。錢理群認為魯迅在《野草》中“赤裸裸地把‘自己展現給讀者”。與魯迅相對的是那些嘩眾取寵以“革命”“前進”為旗號的人,魯迅和他們不同,不隨意接受流行的理論和口號,結論、真理“也要經過自己獨立的思考和消化,用事實加以檢驗,才能真正化為自己的血肉”38。魯迅對思想的轉變持懷疑的態度,他期望用客觀事實和實踐檢驗理論,而不盲從。在《魯迅與進化論》中,錢理群發現了魯迅思想在從進化論轉變為階級論過程中的復雜性:魯迅在對進化論的吸收中有批判,而對階級論的接受也是在彌補進化論不足的基礎上接受的,階級論并沒有根本否定進化論,只是糾正了進化論的偏頗。最后,錢理群得出結論:“魯迅并不曾作過任何思想的‘俘虜。他總是‘以我為主,從自己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目的出發,對這種種思想不僅有所選擇,而且有所改造,有所揚棄。……種種龐雜的思想,經過魯迅的改造,統統融(熔)為一爐,自成一體,成為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及魯迅個人風格的思想。這是繼承,也是新的創造。用任何一種曾經影響過魯迅的思想來概括這種嶄新的思想,都是片面的。”39對魯迅思想轉變辯證的論述,對魯迅獨立性的認識,體現了錢理群思考的獨特之處。魯迅的獨立性體現在魯迅與其他知識分子之間的差異,即“個人主義的核心在于我們最初的心理體驗:在我的存在與他人的存在之間的一種明顯的差別感”40。錢理群的魯迅觀發掘出魯迅區別于其他知識分子的精神特質,從而發現了魯迅所代表的五四個人主義傳統。
通過解讀錢理群的“幼年之作”,可以一窺錢理群貴州時期的思想軌跡、情感體驗以及當時的歷史背景。錢理群在1960—1970年代的人生經歷與其思想轉變存在緊密的關聯:對革命的認同與居于“革命者”之外的邊緣身份的尷尬;革命熱情消退后參加民間思想村落,通過閱讀共產主義理論、毛澤東、魯迅的著作,獲得了反思、批判社會、現實的理論武器;而正是他的革命經歷以及在民間思想村落中的思想操練,促使錢理群與魯迅的相遇,接近了魯迅所代表的個人主義傳統。在這些關于魯迅的論述中,反映出錢理群貴州時期的思想特點與精神狀況,雖然錢理群的魯迅論依舊是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框架下,但他通過吸收魯迅的思想資源接續了五四新文化傳統,借助魯迅度過了貴州時期的精神、信仰危機,在時代的局限性下做出了自己獨立的思考。更為關鍵的是,錢理群在這四篇文章中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與情感色彩延續到了其1980年代以后的學術研究之中,錢理群貴州時期與北大時期的學術思想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貴州時期錢理群的精神結構中還帶有濃厚的革命意識形態色彩,而這種精神狀況又與其1980年代的啟蒙主義思想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未經改造的自我與改造了的新我,個人自由、民主觀念與革命意識形態的相互詰難、打架,造成了價值判斷上的搖擺。”41以致于“陷入重圍,進退失據,左右為難”42。他早期學術思想以及學術實踐是其學術道路中不容忽視的存在,錢理群在貴州時期的“舊我”所代表的革命意識形態與北大時期的“新我”所代表的啟蒙主義思想,映現著錢理群不同人生階段的思想狀況,共同決定了他后來的學術道路43。而我們回望他晚年的思想時,早期的精神邏輯還是忽隱忽現的。■
【注釋】
①陸青劍:《錢理群:貴州·北大,我人生的兩個空間》,《當代貴州》2009年第22期。
②1118202141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第51、258、366、61、57、254頁。
③④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冊),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第425、427頁。
⑤何言宏:《當代知識分子寫作與現代性問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第83頁。
⑥[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孫名之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75頁。
⑦[美]莫里斯·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杜蒲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第277頁。
⑧⑨14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冊),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第117、118、120頁。
⑩22錢理群:《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第25、27頁。
12“五七”體制是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中講到的1957年反右運動后建立的國家政治社會制度,包括政治鑒定制度、政治審查制度、檔案制度、單位制度。
13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年第10期。
15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第4頁。
16錢理群:《我與魯迅——〈心靈的探尋〉后記》,見《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45頁。
17籃子:《奔突的地火——一個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歷程》,見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第55頁。
19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后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第259頁。
23錢理群貴州時期的幼年之作包括《魯迅與毛澤東》《讀〈野草〉、〈朝花夕拾〉隨筆》《老譜新用》《魯迅與進化論》四篇論文。錢理群自述“《魯迅與毛澤東》寫于1962年,是直接從當年的‘讀書筆記里抄下來的,雖談不上是學術論文,卻是我的魯迅研究的開端。《讀〈野草〉、〈朝花夕拾〉隨筆》寫于1976年3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階段;《老譜新用》則是‘文革結束時的產物。《魯迅與進化論》是讀研究生以后的第一篇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確是根據我在‘文革時期所寫的一些讀書筆記整理、補充的”。見錢理群:《走進當代的魯迅·后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430-431頁。
2425293132333435373839錢理群:《走進當代的魯迅》,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431、356-357、366、416、380、375、376、374-375、382、378、406頁。
2627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第156、155-156頁。
28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41頁。
30籃子:《山崖上的守望·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第7頁。
36夏濟安認為魯迅“他對光明的信心,其實并沒有驅散黑暗:但它至少形成一面盾牌,為他擋住黑暗的誘惑。……魯迅的黑暗的閘門的重量,有兩個來源:一是傳統的中國文化與文學。一是作者本身不安的心靈。魯迅敏銳地感受到這兩種具有壓迫力、滲透力,而又不可避免的力量”。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見《夏濟安選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第20-21頁。
40Colin Morris,The Discovery of the Individual,見[捷克]丹尼爾·沙拉漢《個人主義的譜系》,儲智勇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第18頁。
42錢理群:《有缺憾的價值——關于我的周作人研究》,見《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52頁。
43錢理群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處于兩種歷史選擇之中。一是追求“民族解放,社會平等,思想統一與意識形態化”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的道路。二是追求“個性解放與自由、思想分離與超越”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道路。錢理群:《有缺憾的價值——關于我的周作人研究》,見《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62-63頁。
(吳海洋,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