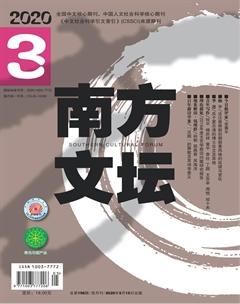新仕女圖:“海派”語境下仕女畫的當代轉型
中國傳統仕女畫以女性作為表現的主要對象,它體現了一個時代的女性和觀看女性的方式,更包含著對于女性身體意識的發現,也彰顯著審美觀念的變化。總體來說,傳統仕女畫的歷史可以分為晉唐以前、晉唐至明清及近現代這幾個大的發展階段。并逐漸形成了根植于古代貴族男性審美理想的女性藝術形象。
本文從19世紀末以來“海派”仕女畫對傳統的仕女形象的重塑為出發點,分析傳統仕女畫在樣式和內涵上轉型的可行性,并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討論當代“海派”語境下“新仕女圖”的創作的要點。
上篇:“海派”畫家對傳統仕女形象的重塑
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上半葉,“海派”繪畫①在江南地區崛起,帶著濃厚的商業特征與市民氣息。如果說,從唐宋至明清,男性的理想與想象在“仕女畫”的形象塑造中一步步深化,形成了鳳眼、柳眉、櫻桃嘴、長臉、細頸、溜肩、美人長、宮樣妝等仕女造像的“標配”的話,那么,“海派”畫家的仕女圖形成了與傳統仕女畫的樣式、審美上的鮮明區別,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以任伯年為代表的一批畫家,將折中的審美意識納入仕女圖中。人物的個性化減弱,唯美化、裝飾意味加重,圖像主題對女德的弘揚隨之弱化了,轉而尋求對象的形式美感,特別是形象的雅俗共賞傾向。這些通俗化描繪,凸顯的是對現實的妥協,這可以從一些生動的細節刻畫和人物面部表情的神韻中影射出來。由此,在傳統文人的審美價值導向下所衍生的仕女形象造型原則開始松動了,盡管我們仍能感受到其中與傳統仕女造型同條共貫的聯系。
第二,以林風眠為代表的留洋畫家,將西畫的造型與色彩融入仕女畫中。林風眠筆下的仕女,以個性化的流暢而概括的手法描繪出來,其充滿異域風味和裝飾感的造型表述,與傳統仕女圖清淡雅致的格調形成鮮明對比。“林氏”仕女畫是近代“留洋派”人物畫改良最為成功的案例,這種使形式美感與表現性占據了主導地位的改造方式與風格為傳統仕女畫未來的重塑提供了新的參考。另外,張大千雖不是“海歸派”,他是傳統仕女圖的繼承者與“深化”者,“深化”之處在于,他把女性形象與畫面唯美化了,他的仕女圖畫面明麗、干凈、甜美,塑造了帶有鮮明民國審美氣質的女性形象。
第三,女性形象的世俗化。這個方面可以海派畫家胡也佛為例。胡氏筆下的仕女形象,與其說是傳統意義上的“仕女”,還不如說是扮相上具備仕女特征的近代都市女性。她們無一不滲著濃濃的媚韻,這一特質,極為妥帖地還原了海上這一時期十里洋場的女人樣貌,時代的審美意識在這些形象里獲得了典型化的呈現:洋氣,嫵媚,富于風情,傳統仕女畫家極力回避的情欲與肉欲在他的仕女圖中得到了體現,這是一種重大的變革,是仕女圖世俗化最激進的變化。此外,胡也佛把西式的寫實觀念與民國月份牌所具有的吸引力,納入仕女圖的創作中,他的畫中細節精細入微,一絲不茍,因此,顯得繁復、煽情,且隱含著不可言狀的私密感。胡也佛的作品體現著現代都市男性的世俗趣味,色彩顯得艷麗奪目,一改傳統仕女畫的雅淡,而彰顯某種刺激性,在人物的塑造上,女性身體得到了更多的關注,由于畫家具有極強的寫真能力,因此還可以對面部表情,對眼神進行細致刻畫,而這種刻畫著意突出了女性的媚態或者說性感。
通過對以上諸家的分析,我們應當看到,“海派”畫家從造型、表現性、形象和審美趣味等角度,結合古典傳統與西學資源去改造傳統仕女畫的實踐對我們今天創造當代仕女畫具有啟發意義。盡管他們的作品未脫傳統仕女畫的審美內核和樣式框架,但卻是我們進行新的創造的重要參考與前奏。
下篇:當代“海派”文化語境與
“新仕女圖”的塑造
自20世紀改革開放的序幕拉開,一大批涉及都市情節的文學作品在各地相繼問世,這其中也包含滬上文壇王安憶的《長恨歌》、金宇澄的《繁花》等反映都市市井生活的優秀小說。與文學思潮相呼應,傳統國畫領域里,經過多年開拓積累,都市水墨畫漸成規模,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碰撞交融頻繁而激烈的上海,水墨人物畫的創作更是突出了都市的文化特征,形成了“后海派”。
在“后海派”水墨畫中,女性題材作品尤受關注,從形式到內容,也一改過往審美機制下仕女畫的單一表述,取而代之的是形式多樣化的以現實生態中豐富多樣的都市女性為依據的寫照,這些鮮活的個體,成為源源不斷可資照觀體察的創作靈感對象,這里,不妨把這類當代女性作品稱之為“新仕女圖”。
受惠于上海這座城市的滋養和文化浸潤以及都市生態特質影響,都市女性成為我多年來藝術創作表現的主要對象,這既是生活現狀使然,也是對往昔的追懷和一種情愫的自覺。在我看來,所謂的“新仕女圖”,畫中的女人不再是封建社會以男性為主導,依附于男權機制下的女性,也不是傳統審美中應物象形的外化,而是在新時代背景下人格、經濟獨立,具有自我支配意識的當代女性形象,故在形象塑造上應彰顯個性特征、時代審美烙印并兼顧地域性審美特征。以下從個人實踐的角度出發,試從下面幾個方面來剖析都市水墨人物畫中的“海派”女性形象的塑造。
一、立意角度的選取。畫家的生活體驗、品位覺悟、造型天賦及修為往往對創作態勢的大致走向起決定作用。將對都市文化的自覺與自省貫穿于創作思考之中,這種考量能較為能動地不斷激活新視角和域界,更替單一、單向的維度思考,進而增進造血功能。筆者近些年的創作,由簡入繁,循序漸進,一直回避敘事性的表現,更多地追求的是以社會生態為背景,借助于不同鮮活個體為藍本,因此,選擇以主觀意象造型來重構當下海上都市年輕人豐富而私密的內心獨白。過往的人生,給了我駕馭的方向感,力圖還原感同身受的種種際遇所引發的情緒追懷,這其中暗含種種隱涉內容取向,不經意間豐富了作品的感知內涵,也定格了人物瞬間的生機,進而引發各種聯想和共鳴。
二、人物造型及著色的運用。猶如搭臺唱戲,對于臺上旦角扮相的思考和拿捏,事關情境內容的鋪展,開相、臉型、胖瘦、發型、配飾、服裝等諸造型要素局部打造,著實有太多的講究,這些形和造有關,而非簡單地以存形為目的的再現,得由劇情的需要進行意象衍生,是主觀虛擬,最終如何落實到一招一式的身體語言上,會牽涉到許多方面,故是個復雜的綜合工程,杜絕排異,相互匹配和諧共生是主旨,當然,若最終能實現搖曳生姿還能贏得滿堂喝彩的話,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了。畢竟,角色的塑造是都市人物畫中的核心所在,這一關不過,其他都免談了。
一方面,為了著力于人物內心私密刻畫而力圖著色單純,顏色的絢爛與繁復容易產生喧雜和騷動,背離了我畫意的初衷,故而我的作品大面積沿用了傳統的墨分五色,水、墨、色在技術手段支配下彼此漫漬、游離,沖突和妥協交替發生,所形成的色塊與墨塊、色線與墨線彼此呼應,暗合了情緒的動靜轉化和跌宕起伏,最大限度地重構傳統意義上墨色語義的當代轉化。另一方面,鑒于人物氣質、性別、角色、劇情等方面需要,色彩的指涉象征用途得以延續,例如胭脂色,已成為筆者畫中女性膚色暈染的不二選擇,它妥帖地擔當起海上女人嫵媚矜持的小資格調語義訴求,在胭脂的烘托下,人物舉手投足間往往會入戲三分,活脫脫地成全了海上女人自我情緒性體驗的轉借需要。
三、肢體語言的意象表達。人物畫肢體語言的有意識表現,筆者探索人物畫初期即有體現,從以單一再現圖解為目的,到形成意象化的主觀表達,肢體語言的形式價值不言而喻。鑒于“新仕女圖”人物個體所承載的內容和形象豐富性遠超傳統仕女畫,故如何“活用”肢體語言內含的象征指涉功能,多年來已成為筆者海派女性塑造方面實踐的重點之一。現實中,不可否認,女性是最善于利用身體語言來傳情達意的,眉目傳情是一路,而運用肢體語言能力的優劣,卻往往事關女人整體魅力高低,這其中,包含著太多的信息需要去感知品咂。畫中女性只是“借殼”而已,實則是“幻化”的我,或舒展,或聚攏,或小憩,或冥想,或顧盼……在自編自導自演立意的主導下,借助于“舉手投足”,完成了多義性語義重構的轉換,這份“入境”的快意,常讓我欲罷不能,再生了臆想中姿態各異的新仕女,進而使人物造型語言的邊界得以拓展,最大限度挖掘新時代背景下女性個體的豐富內涵,還原她們當下的真實樣貌。
四、構圖空間的經營。謝赫的“經營位置”中,經是度量,營是謀劃;位置是動賓結構,即安排布置到位②。可見傳統繪畫中,主觀營造、合理安排的構圖意識早已確立,而今這一具有開放性和生長活力的傳統依舊具有現實實踐意義。
都市水墨人物構圖空間無非室內室外兩種:室內,借助女性在相對狹小空間內個人化狀態的重塑,揭示在生存、生活雙重壓力背景下都市女人獨處時種種私密的樣態,及其中所折射出的豐富內心世界,這些能體現新時代人群典型性特征的傳神寫照,與經過提煉的、簡約而不喧賓奪主的舞臺劇式布景的道具混搭最能互為映襯。畫面有意以構成理念進行切割處理,使人景和諧共生地維系著一幕幕虛妄的都市情景劇鋪展;室外,現今的生態雖已絕無可能還原古人的看山望水、臨風惆悵的情致,但骨子里的懷古情節仍會誘惑著你去虛構心中的“室外桃源”,尤其是作為久居水泥森林的身心疲憊都市人,內心渴望“慢生活”,心緒必然會和回歸自然的旨意不謀而合,在此心境驅使下,作為沿海城市,水、沙灘、陽光這些熟知的元素自然納入了我的視覺范圍,于是乎,各色人物“和諧”置于所熟稔的周遭生態中被“盤活”了,一心向而往之的景致慢慢得以清晰呈現。
上海這座有著殖民遺韻的城市,將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和諧共生地統一在一起。過往的歷史機緣成就了近代“海派”繪畫的輝煌;如今,在新時代背景下,似乎又到了一個關鍵節點,即在傳統仕女畫的當代轉型已成必然的趨勢下,在面臨各種機遇和挑戰并存的當下,如何賦予乃至深化當代“海派”仕女畫的當代性,以恰當的方式勾勒出海上女性經時光沉淀所展現的美感,的確很有探討梳理的必要,望今后這個課題得到更多的關注,得到探討與深化。■
【注釋】
①“海派”一詞,在學術界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海派”,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一個畫派;廣義的“海派”,則可以延續到20世紀新中國建立以后的繪畫創作。鑒于“海派”的內涵與外延仍在學術探討中,本文所言說的“海派”取廣義,也包括20世紀在上海進行創作的留洋畫家。參見單國強:《試析“海派”涵義》,《故宮博物院刊》1998年第2期。
②阮璞:《謝赫“六法”原義考》,見《中國畫史論辯》,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
(白瓔,上海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