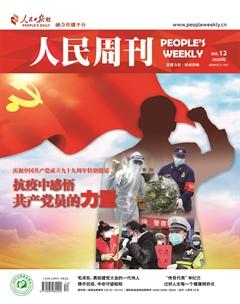木橋上覓夏涼
宮鳳華
夏日溽暑,酷熱難當,瓜棚豆架、竹林軒窗、榆柳蔭檐、青葦湖蕩,品茗遣夏,亦無不可。
在清代李漁眼里,“荷花之異馥,避暑而暑為之退,納涼而涼逐之生”。荷葉沾露,蜻蜓點水,菰雨生涼,有風既作飄搖之態,無風亦呈裊娜之姿。
我喜歡尋找從前古典的木橋或石橋。我想在夏夜凝眸浩渺的星空,品咂一個中年人酸楚的鄉愁。站在木橋上,到處都是田園山水,正如陳繼儒《小窗幽記》中所說“俗念都捐,塵心頓洗”。
我總想起小時候的鄉村生活場景。小村南面有一條河,靈動溫婉,蒿茼凝綠,河鮮潑剌。村姑織網,漁人捕魚,黃發垂髫,怡然自樂。
清澄的月光下,人們圍坐在院子里的桑木桌旁,悠然地抿著老白酒、吸著炒螺螄。濃濃的飯菜香引來了低飛的流螢,引來了陣陣歡聲笑語。
鄉親們撂下飯碗,擰著小杌子或小板凳,搖著蒲扇,三三兩兩聚到木橋上乘涼。我們坐在干凈的庭院里納涼。祖父邊編竹籮邊給我們講民間故事,不失時機地對我們進行仁義道德、忠孝節義的教育。
明月掛在鐵質枝椏間,月輝似汩汩細流,天地便如銀如鉑,朦朧而氤氳。流螢成群地在夜空中飛翔,那美妙的形象和光影把深邃的夜色點綴得分外瑰麗、分外神奇。
祖母坐在小凳上,我們圍在她旁邊,聽她講《七仙女》和《白蛇傳》的故事。她搖著一把蒲扇,搖著緩緩流淌的時光。院子里的墻頭上掛著鋤頭、彎刀和連枷,以標點符號的姿勢,記錄著遠去的農耕歲月。
我們總喜歡奔走于墻角、菜畦、草叢和草垛間,捕到螢火蟲,裝進墨水瓶里,比賽誰捉得多哩!父親見了便給我們講起“車胤盛螢照讀”的故事,我們聽后很受鼓舞,理想的種子在少年的心中悄悄萌發。
木橋兩側依次擺放著竹席、板凳、涼匾等。莊稼漢們往往赤裸著上身,談論著莊稼的長勢和收成。媳婦們聚在橋尾扯著家長里短,有的納鞋底,有的結網,還有的在船上墊一張蘆葦席,斜躺在上面,頗有“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憂怨。
葦叢里時時傳來野鴨的撲翅聲和驚飛的鳥鳴聲。蛙們以一種原始的激情,填補農事的間歇,貫穿春種秋收。農人從其旋律中,能傾聽到稻麥分蘗、坐胎和灌漿的聲音。
鄉村的夜晚除了飄飄悠悠的蟲鳴,便是盈盈灌耳的陣陣蛙鼓,激昂亢奮地聒噪著,將落寞的靜夜和曠野,喧囂得如同夏天一般熱情洋溢、生機勃勃。
祖父坐在橋堍頭拉二胡。拉起一段淮劇《趙五娘》。我最喜歡二胡蒼涼和憂傷的情調,令人內心一片秋水長天。那悲涼凄婉的淮調讓人禁不住黯然神傷。人世間的大喜大悲、愛恨情仇都得到酣暢淋漓的宣泄。
而今,人們享受著空調電網怡人的涼爽,少卻了與蛙鼓蟲鳴、潺潺流水的親近,少卻了鄉風民情的濡染、芰荷菰蒲的滋潤。
去周莊古鎮看到石橋,去溱湖濕地看到木橋,心中鄉愁汩汩流淌。木橋蒼老,夕照凝脂,流水嬌柔,牧笛輕飏,麥秸草屋,灰瓦土墻,隨意穿插,一種累積千百年沉垢般的氣息,撲人衣袂,宋畫般蒼勁古雅。
在木橋上覓夏涼,讓我們走出喧囂和浮躁,走出局促和狹隘,享受眼前的清風明月、耳畔的鄉音土韻,擷拾遺落在歲月深處的悲憫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