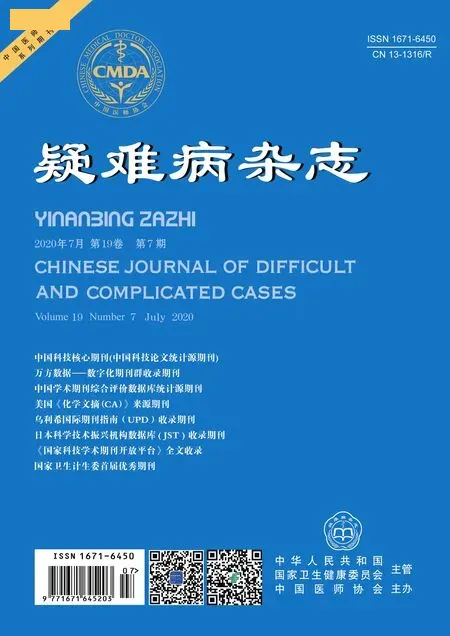無癥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核酸檢測35 d持續陽性1例
鄭志林,范正俊,艾俊,周林波,肖元川,孫榮艷
患者,女,16歲,因“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 入院。2020年1月23日患者乘坐高鐵自武漢回家,于2020年2月3日被當地衛生院隔離,2月5日曲靖市疾控中心咽拭子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陽性收住我院。入院前后患者無任何不適癥狀。其密切接觸的親友未見發病。入院查體:T 36.5℃,P 69次/min,R 19次/min,BP 144/82 mmHg,SpO297%。2月6日血常規示WBC 4.7×109/L,N 0.56,淋巴細胞絕對值1.56×109/L,RBC 4.59×1012/L,Hb 146 g/L,PLT 222×109/L。肝功能:總膽紅素37.5 μmol/L,間接膽紅素27.40 μmol/L。紅細胞沉降率22.00 mm/h。胸部CT:左肺下葉局灶性磨玻璃影(見圖1A)。依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診斷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輕癥。給予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克力芝)片500 mg口服聯合α-干擾素500萬U霧化吸入,每12 h 1次,抗病毒、防治并發癥和中藥等治療。2月17日復查肝功能總膽紅素和間接膽紅素指標正常。2月26日胸部CT示左肺下葉局灶性磨玻璃影已吸收(見圖1B)。CD4+細胞計數480 個/μl,2次外院檢測血清新型冠狀病毒特異性IgM、IgG抗體均陰性。經省級專家會診,依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最后診斷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普通型恢復期,2月17日起(治療后12 d),每48 h取咽拭子及痰液行COVID-19核酸檢測,核酸檢測35 d持續陽性,3月9日和3月10日分別輸入200 ml新冠肺炎患者康復期血漿治療。2020年3月11日轉陰,出院后每2周復查痰液、咽拭子核酸檢測,至4月14日均為陰性,臨床治愈。
討 論COVID-19屬于以往醫學的未知區域,但隨著相關領域專家地不斷研究探索,終于揭開了它的神秘面紗。國家衛健委聯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進行了多次更新。依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1],基于流行病學資料,輕型患者入院前后可無任何臨床癥狀,僅在COVID-19核酸檢測時呈陽性表現,和/或肺部磨玻璃樣改變。此類患者往往不屬于當前疫情防控篩查、管理的重點對象,卻依然存在傳染性,成為了移動的傳染源,給疫情防控阻擊戰帶來了更大的挑戰。通過對該患者的救治,筆者發現咽拭子核酸轉陰時間明顯早于痰液,說明單純進行咽拭子核酸檢測,在疑似患者篩查過程中容易造成疾病漏診,治療過程中咽拭子核酸檢測存在復陽的現象,需要高度警惕。聯合咽拭子及痰液檢測可以明顯提高檢測的準確度及敏感度。但是多數新冠肺炎患者表現為干咳,痰液標本檢測困難,對于高危患者有必要行支氣管鏡獲得深部呼吸道分泌物。該患者在胸部CT病變吸收后13 d后核酸檢測方轉陰,距首次核酸檢測陽性結果長達35 d。為了避免在此期間造成的疾病傳播,依賴咽拭子病毒核酸轉陰及CT肺部病變的吸收仍不足以讓患者解除隔離。
注:A. 左肺下葉局灶性磨玻璃影(2020-02-06);
B.左肺下葉局灶性磨玻璃影已吸收(2020-02-26)
圖1 患者胸部CT影像學變化
該患者在肺部毛玻璃陰影完全吸收后12 d痰液COVID-19核酸檢測仍然呈陽性,經云南省專家組討論最后診斷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普通型恢復期”。根據楊曉明等[2]推薦,感染后14 d內抗SARS-CoV-2 IgG抗體滴度低的普通型和重型患者可以選擇COVID-19的康復期血漿治療,《新冠肺炎康復者恢復期血漿臨床治療方案(試行第二版)》中建議采用康復者血漿免疫治療原則上病程不超過3周;在病情急性進展期,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或臨床專家判定患者存在病毒血癥時應當盡早使用[3]。該患者在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第32、33天輸入恢復期血漿,第36 d即出現轉陰,說明血漿免疫治療在新冠肺炎患者康復期仍然有效,可以有效縮短病程、促進機體清除病毒。至于該患者在確診后14 d及21 d,COVID-19 IgG、IgM均表現為陰性的原因仍不明確。新型冠狀病毒特異性IgM抗體多在發病3~5 d后呈陽性,IgG抗體滴度恢復期較急性期增高4倍及以上[1]。該患者IgM、IgG的缺失可能與機體對COVID-19病毒缺乏免疫應答有關,也是造成機體長時間攜帶病毒的重要因素。只有在被動輸入高水平的IgG中和抗體,提高體液免疫應答后才真正清除了病毒。
目前SARS-CoV-2核酸檢測靶標主要包含病毒基因組中3段保守序列, 即開放讀碼框1ab (open reading frame 1ab,ORF1ab)、核殼蛋白(nucleocapsidprotein,N)基因及包膜蛋白(envelop,E)基因[4]。另外,核酸殘片遺留也可能是病毒核酸檢測持續陽性的原因,但其機制仍不清楚。其次,如果康復期無癥狀患者病毒核酸檢測持續陽性,是否需要持久抗病毒治療,需要采取何種治療措施仍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