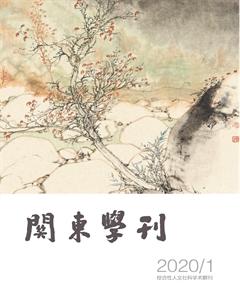大運河與天津飲食初探
萬魯建
[摘要]京杭大運河是貫穿中國南北的重要交通渠道,曾經為南糧北運發揮了巨大作用。大運河在溝通南北的同時,也使各地不同的文化得以交流與融合。飲食文化也是其中之一。天津的飲食,也深受運河的影響,融合了南北各菜系的特色,逐漸形成了具有天津地方特色的飲食。
[關鍵詞]運河;天津;飲食;文化
[作者簡介]萬魯建(1980-),男,歷史學博士,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天津300191)。
一、運河與中國的飲食文化
如今,大運河研究如火如荼,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涉及方方面面。既有運河本身的研究,也有運河文化的研究,更有運河沿岸城鎮的研究。相對來說,運河與飲食關系的研究,還稍顯不足。其實這也是運河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包含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運河與飲食文化的相互影響問題,另一個則是運河沿岸的飲食文化,后一個包含更為豐富的內容。
所謂飲食文化,是指“在食物原料開發利用、食品制作和飲食消費過程中的技術、科學、藝術,以及以飲食為基礎的習俗、傳統、思想和哲學,即由人們食生產和食生活的方式、過程、功能等結構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總和。”高成鳶先生長期研究中華飲食與文化的關系,出版過不少著述,其著述部分章節也偶有談及。如他在《飲食之道——中國飲食文化的理路思考》一書談到烹飪和京劇是中華文化并峙的雙峰時說道:“從更大的時空背景,關于菜系形成的史、地條件,天津的漕運和鹽商也非常重要。運河船夫的飲食,促進了天津小吃的繁榮,而小吃是烹飪技術出新的突擊隊。”他認為天津包子與淮揚的“湯包”有密切關系,而關于馃子由來的傳說也可以證明課子是通過運河傳到天津的。
《中華文化通志·飲食志》有一節專門談及南北大運河的開鑿對飲食資源交流的意義:“從隋唐到明清,運河不僅是封建政權漕運的大動脈,也是南北人民經濟交流的大動脈,東南的糧、棉、鹽、絲綢和海味,北方的煤、鐵器、棗、栗、藥材和皮毛,都是重要的交流物資。”“各類城市,都是由各自的腹地供應大量的飲食物資或與飲食有關的各類物資的集散地,如各種糧食、禽畜、水產、蔬菜、水果、海味、臘味、干果、藥材、鹽、糖、油、醬、醋、茶、煤炭、各類炊具、食器等等。由于城市五方雜處,又集中了適應各地口味的飯館和小食店。港口城市還常常進口高檔餐具,如水晶、瑪瑙、玻璃器皿,和高檔海味,如南洋的燕窩、魚翅,日本的干貝,墨西哥和日本的鮑魚等等,供貴族社會享用。各大城市由于各族雜居和中外雜居,又是飲食文化的地域交流、民族交流和中外交流的基地。”
運河沿線城鎮的飲食文化與運河密切相關,如張熙惟在《略論運河文化》一文中談道:“運河區域諸城鄉廣大居民有著共同的節日習俗,甚至各地的飲食習俗也因運河而廣泛交融。揚州居民煮茶獨取運河之水,天津居民飲食亦‘皆運汲于河水。揚州富商宴席上‘餌燕窩,進參湯,德州豪貴同樣把‘燕翅席作為高檔享受,故海參、魚翅、燕窩、魷魚、火腿等貴重食品充斥于運河城鎮市場。”臺前縣甚至將本地的飲食文化視為“運河舶來的”,主要是糖醋魚、醬菜和炸鵝脖三種。很多名菜,隨著運河的開通而通達南北各地。直至清代,大運河仍為北京與華中、華南廣大地區聯系的主要動脈,每年僅漕船就有7690余只,連檣接帆,駛往通州。各種“南貨”“廣貨”“洋貨”的源源而來,使得朝廷在河西務設河主簿廳一所,設河西務巡檢司。
周愛東所著《揚州飲食史話》,對運河名城揚州飲食文化與運河的關系作了闡述:“由于運河的開鑿,中國東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物產、文化、經濟、政治的聯系一下子變得緊密起來,而這個聯系的關節點就是揚州。從此以后,關于揚州飲食的諸多話題最終都會扯到運河上來。”隋唐之前,揚州飲食的基本風格是樸素,除去用料與風味,意趣上與其他地方并無太大的區別,但到了隋唐,揚州飲食開始表現出其精雅的風格。他認為:“在明清揚州鼎盛時期,揚州美食制作的主力軍,開始并不全是揚州本地人,而是那些富商或官僚帶來的家廚。但到了嘉道時期,這些商人在揚州生活日久,他們的家廚也逐漸本土化了。揚州衰落的時候,揚州本地的名廚紛紛外出去討生活,很多人去了上海。”
浙江菜的形成,也深受運河的影響。“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開通,南北的交通更為方便,特別是到了北宋,杭州作為國都,城里遍布全國各種風味的酒樓,各地的名廚均聚集在這繁華之地一顯身手,使浙菜形成了‘南菜北烹的獨特風格,一度成為我國南菜的主要代表。”眇‘隨著大運河的開通,杭州醋魚、魚羹等美味傳至大運河沿岸城鄉,直至北京宮廷。”
關于天津飲食與運河的關系,譚汝為曾在《天津方言與津沽文化》一文中指出:“從運河漕運時代,淮揚菜與魯菜已開始在天津融合,輪船通航又使大批膠東人從海路來津,使以‘河海兩鮮固有特色的‘津菜技藝大為提高。”根據民初天津方志所列飯店、食堂、旅館、棧房,即多達幾百所。“其中飲食業極享盛名,出現了全國各地風味的飯館,從而為南來北往的官吏、商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許多飲食在運河沿線興盛,和漕運船只南來北往帶動了南北交流不無關系。
例如,包子大致始于北宋,南宋時流行于民間,陸游與鄉鄰聚飲時也經常吃包子。包子的特點是能夠將主食與佐餐的菜肴統于一體,可以邊走邊吃。“清代運河線上埋城壩以北的纖夫就是這樣做的。也因此運河沿線碼頭城市的包子都或大或小地有些名氣,沿岸集鎮渡口的飯攤上也多賣菜多肉少或干脆無肉的菜包子。”天津食品三絕之一的狗不理包子,最初也是南運河尾閭侯家后岸邊的小包子鋪的實惠便捷食品。“主顧除河壩上的腳行,就是停泊船只上的船工和待駁的纖夫們,都是些既圖實惠又圖方便快的負力忙人。”
二、近代天津飲食業概況
開埠以前,天津因漕運而興,近代開埠以后,天津更成為一個南北客商、中外人員往來集聚之處。人員的交流,帶動了飲食業的繁盛。《津門雜記》說:“津地為九河下游,合眾流匯歸三岔河,皆由直沽人海。”又說:“天津一城,三面臨河,大海在其東南,三角淀繞其西北,為河海之要沖,畿南之屏蔽也。”《續天津縣志》也說天津“誠水陸通衢,畿南之大都會也”,故“舟楫之所式臨,商賈之所萃集,五方之民之所雜處”。正是由于這樣的地理位置,使得天津盛產魚蝦蟹等水產品。加之東臨渤海,西扼九河,北界燕山,南有港淀,各種食材豐盛,為天津飲食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天津自建城以來,飲食業極為繁盛,風俗詩中談到天津的飲食:“數到珍饈是食羊,西瓜餃子酸辣湯。今朝供客添佳味,烙餅加攤韭菜黃。”尤其河海產品每每見于百姓餐桌,是天津人的最愛。《秋吟詩草》說:“津門三月便持熬,海蟹堆盤興盡豪。”清人羊城舊客所著《津門紀略》所列“食品”一卷,說道:“津沽出產海物俱全,味美而價廉。春令最著者則蜆蟶、河豚、比目等類;秋令螃蟹,肥美甲天下;冬令則衛河銀魚,馳名遠近。更有鐵雀,佐酒亦佳。黃芽白菜勝于江南冬筍者,以其百讀不厭也。”唐芝九也有詩吟誦鐵雀、銀魚之美味:“樹上彈來多鐵雀,冰中釣出是銀魚。佳肴都在封河后,聞說他鄉總不如。”而清代津門詩人樊彬的《津門小令》則更為形象:“津門好,美味數初冬,雪落林巢羅鐵雀,冰敲河岸網銀魚,火擁獸爐余。”《津門食譜》也說:“銀魚,為津門之特產,前清時曾充貢品。販者每以衛河名;殆產于衛河者為佳,產于三岔河口者為貴。衛河即南運河;三岔河口即疇曩南北運河與海河會流之所,故址在望海樓前。”也正是因為天津人愛吃、會吃,故天津人有“衛嘴子”的稱號。
天津飲食業比較發達的地區主要集中在運河與老城廂附近,清末民初,伴隨著河海運輸的繁榮,侯家后、北大關、官銀號一帶地區工商業興起,旅館、餐飲業日漸發達。據刊印于1898年的《津門紀略》食品一卷所記載,當時天津有各類有名飯館多達35家,如義和成、聚升成、聚源成、天和樓、天慶館、真素館等。1920年代,根據統計南市比較有名的菜館飯館就有三十余家,像天一坊、華寶樓、聚慶成、登瀛樓、義和成、天和玉、泰豐樓、燕春樓等都在這里。到了三十年代,河北鳥市和侯家后、北大關、南市并稱為天津飲食攤販四大市場。河北的三條石、河東的東車站等地的飲食業也比較發達。根據1936年《天津游覽志》后附的《津門小志》記載,本埠飯莊約五百有奇,其最著名者,為侯家后紅杏山莊和義和成兩家,其次為第一軒、三聚園,裝飾之華麗,照應之周到,味兼南北,烹調絕精,大有“座中常客滿,樽中酒不空”之慨。
天津不僅有天津風味的菜系,很多山東風味菜系、南方風味菜系和西式及日式的飯莊飯館也紛紛出現。根據1934年天津市志編纂處編《天津市概要》統計,此時天津計有山東館8家、濟南館2家、河南館2家、四川館2家、廣東館2家、保陽館2家、山西館2家、清真館2家、西餐館4家、中西餐館5家、日餐館3家。此外,還有西點鋪、中點鋪等。據另一統計數據,1930年代,天津知名的八大成、九大樓、十大飯莊也都先后建立。八大成主營天津菜系,為明利成、聚德成、聚慶成、聚合成、義和成、聚興成、聚樂成、聚合成;九大樓則主要是回民羊肉館,即相賓樓、賓華樓、大觀樓、迎賓樓、富貴樓、老會芳樓、會賓樓、鴻賓樓、暢賓樓;十大飯莊則為山東菜系,即同福樓、全聚德、天源樓、登瀛樓、松竹樓、天興樓、晉陽樓、萬福樓、會英樓、蓬萊春。至此,天津的各類飯莊及馃子鋪、豆腐坊多達兩千戶。天津飲食業之發達,不僅吸引了南北往來的客商,更是連京城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也都聞名而來。據《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編》之“天津之社會觀察談”記載,“天津商肆之多且盛者,首推酒席館”,“北京名公巨卿,遇有大宴會,輒苦拘束,不能暢所欲為。乃群趨于津埠,呼盧喝雉,任意揮霍。風會所趨,而酒席館遂應時大興。高樓大廈,陳設華麗,遠勝京師。每當夕陽西下,車馬盈門,笙歌達旦。”由此可見,當時天津飲食業之盛。
“九一八”事變后,由于日本不斷在華北制造事端,使得華北局勢日益緊張,人心惶惶,工商業受到極大影響,而寓居天津的官僚政客、軍閥富豪紛紛南下,或避居租界,對南市一帶的商號打擊很大,很多飯莊、飯店和飯鋪倒閉,使得天津飲食業出現一次衰落。尤其是“七七”事變后,戰亂使天津飲食業遭到了嚴重打擊。到1940年代,隨著日租界中原公司和法租界泰康商場、天祥市場、勸業場一帶地區的畸形繁榮,飲食業才又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根據天津日本商工會議所編印的1942年度《天津華商公會名鑒》統計,當時天津有各類飯館200余家,如著名的登瀛樓、永安飯店、聚合成、豐澤園、致美齋等都在其列。另有從事面食業的商戶300余家。另據1943年的統計,“全市包括大飯莊、中型飯館、小飯鋪和錁子鋪、豆腐坊等共有2800余戶,另外還有天津聞名的侯家后(鳥市)、三不管、郭莊子、謙德莊四個飯攤市場和各地區走街串巷的個體戶2000余戶,較之以前發展可謂更上一層樓。”
如果說在1945年之前天津飲食業是以北菜館為主的話,那么伴隨著國民黨接收的到來,南方人日益增多,南菜館也在逐漸增加,由原來的15戶增至34戶。到1946年天津市的飲食業發展達到頂峰,全市飲食業坐商多達3900戶,職工人數為15000余人,另外還有飯攤和個體飲食戶4500余戶,從業人員5000余人。按照菜系來分,天津菜系還是占據主流,多達百戶;山東菜系50余戶;江蘇菜系17戶;廣東菜系17戶;浙江菜系3戶;四川菜系3戶;西餐13戶。另外還有其他各種菜系的餐館及素菜館十余戶。從空間分布來看,勸業場、天祥市場、泰康商場附近有80戶;南市一帶有50多戶;在官銀號、侯家后、北大關一帶有40多戶;在河東、河西、南開等區有40多戶。此后因受戰爭的影響,1949年天津解放時,全市飲食業坐商下降至3500戶,飯攤和個體戶歇業者更多。
近代以來,伴隨著天津的開埠和租界的設立,天津的直接對外貿易日益繁榮,西方的飲食文化也伴隨著外僑的到來而發展起來。最初是起士林和義順合兩家西餐館。起士林位于舊德美租界交界處,義順合位于小白樓。義順合于1932年改為維格多利。此外比較有名的還有福祿林飯店、國民飯店、惠中飯店。福祿林飯店始建于1931年,后改為永安飯店,位于法租界原明星電影院旁(今新華路和平影院旁)。當時不少軍政官僚、官紳巨商等多在此舉辦喜壽喪事。1944年停業改為黃金市場。國民飯店建于1923年,位于原法租界天增里(今赤峰道52號),是成立最早的西餐飯店。1933年吉鴻昌曾在該飯店被捕殺。該飯店以西餐為主,設備比較講究,且附設旅館業務,并有舞廳、中餐等部,裝潢也富麗堂皇,頗受當時官商富紳的喜歡,很多紅白喜壽宴會多安排在此舉行。惠中飯店位于勸業場華中路,1931年開始營業,產權為前熱河督軍湯玉麟所有。內部不但有西餐部,還有中餐部、舞場、高爾夫球場、屋頂露天電影等,是當時全市最大的餐廳。此外還有小規模的西餐廳,如大華飯店、太平洋飯店、安樂飯店、熙來飯店、華園大菜館、德義樓等。日租界的設立以及日僑的大量來津,也使得日本飲食文化逐漸在津門生根發芽。像當時比較有名的大和旅館、敷島、神戶館、芙蓉館等都兼具旅館和飯館。此外還有專門的日本料理店,如清月、末廣、櫻花食堂、東洋軒等;還有壽司店,如奴壽司、曙壽司、新橋、美登里壽司、一休、若乃等,雖然規模未必有多大,但日本味道十足。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滅亡,很多清朝的遺老遺少寓居津門,他們又帶來了宮廷飲食文化。如此一來,天津成了中外美食的匯集地,相互融合,五方雜燴,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天津飲食文化。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餐飲業達到頂峰,甚至成為中國北方之最。即便時至今日,外地人說起天津,首先會想到“煎餅果子、狗不理包子和十八街麻花”,外來游客來天津游玩,一定會去南市食品街、古文化街品味天津美食。
近代天津飲食業之發達,不但聞名國內,國外一些漢學家也都予以關注。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歷史學家稻葉巖吉,曾于義和團事變前后來中國華北、華中地區考察,后來他與曾任日本駐齊齊哈爾領事古澤幸吉合著《北方支那》(岡崎屋書店1902年版)一書,專門有一節記述天津的餐飲業情況,即“天津的飯館子”。他在書中寫道:“天津北門外有一條狹窄的斜巷,僅能容一輛車通過,當地人稱為侯家后,房屋連排,戶戶藏嬌。而且天津的茶園飯館主要集中在這里,有名的為義和成和聚盛成兩家,兩者都是中國飯館,皆能容納數百人。天津自古以來都是奢侈之地,而且一般商賈商談交易都是在飯館茶園進行,由此不難想象侯家后的繁榮。現在要問中國飯館的情況,主要是由山西、山東兩省的人經營,南方來的人從事此業的以前完全沒有,而且飯館也都是純粹的飯店,飯飽之后沒有嫖妓的規矩。如果有的話,也是最近出現的一些飯館。飯館為了迎合客人的嗜好,可以拿出單子點菜,不過是魚翅、海參和鴨子,作為一桌的主人還要說明所需的佐料,酒主要是紹興酒,偶爾也用燒酒,也只是為了迎合客人的嗜好。需要提前預定,藝妓的陪酒也都是一般性的。”從他的這一記載來看,最初天津的飯館多為山西、山東人所經營,著名的登瀛樓飯莊就是以經營魯菜而聞名。后來在津南方人日益增多,粵菜館、湘菜館、寧波菜館等也日益興盛,形成了南北菜系匯聚津門的情況,即有“魯、粵、蘇、川、浙、閩、天津飯館和回民飯館。”正如津門詩人崔旭曾所言:“曾經最說天津好,運河薈萃八方菜”。陳克也認為:“山東菜和淮揚菜對天津菜的影響離不開運河的溝通作用。”
三、運河培育的風味食品
運河,除了讓風味各異的菜系匯聚津門,同時也造就了風味獨特的食品,最為著名的就是楊村糕干和獨流老醋。
楊村糕干是位于北運河畔的武清區楊村的杜姓人家所制作的。杜家本是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人,后沿運河來到武清楊村。因不懂北方耕種習俗,故以做小本生意為生。他們從官家運糧船購得私米,將其磨成面粉并加白糖加工成糕干,沿河叫賣。由于他們做的糕干甘甜可口,價格便宜,很受南來北往客商的歡迎,生意越做越好,后來杜氏家族生產糕干者多達十余家。康熙皇帝南巡駐蹕楊村時曾品嘗過楊村糕干,贊不絕口,并將其列為貢品。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歡,甚至御賜“婦孺恩物”四個大字,并賞龍票一紙,使其可以購買官價白米,更使得杜氏糕干名聲大振。據說還曾獲得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三等“嘉禾”獎。1946年后擔任天津市長的杜建時曾自稱出生于楊村萬全堂糕干世家,故被時人戲稱為“楊村糕干”。1956年,周總理陪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到楊村參觀筐兒港八孔閘水利樞紐工程時,在品嘗楊村糕干后說道“不減當年!不減當年!”甚至還風趣地吆喝一聲“楊村糕干老鋪的好!”時至今日,楊村糕干仍舊深受大眾的喜愛,2008年被天津市批準為“天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獨流老醋,也因運河水而聞名于世。因為“食醋好不好,用水最重要。”而獨流鎮又恰位于南運河和子牙河、大清河交匯處,有著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1927年《益世報》曾報道說:“醋為獨流特產……以其水土宜于制醋,故味佳,醋商亦發達。”獨流老醋的生產早在明朝嘉靖年間的《河間府志》就有記載,后來在清朝乾隆年間還一度成為貢品。關于獨流老醋的由來,靜海地區還有一則美麗的傳說,流經獨流鎮的南運河水甘甜可口,康熙知道后命令獨流的造酒師來福利用運河水釀造御酒進貢。但來福不愿意獻技皇上,撒謊說甜水加熱要變成酸酒的。康熙便命令他造酸酒,最終在一個仙師的指點下得以造出酸酒,因二十一日酉時出,故名醋。康熙曾特意頒旨,賜名“獨流老醋”,使得其聲名遠播。1922年,大總統黎元洪經過獨流時專門去老三立作坊品嘗老醋,并為其題寫了牌匾。后來在1922年的直隸省第一次工業觀摩會上,獨流老醋還獲得了食品類一等獎。據1906年成書的《直隸全省商務概況》記載,“天津府靜海縣獨流醋行銷天津、河南、山東等地。”1913年《直隸第一次實業調查記》也說:“獨流所制之醋,品質極佳,久已運銷進京及各縣。”1932年的《益世報》也有報道說:“獨流醋,氣香味醇,為他處所不及,鄰近諸縣,視為珍品,故恒以此送禮。該鎮所產之醋各省馳名,獨流老醋無不知者,暢銷于長江南北及平津一帶。”新中國成立后,獨流老醋得到全面的繼承和發展,并確立了“天立”商標,2001年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如今,天立獨流老醋早已行銷全國各地,甚至遠銷美國、日本、俄羅斯、新加坡等世界各地,成為天津飲食的一道名牌。
據說嘎巴菜也與南運河沿線的農民有關。根據顧道馨先生的說法,清乾隆年間魯北冀南運河沿線農民下衛,行囊中多自帶煎餅以充主食,開水沖青醬(即醬油)泡一下,即可泡軟煎餅,又有了咸味,這就是一頓飯。后來西碼頭一帶(現紅橋區蒲包店一帶)的小店、小飯鋪做起了這種生意,將蔥、辣椒、醬油熗鍋做成鹵汁,既有滋味又有濃度。這就是嘎巴菜的雛形。此后這種食品不斷從遠郊向近郊傳播,不斷改進,最終形成現在的嘎巴菜做法。武清河西務的飲食習俗,也與漕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河西務具有特色的食品大油餅,就是為了適應漕船上的船工們和倉庫的搬運工們專門食用的。這種食品個大味香,外焦里嫩,論斤賣。賣苦力的船工們花上有限倆錢兒,就能填飽肚子,大油餅又賤又經餓,頗受體力勞動者的歡迎。數百年來,河西務大油餅譽滿南北大運河。”
此外還有河西務的金家課子攤兒。這是一個名為金振山的回族小伙子開設的。最早只是一個臨時馃子攤兒,只炸“套包子”馃子。所謂“套包子”,就是炸出來的馃子是橢圓形的,就像套在馬匹肩上的套包子,故而得名。后來金振山又改進了技術,面劑加大,搟成薄薄的大片,用刀在上面劃幾道口子,再放油鍋里炸。如此炸出來的馃子焦、脆、香,特別好吃。后來還烙大餅,變成了大餅卷果子吃,使得其早點攤更加受歡迎,甚至連賣豆漿、豆腐腦的攤點老板,也都聚集在金家馃子攤旁邊做生意。此后,金家又將這一制作工藝傳授給了同行,使得大餅馃子逐漸成為河西務鎮的特色小吃。
至今,大餅卷馃子,也是天津人早點的重要食物。甚至當年在津的日本人也非常喜歡。
日僑豐田勢子在回憶錄中曾談到天津的食物,她說兒時在津的早點吃的是素面包和大餅。素面包一般都是自己做,而大餅則要出去買。一般都是豐田和她姐姐去。她們會高興地看如何制作大餅。她寫道:“面粉抹上芝麻油,攤得薄薄的,來回攤幾十次,變成直徑四十厘米的面餅,在鐵板上烤。”然后把大餅切成三角形,卷上課子吃,味道非常美。還有就是“將大餅切成放射狀,卷上馃子吃。馃子是在面粉中加入砂糖和油等作料,做成長度為三十厘米,表面泛著芝麻油的油炸東西。稍微帶有咸味的大餅和甜味的馃子簡直是完美結合,不知道是否還有什么比這好吃的。第二天,還可以將變硬的大餅切成寬條,與剩下的馃子和肉及野菜一起煮,也非常好吃。”
日僑近藤久義同樣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他在回憶錄中也寫道:“和這個肉店并排,還有賣饅頭、包子、鍋貼、大餅、課子和燒餅的商店。早飯經常吃大餅馃子。包子根據季節和食材,加之秘傳手法的不同,其配料也有細微變化。包子只有趁熱才好吃,還能從里面流出汁。那種令人懷念的味道,至今還無法忘記。”他甚至還記得烤餅的情況:“烤大餅時,要用半圓形屋頂形狀的素陶器做成的東西,上面有直徑五毫米的小洞,每個小洞間隔三四厘米。小洞發熱,大餅上面就會形成針灸一樣燒焦的痕跡。”
久村千惠子對于天津的飲食,也有滿滿的回憶。她寫道:“我們在中國生活時,廚師給我們做一日三餐。早晨,母親是咖啡和面包;我們則是面包餐,有西式的面包、火腿、雞蛋;父親買來豆漿,撕碎新炸的‘錁子,放人有咸味的豆漿里,每天都是如此。我們也偶爾吃,覺得非常好吃。天津的豆漿也非常好喝。”并說他們的小吃就是大餅夾馃子,非常可口。大餅還有厚薄兩種,薄的卷起來更好吃。
四、運河形塑天津飲食業
飲食文化的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是多種因素的合力而成。它“除了依存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地域交流、民族交流,還依存于國土開發和生態環境的發展。”彼此之間又互為條件、互相促進。因此,天津飲食文化的發展,也離不開上述這些因素的影響。
天津地處渤海西岸,是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南運河和北運河交匯之地,河多、灣多,還有各種湖、池塘等,水域寬闊,水產極為豐富。因此,河魚、海魚、蝦、蟹、蚌類,應有盡有。天津人也因此喜歡海鮮、河鮮。周楚良在《竹枝詞》中提道:“爭似春來新味好,晃蝦食過又青蝦”。張燾也有詩云:“二月河豚八月蟹,兩般也合住津門”。天津人更有俗語“當當吃海貨,不算不會過”,還有“吃魚吃蝦,天津為家”。可以說,天津人對于河海鮮的喜好,既與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也與運河帶來的各類飲食習慣有關。隨著大運河溝通南北,“各地風味開始涌人津門,逐步‘津化,使津菜形成多元的風格,由簡便、實惠、質樸的民間本色發展成為以咸鮮為主、酸甜為輔、小辣微麻、復合烹調、風格獨特的地方風味流派。”1935年的《津門食譜》說:“津門處五河下游,土產最富,舉凡羽毛鱗爪之類,可充庖廚而屬饜于饕餮者,四時不絕。”1938年出版的《天津旅游便覽》也曾如此寫道:“天津五方雜處,當南北之衛,故南北飲饌,皆有專門烹調之處。”并說:“山東館為北方固有之品……四川館之烹調,鮮美可口,美麗為其巨擘。……紫竹林為寧波館,北安利為廣東館,兼售西餐。小食堂為江南館,而兼售川菜,皆宜于小吃。”總之,天津因運河而為南北交匯之地,為了適應來自全國各地民眾的需求,各類餐館和食品應運而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并最終形成獨具特色的津門飲食文化。天津風味具有代表性的菜肴為八大碗、四大扒、冬令四珍等。八大碗有粗細之分,粗八大碗是熘魚片、燴蝦仁、全家福、桂花魚骨、燴滑魚、獨面筋、川肉絲、川大丸子、燒肉、松肉等;細八大碗有:炒青蝦仁、燴雞絲、全燉、蛋羹蟹黃、海參丸子、元寶肉、清湯雞、拆燴雞、家常燒鯉魚等。四大扒則是成桌酒席的配套飯菜,有扒整雞、扒整鴨、扒肘子、扒方肉、扒海參、扒面筋、扒魚等。冬令四珍則是指鐵雀、銀魚、紫蟹、韭黃。天津著名餐館“八大成”的代表菜,如罾蹦鯉魚、熘黃魚扇、炒青蝦仁、煎烹大蝦、酸沙紫蟹、金錢雀脯、麻栗野鴨等,大都是海產品煎制而成。這無疑與運河有很大的關系。
此外,天津盛產高粱酒,也與運河有著密切的關系。康熙《天津衛志》所載之“接運海糧官王宮董魯公舊去思碑”中提到,“直沽素無嘉醞,海舟有貨東陽之名酒者,有司市以進。”這說明直沽地區作為河運和海運的交匯點,成為漕糧的中轉碼頭,得以通過船運帶來別處的好酒。明人作的《直沽棹歌》日:“天妃廟對直沽開,津鼓連船柳下催;釃酒未終舟子報,柁樓黃碟早飛來。”所描述的乃是漕工抵達直沽后在天妃廟前以酒行祀的風俗。由于有祭祀和消費的需求,漕工便開始取大直沽后街的優質小溪之水,自設燒鍋釀酒。“先是自給自足,后是余酒出售。天津釀酒業,自此開創。”但是在1884年以前,天津燒鍋業的整體產量每年不超過2萬擔,1900-1917年天津燒鍋業得到飛速發展,1910年至1916年更是天津釀酒業的黃金時期。1916年達到了153246擔,折合1500多萬斤。到了1930年代,天津的燒鍋業達到鼎盛時期,1931年出版的《天津志略》記載:“天津燒鍋最盛時,多達72家”。從這些燒鍋的分布來看,“大量的燒鍋其實都分布在運河和海河兩岸,是漕運船民的活動地區。”雖然天津人以飲燒酒為主,“但是在江南風味的飯館內也可以品嘗到南酒,有竹枝詞為證:‘消夜鐘方一點交,無非蒸餃與湯包。花雕酒佐江南菜,小碗乾絲幾片肴。”由此可見運河對天津酒文化和餐飲業所帶來的影響。
天津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地方,河海漕運的興起,又便利了南北往來,使得南北餐飲文化的交流和借鑒成為可能。從菜系的豐富、菜品的多樣、飯館的位置來看,在某種程度上都與運河有關。飲食文化學者許先說:“‘九方雜居借河海漕運之興,溝通了南北餐飲文化的交流與借鑒。從津味醋椒魚、香榭蝦扁到杭州的西湖醋魚和龍井蝦仁;從津味的‘八大碗與津人飯俗到安徽的‘九規十大碗及扣模蒸食;從津味煎餅馃子、鍋巴菜到山東大煎餅;從津味八大扠、翡翠鴨舌到浙鲞閩糟;更有天津灶上的大炒勺順著大運河飄到了杭城戛然而止……這一切都展現了南北餐飲文化經過長期交流而遺傳下來的文化基因血緣。”正是由于大運河南北溝通,使得各地的菜系走向他處成為可能。飲食文化學者高成鳶認為:“運河交通必然帶來文化融合。‘天津菜的形成,肯定融會有淮揚菜的精華,狗不理包子的含有湯汁(高湯),就是有力證明。”許先也說:“縱貫祖國南北大地的大運河是一條文化紐帶,不但飄出了天津這一方熱土,更是給斯地凝聚了一腔靈氣。正是這股靈氣鑄就了天津近代餐飲文化的輝煌歷史。”又說:“津派菜的形成得益于大運河的孕育與培養,是祖國南北餐飲文化互相交流借鑒的結果,而新時代餐飲文化的發展,同樣也離不開大運河這個文化紐帶的串聯與凝力。”學者陳克也說:“有了運河,南方的食品也不斷地出現在天津的市場上,如廣東、福建出產的海參、魚翅、燕窩等干制水產品,江南的腐竹、干筍、火腿等特產以及各種調味品,極大地豐富了天津的餐桌。”因此,他說:“運河不但孕育了天津這座城市,而且給天津人帶來了各地的佳肴美味,不論是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都能在自己的圈子里共享祖先創造的飲食文化,同時天津人也為中國飲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大運河申遺成功以后,各地對大運河的保護利用日益重要,開展大運河研究更是重中之重。運河文化研究也成為重點,但系統性、整體性研究大運河與各地飲食文化的研究成果還不多。天津作為大運河的重要河段,其城市發展又深受大運河的影響,開展大運河與天津飲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未來,我希望探討運河與天津飲食文化的互動關系,既要探討運河對天津飲食文化的影響,是如何形成“運河薈萃八方菜”的?各菜系究竟在天津餐飲業當中占據什么樣的地位?這就同天津經濟社會史、城市生活史等聯系起來。同時我也想探討天津飲食文化又是如何借助運河走向全國的。通過這樣的互動研究,我想更能全面認識運河與天津飲食文化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