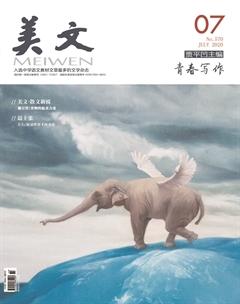食物的溫柔力量
戴呈哲
貴州貴陽,與臨近的昆明一樣有溫和宜人的氣候,山澤湖河,滋潤了菌菇蓀筍,各色時鮮異珍。那里沒有大城市高樓大廈林立的疏離之感,也不見鋼筋鐵臂的冰涼之姿,卻充滿了雨露陽光滋養出的香辛熱辣又熨燙人心的食物帶來的煙火至味、人間味道。
貴州最有名的小吃,當屬阿羅嫂家的雞蛋面。
在灰面放上攪打均勻的雞蛋液,壓面時用上一根粗而長的木棍,用人坐下時的壓力帶著木棍打在上面——當地人稱之為跳面。因處處是費時費力的工序,多數店家已不再使用人力完成這道決定面質的工序,而這家店卻仍舊不改傳統本色,沿用發揚至今,著實令人嘖嘖稱嘆。
經過反復揉搓的面已半熟,入鍋九秒便可出鍋,加上炸過的山珍雞、各色野物,秘制半年的臊味和其他調味料,最后再淋上一捧滾燙滾燙的豬油,食物的香味蒸騰四散,終讓無數慕名前來的食客為之神魂顛倒,思之如狂。
這種純手工制作的食物所帶來的美好,在面條輕觸舌尖那一刻便一展無余。而比單純的食物風味更為重要的是,藏匿在食物背后的制作者對待食物精益求精的態度,對用心做出一碗好面的追求——即便是這細微生活的淡淡一筆。但就是這隱約一筆,或許才是貴州阿羅嫂馳名的原因吧!
阿羅嫂的面,說起來就像是許多中國傳統美食一樣:色香味俱全,卻不是什么海味山珍。只是,在一絲一縷做面的過程中,承載著做面人溫良厚重的情誼。
而做面人阿羅嫂,自己經營著這家面館,在風晨雨夕中準時開張。她是這座城市里那些流落異鄉者、孤獨飄零者,以及土生土長的當地人的真正廚娘。百年不變,究其一生;默然堅守,無欲無求。她的丈夫已于四年前去世,而她自己在痛失愛人后,飽含著拳拳深情,守護著夫妻幾十年含辛打磨的食味結晶。她從早到晚,用心意,用青春,帶著愛的溫度做出美味爽口的食物,堅守自己人生的守望——守望著遠游漂泊的游子,守望著浩散離離于天地間的丈夫,守望著那一份恒古不變的至味真情,守望著那難以掩飾的傳統風韻。
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載著這樣的情懷,地道正宗的中國至味隱于人間、隱于山野。中國的食物亦是如此,精髓重在其間情誼,而非追逐技巧和食材的高檔精致。中國人的口味,往往亦如食物般源于祖國或母親特有的氣息。在這樣一個漂泊成為常態的時代,在異國他鄉,在午間飯后,在燈火初上,在夜闌人靜,在某個引人悵惘、泫然欲泣的瞬間,游子對家鄉的思念往往會借一道再普通不過的家常菜,占據心靈最柔軟的角落。
你未必聽說過“阜陽”這座皖北小城,但你一定在夢里見過她。西湖是歐陽文忠公筆下的婀娜蹁躚之姿,“行云卻在行舟下,空水澄鮮,俯仰流連”;是蘇東坡生花妙筆下的“大千起滅一塵里,未覺杭潁誰雌雄”,景致可與杭州西湖并稱。蘇東坡敬仰退居西湖的恩師,愛潁州閑逸的山河,愛著行經處的一切美食。食物是蘇東坡的最愛,他平生寫過三十多首贊美食物的詩詞,即使在苦辛的貶謫途中也不忘品嘗美食,并吟詠己見。蘇東坡在潁州期間一舉多得:不僅拜謁了恩師,恪盡職守,還邂逅了潁州的絕佳風味——格拉條。
相傳,蘇東坡在潁州任知府時,結識了東關的白老先生。他們談話甚是投機——除了談論詩詞歌賦,還互相分享美食。蘇東坡愛美食,更愛做美食,夢想嘗遍天下美食。他創制的“東坡肉”迄今仍是中國最美味、最知名的美食之一。一日,蘇東坡與白老先生說,自己已經嘗了他推薦的所有美食,不想再吃重樣兒的了。白老先生雖滿口答應,但還是犯了難。走在街上,忽然看見粉絲店掛著的粉絲,當即心生一計。他按照加工面粉的方法,把它們做成類似粉條的圓形面條,放在鍋里煮熟,再用涼水焯一下,放入大碗中。再加入芝麻醬、豆芽、豆角等配料,便完成了一道美食。東坡食之,大悅,問白老先生這道絕味的名稱,白老先生便用潁州方言作答:“擱拉擱拉。”東坡便道:“格拉條也。”
如今,隨著科技的進步,格拉條的口味和做法都得到了進一步完善:機器取代人工,使外形更加優美流暢;芝麻醬等醬料因機器生產而更加粘稠,散發著歲月流淌的醇香。曾經于家時,我總愛吃格拉條。一根根粗粗長長的格拉條和平常軟塌塌的掛面不同,它似乎有別樣的韌性,不如細的易折腰。或許是經歷了火海冰山的緣故,這面條特別有嚼勁,尤其是沾上粘稠的芝麻醬后,面食越嚼越香的特質和芝麻醬暗自清香的質料融會貫通,再添一抹香菜的清香,總會使我塵夢難醒。我總覺得潁州的芝麻醬有一股醇香的大自然氣息。芝麻的生命力很頑強,經歷風吹日曬仍是巋然不動,且越挫越勇,剛毅堅卓的品性與這獨特的面條高度吻合。食物果真是自然的饋贈,在婉轉的時光中抒寫生命的別樣印痕。
我,地地道道的皖北人,客居西南,對于桂北酸辣重油的口味著實不甚喜愛。但自從來到桂林,舌尖觸碰米粉的短短一瞬,就愛上了這座城市最簡單樸素的味道。從早到晚,米粉的香氣染遍了這山水之城中的每一株碧草,沖向每個人的毛細血管。我像是在寒風中尋寶一樣,盡情地嗅著這遍布大街小巷的食物的味道,追逐氣息,尋找有緣的米粉店。這飄忽的氣味使我覺得,即使在桂林特立獨行的冬季,呼嘯的寒風也無法蠶食我周身的溫暖,我甚至在風雨中盡情奔跑,笑出了一串酒窩。那靜臥在我光潔碗里的、一根根雪白的米粉,用它別致的軟語喚醒我對皖北風物的回憶。我雖常懷念那一碗碗裹著濃郁芝麻香氣、熱騰騰的格拉條,但當米粉用它絲滑的雙手溫柔地觸摸我的味蕾,那一絲專屬于桂林米粉的鮮香似乎總愛順著我的血液流淌,亦如水一般寬慰著我客居的心。“日啖米粉三兩多,不辭長作嶺南人”。不錯的,東坡曾到過嶺南,嘗過嶺南的荔枝,不悔貶謫,我亦因嘗過這桂林米粉而不虛此行。短短年歲,米粉亦漸漸消解了我繾綣的游子情。每當制粉的師傅麻利地盛好一碗粉,輕撒配料,在湯汁灌入白茫茫世界的那一刻,我被霧氣模糊了的雙眼仿佛看見這米粉幻化成我那家鄉風物的模樣。
我以為,不論是何種食物,尤其是手工所制者,之所以讓人吃之不忘、思之如狂,全在于斬淘切洗間的深厚情誼、添鹽減油時的深深思索、熬炒烹炸中的情思如縷。說到底,便無一不是中國人珍視傳統、根深蒂固的家的觀念,對傳統風味的不懈追尋。一生無論高祿厚秩還是勉強維持,在外無論是光鮮亮麗還是窮困潦倒,在那個時候,那個地點,總會有一盞燈準時亮起,傾注心意,生生不息——為你做一道道好菜,是這世間無二的尊重與撫慰。抑或不只食物,更在那食物背后的其他深意。也是這樣一種文化傳統,讓中國人能夠放心漂泊天涯,四海為家,為小家也為大家奔波辛勞,無怨無悔,讓人們不管走到哪里、泊于何處,時時永遠記掛著家鄉的山水人事,讓一切心事終有可停泊的港口。
“歌一聲,淚兩行,親人遠,故鄉香,夢中回,夜未央,月光光,照地堂”,今時今日,天南地北的異鄉人在城市的街道上交織涌動。中國發展催生出無數異鄉乃至異國之人,同時也帶來了文化與飲食的交融。出離與融入,相遇與訣別,構成時代匯合的大浪潮,掙扎拼搏、勇立潮頭的人們,無一例外在其間獲取到精神和物質上的補償,從而撫平傷痛,珍重過往,奮然前行。
食色,性也。食物所透露出的綿長情意,無論酸甜苦辣,都是中國人溫厚踏實的性情所在,是她對中國乃至世界情深意重的不朽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