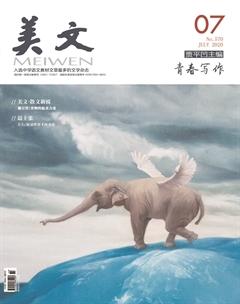瘞旅悲歌
靳超
疫情的冬日漸褪寒意,春夏的暖陽正值盛情。在這個(gè)不尋常的2020,我們看到了最美的逆行,我們生發(fā)了強(qiáng)韌的意志,我們感受了情感的溫度,我們也擁有了那份真摯的希望!對待生命,我們每個(gè)人都應(yīng)該懷著一顆樂觀之心去珍惜;對待生命,我們也應(yīng)懷著一顆敬畏之心去擁抱他人,審視自己。
一、瘞旅之悲歌
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在對待生死的問題上,孔子持有“存而不論”的態(tài)度。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對待生死的問題上,可謂給出了十分明確的態(tài)度:敬畏生命!
故事發(fā)生在正德四年的秋天。王守仁被貶龍場驛丞,在瘴癘毒氣的惡劣環(huán)境下頑強(qiáng)地生存著。在一個(gè)陰雨綿綿、天色陰暗的一天,王陽明從籬笆的縫隙中看到了一個(gè)從京城來的官吏,他帶著一兒一仆前去赴任,途徑龍場,投宿在當(dāng)?shù)氐拿缱迦思抑小5搅说诙鞂⒔形绲臅r(shí)候,有人來告訴他,有個(gè)老人死在了蜈蚣坡下,旁邊有兩個(gè)人哭得很是悲痛。王陽明一下子反應(yīng)過來:一定是昨天那個(gè)官吏死去了。傍晚時(shí)分,又有人來說:“坡下有兩個(gè)死人,有一個(gè)人坐在旁邊哭泣。”陽明推斷是官吏的兒子也死了。到了第三天,王陽明又從他人的口中得知:“看見蜈蚣坡下堆積著三具尸體。”原來他的仆人也死了!這是一件多么令人悲傷的事情!
王陽明眼見此情此景,心中油然而生一種敬畏之情——那是一種對于生命的敬畏之情!遠(yuǎn)在他鄉(xiāng),曝尸荒野,無人收殮,生命終結(jié)之時(shí)怎能如此地痛失尊嚴(yán)!于是他帶著兩個(gè)童仆,扛著鐵鍬和簸箕,一連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去埋葬這些原本與他無關(guān)的人。
二、同是天涯淪落人
在王守仁的心中,官吏的死何嘗不是千萬個(gè)客死他鄉(xiāng)之人的真實(shí)寫照呢?而王陽明也是其中的一個(gè)。古人不輕易離開家鄉(xiāng),外出做官也絕不會超過千里,而王陽明因直言上疏“逆瑾”而被貶謫到貴州龍場做驛丞小官,這是何等的無可奈何!龍場的瘴癘毒氣只是在侵襲著他的身體,更深的痛苦是來自于內(nèi)心的壓抑與折磨。在王陽明看來,死去的官吏又何嘗不是自己!他與官吏三人一樣,冒著風(fēng)霜寒露,在曲折的山路上走走停停,翻山越嶺,途中饑渴難耐,身心俱疲,又要忍受著瘴癘毒氣的侵襲,內(nèi)心所壓抑著的愁苦煩悶深深地郁結(jié)在心中!
于是,陽明給官吏做了一首歌詩,大致意思是這樣的:
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游子懷鄉(xiāng)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huán)海之中。達(dá)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龍場這樣的荒野之地,連綿的山峰與天相接啊,連飛鳥也不能通過。羈泊他鄉(xiāng)的游子懷念故土啊,辨不清西和東。辨不清東和西呀,只有天空在哪里都是一樣的。他鄉(xiāng)異地啊,也是環(huán)抱在四海之中。達(dá)觀的人四海為家啊,不一定非要有固定的住處。魂啊,魂啊,不要傷心悲痛!
三、真誠之心——每個(gè)生命都值得敬畏
生命的長短本身是不可預(yù)料的,生死的問題也是一個(gè)無解的答案。可是,我們對待生命理應(yīng)有著自己獨(dú)特的態(tài)度——真誠!
何謂以“真誠”的態(tài)度對待生命呢?“誠意”也是陽明心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精神。以生命為例,人是具有靈性的動物,而后期外界所賦予的名字、官職、稱謂、地位等均為性靈之外的東西。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拋開身外的名字、官職、稱謂、地位等一切的東西,我們的性靈與生命在本質(zhì)上是平等的。以此為起點(diǎn)出發(fā),我們對待每個(gè)生命都應(yīng)當(dāng)尊重,更應(yīng)當(dāng)敬畏,因?yàn)橹挥羞@樣,我們才能真正地做到“感同身受”,才能夠在他人的身上寄托“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思。而我們對于內(nèi)心的悲憤、歡欣、失意、痛苦的表達(dá)也才能夠真正地被他人所理解,所接受。
清代林云銘曾這樣評價(jià)《瘞旅文》:“掩骼埋胔,原是仁人之事,然其情未必悲哀若此。此因有同病相憐之意,未知將來自己必歸中土與否,觸景傷情,雖悲吏目卻是自悲也。及轉(zhuǎn)出歌來,仍以己之或死或歸兩意生發(fā),詞似曠遠(yuǎn),而意實(shí)悲愴,所謂長歌可以當(dāng)哭也。余讀先生全集,多見道之言,且行文自成一家,不傍他人墻壁,真一代作手矣。”盡管瘞旅是一件施行仁義之事,而若只是普通的瘞人之事,其情感根本不會如此地深沉。正因?yàn)橥蹶柮靼褍?nèi)心的“真誠”發(fā)揮到了極致之地,才有了真正的同病相憐與感同身受。因此,陽明瘞旅實(shí)則瘞自己,長歌當(dāng)哭也不僅僅在悲嘆吏目一家,更是在哀嘆自己悵惘的命運(yùn)。也正是在這樣的嚴(yán)酷環(huán)境下,王陽明絕處逢生,悟出了“心即理”的偉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