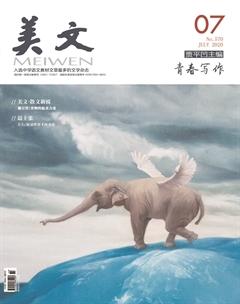悠悠端午艾草香
楊逸涵
拋開流傳淵遠的歷史故事,亦無濃郁的文化厚重感,這里的端午節(jié),只彌漫著艾草香。
20世紀(jì)50年代筑建的老舊小區(qū),斑駁的墻皮有些剝落,暗紅色的磚托起滿墻爬山虎,土陶盆中的茶靡味殆盡。院中楊樹下,午后暖暖的陽光,一張?zhí)贄l椅,一只收音機,一把蒲草扇,白發(fā)誰家翁媼。
“端午——端午——”小孩稚嫩的聲音劃過水靜般的午后,小貓似的叫著,跳著,鬧著。一會兒,一只老貓顫悠悠地走來,蜷在孩子腳邊。老人笑笑,輕撫著老貓。
時間倒退十三年。端午節(jié)那天,一只小貓正在貓舍打盹,被一位老人買走,領(lǐng)間系上了一條五彩絲繩。從此,它便叫“端午”了。
兒女忙于事業(yè),子孫異地求學(xué)。她與老人整日無所事事,“端午”成了他們的樂趣,老舊的家中迎來了新生命的氣息。“今年端午回來吧,我養(yǎng)了貓,都回來看看吧。”兩位老人用幾乎祈求的聲音,打遍了兒女的電話,笑盈盈地邀請孫子們回家看看。小小的“端午”在地上與彩絲繩逗玩。
小鋁鍋中沸水咕嘟咕嘟地冒著泡,拳頭大的粽子在水中微微翻動,粽香與棗甜溢滿小屋,混著艾草的清涼幽微。兒女們尋味而來,大人小孩,浩浩十幾人。許久未聽到老人這般爽朗的笑聲——兒女遠走高飛后,只剩父母在原地等待。
“端午——端午——”像逗弄滿月的嬰兒,老人拿著系了小球的絲繩,又捏一角粽子,眼中溢出了溫柔與慈愛。“涵兒小時候,也這么愛鬧。”小貓張著大大的綠眼睛,用沾了艾草香的腦袋,蹭老人干枯的手。黃昏的陽光,帶著溫柔的暖橙色余熱,照亮老人歷經(jīng)風(fēng)雨仍懷希翼的臉龐,照在“端午”毛絨絨的身上,將身影拉得細(xì)長,照在它綠色的眼睛里,把眸子鍍滿金黃。
老伴在一旁撥弄著艾草枝葉。電視里是龍舟賽直播,兒女喧笑間把晚餐端上桌,廚房的當(dāng)啷聲此起彼伏。不起眼的角落里,老人和貓,占據(jù)整個世界。
墻外的爬山虎,綠芽長了一層又一層;家中的艾草,每年準(zhǔn)時彌散出清幽的香氣;子子孫孫,借著“端午”的由頭,在端午相聚。巴掌大的“端午”被幾載粽香喂長了許多;活潑好動的性格在五彩絲繩的牽引下,變得怡然靜和。無需牽掛,無需命令,一個眼神,一聲輕咳,數(shù)年相伴,老人和“端午”,故友般心意相通。
午后的陽光依然是暖暖的,院中的楊樹已經(jīng)枝繁葉茂,“端午”依偎在老人身邊。細(xì)碎的陽光灑在“端午”略失光澤的毛皮上,照在老人眼角的皺紋上。
抿一口軟糯白粽細(xì)細(xì)品味,慢悠悠編一根五色絲,“端午——端午——”不再似從前硬朗,老人的聲音平添滄桑。“端午”悄悄從藤條椅下鉆出,伸長脖子,靜靜等待老人為它系上端午節(jié)的絲繩。“過了這個端午,你就十三歲了,我們兩個老人……”老人輕輕笑著,不再說下去,只把一角甜粽喂給“端午”,等著兒孫們前來拜訪。
露來霜往,年復(fù)一年,老人和“端午”一直相守,等待著端午這一天,粽香和兒女們的歡笑聲,一同飄灑在小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