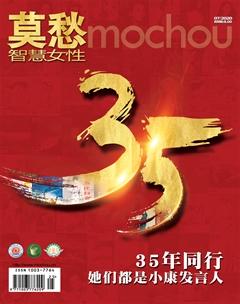追尋之路
吳躍農
每個人都有充滿期盼憧憬的懷想,有為之追尋的興奮、焦慮或忐忑。那是1990年夏,我從文藝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后,輾轉成為了中共江蘇省委統戰部的工作人員。放到現在,這可能是數百人競爭的崗位,但在當時,拿到報到通知書,對我來說卻是十分茫然和無奈的。
我在校期間已經發表過數十篇較有分量的文學評論,被《光明日報》譽為“著名青年評論家”,追尋專業工作顯然是我的不二選擇。為此,我當時放棄了去某外經貿機關工作的機會,執念于追尋專業工作。
社會不是按照個人擇業對口的想法而運轉的,追尋之中,我頻頻受挫,拿著省某某院文學研究所報到通知書興沖沖而去,卻被告知,通知書張冠李戴發錯了。就這樣,最后我通過省人事廳統一分配去了省委統戰部。
這是一個對我來說十分陌生的工作領域,要轉變成為統戰工作者,要轉變成黨委部門公文寫作者,現在想起來,這個轉變盡管開始是不自覺的,漸漸地變得自覺起來,很快,我就將工作視為專業,進入了狀態。
而《莫愁》,恰是我這個順利轉變過程中意想不到的助推和良師益友。
在省委統戰部圖書室,我讀到了《莫愁》,清新、健康、正能量,文章不深奧但不淺顯,故事不離奇但不平淡,總是那么娓娓道來,總是那么春風化雨,展現了改革開放大潮中人們齊心合力奔小康的精神風貌。《莫愁》成了我工作之余的必讀雜志,并漸漸有了向《莫愁》投稿的想法。
那時《莫愁》在團省委后面一個小樓辦公,上班途中,我試著將一篇散文小稿順路送去。看到辦公室堆滿的書刊,我心中免不了有點喜憂雜陳,辦公室好幾位編輯在埋頭工作,其中坐在最里面的是鄧曉文副總編。她接待了我,聽了我的介紹,說印象中讀過我發表在晚報上的散文,顯然有種“伯樂識馬”的欣慰,但她并沒有流露出來,而是在我透露出專業不對口的“委屈”之后,對我開導并鼓勵。
鄧曉文說話斯斯文文、輕輕柔柔,沒有長句和修飾,也沒有刻意強調什么,就像家常話一樣,但對于沉浸于專業執念中的我來說,無疑于醍醐灌頂,讓我瞬間清醒。
就這樣,我的第一篇統戰人物故事稿不久后在《莫愁》首發。我成了《莫愁》的忠實讀者和認真投稿者,讀《莫愁》、析《莫愁》,從《莫愁》的主題、欄目特色和謀篇,很好地掌握了《莫愁》與這個意氣風發、昂揚進取社會的積極互動關系,從中汲取了許多寫作智慧。
當年,市場經濟大潮涌動,難免泥沙混雜。一次,我參加《莫愁》舉辦的作者組稿會,印象極深的是,鄧曉文說:“一本刊物當然需要市場發行量,以取得刊物影響力,但我們不會迎合低俗趣味來辦刊,我們要用清朗正面、符合社會主義道德和價值觀的內容來安身立命,我們要以生動形象的故事內容來宣傳黨的方針路線,為我國、我省經濟社會發展和奔小康來鼓勁、來激濁揚清、來凝聚力量。”
現在回想起來,上世紀90年代可能是我業余寫作最高產的時期,我將工作中遇見的人和事,將所悟所想,利用周末節假日,以《莫愁》的用稿標準,寫出了一篇又一篇人物稿及散文,刊發在《莫愁》及中央許多報刊,成為全省統戰系統的“快筆”。
這又何止是寫一篇篇稿件。通過和《莫愁》在一起的機緣,通過《莫愁》的良師益友作用,我踏上了一條新的璀璨追尋之路,繼續追尋生命的那份純真,追尋工作和生活中的責任,追尋激動人心的新時代無悔和忠貞,追尋大愛無疆、大道無垠。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項目評審專家、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理事、中國商業史學會蘇商史副會長、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江蘇省工商聯一級調研員)
編輯 家英宏 xjjyh_32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