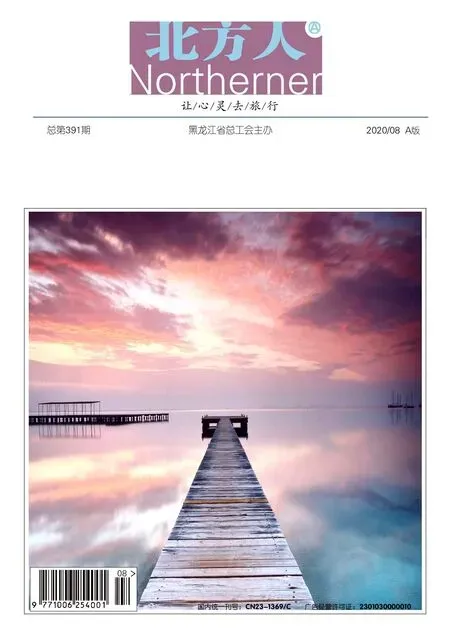中國癮
文/謝大剛

春節那天晚上,我的以色列朋友Amir一直心不在焉。我們4個以色列人在一個云南飯館過節。云南飯館的工作人員都是土生土長的云南少數民族,他們好像根本沒有看春節晚會的打算,那個晚上他們只有兩個打算:唱歌和跳舞。我們也隨他們混進瘋狂歡樂的氣氛中,毫無組織地唱起歌跳起舞。可是我的朋友Amir跳舞時似乎很難集中精力——用以色列土話來講,就是“他的頭放在別處”。飯館是在北京北三環上,而他充滿孩子般期待的眼睛不時往南邊看。“他們都說12點整鼓樓那兒會放煙花,必須去看看。”他靠近我耳朵,試著用很大的說話聲來戰勝音樂的吵鬧。“你急什么急,”我也大聲問他,“春節是每年的事情,明年后年都有機會看。我們今天在這里跳舞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體會。”“你不懂。”他用很果斷又帶著點委屈的聲音說,“我明年后年絕對不會在中國。明年得回以色列上大學了。”
他這個話對我來說沒有什么新意,事實上我知道,他是不會回去的。因為他明顯已經染上了“中國癮”。
畢竟我也是這樣過來的,我也曾經跟他一樣,處于一種堅決否認自己上癮的狀態。別人問我關于未來的打算,我會說:“還要留下兩三個月,有些事情得先處理完,然后再看情況吧。”可是當時自己已經很清楚我在自欺欺人。上了“中國癮”的癮君子們的一個大癥狀就是:他們都會用邏輯非常完美無缺的借口來告訴大家,他們為什么還不回國:“漢語水平考試本來準備考8級,結果只考了6級,我再學習幾個月重新考一次吧,考好了就回以色列。”過了幾個月后:“當時以為8級是漢語水平考試最高級別,沒想到原來還有11級的考試!11級考好了就回國。”再過幾個月:“考了11級不能代表什么。原來以為我中文還不錯,可是在復習的過程中,我走到了中文的另一個境界而對自己的中文水平獲得了新的認識,我切身體會到我的中文知識竟是如此淺薄。我下了決心:一定要把中文學好,看來還有必要留在中國……”
云南飯館墻上的鐘表快到12點了,Amir的舞蹈動作明顯表現出他內心的矛盾。他突然跑出去了,我也隨他出去。12點鐘的北京被煙花的風暴點亮。Amir站在那里,眼前不遠就是他那個晚上夢寐以求的“煙花王國”——鼓樓,而腳下的北三環上的天空只能給他一個煙花的二手感受。路上連續不斷開過能及時帶他去“王國”的空出租車,但是兩分鐘后他轉身回去了。他進了飯館,拿起桌上放著的一瓶啤酒,一口氣喝光,把瓶子放回桌上,然后又開始跳舞,跳得無比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