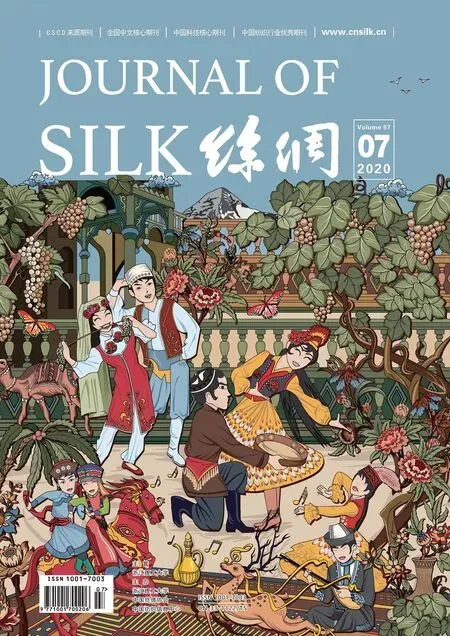無錫七房橋明墓出土紡織品紋樣題材特征與成因分析
崔 藝, 牛 犁, 崔榮榮
(江南大學 設計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明代絲織業發達,尤其是江南地區的紡織品無論是藝術形式還是織造技術都體現出較高水平。兼具江南商業經濟帶來的繁榮特色與士人集聚形成的審美流行,在紋樣造型、構圖、題材上衍生出復雜而多樣的形式,并作為記錄歷史的傳載體之一,投射出明代中后期江南的時代特點、地域文化與審美所向。
無錫錢氏家族是江南地區望族,歷朝歷代皆有俊杰,尤其是明清時代,涌現出眾多的政治家、文學家和著名學者。無錫七房橋錢樟夫婦墓的墓主錢樟(公元1486—1505年)及其妻華氏(1484—1528年)即是明代中后期無錫錢氏家族的重要成員。該墓發現于2012年,古墓保存完整,共出土了金、銀、銅、錫、瓷、木器及紡織品共百余件,其紡織品紋樣資料清晰,對于分析明代紡織品紋樣的藝術特征、文化內涵,以及對明代紡織品紋樣的解構再創造,提供了可靠的研究依據。
1 七房橋明墓出土紡織品及紋樣概述
七房橋明墓共出土相對完整的紡織品23件,另有殘片約13件。襖、裙、褲、鞋及其他服飾配件共18件,占全部出土紡織品的一半。帶有紋樣圖案的紡織品有16件,其中服飾共10件,作為底紋裝飾的暗花緞服飾占較大比重,多使用提花工藝織造而成,而應用于局部或緣邊裝飾的紋樣多為織金和納紗繡工藝制成,刺繡工藝也主要用于單獨紋樣或與其他花緞組合使用。其裝飾紋樣以花卉紋、飛鳥紋、雜寶紋、云紋及幾何紋樣為主(表1),雜寶紋自身多由體積較為小巧玲瓏的器物造型組合而成,通常與花葉紋或云紋等更易充實畫面的大體積紋樣搭配使用。在此墓出土服飾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花卉紋樣,應用于對襟夾襖、鑲邊絹襖、襕裙、膝褲、繡花緞鞋上;其次為雜寶紋樣,除織繡在服飾上外,也廣泛用于枕、被等紡織品當中。此外還有造型更簡潔的幾何紋,作為一種古代傳統裝飾通用紋樣也常見于服飾的緣邊。中國吉祥圖像在構圖上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滿”[1],人們為達到這種“滿而不擠,空而不虛”的理想畫面效果,通常會疊加使用不同題材的紋樣,并衍生出多樣的造型姿態。

表1 無錫七房橋錢氏夫婦明墓出土紡織品紋樣題材分類Tab.1 Classification of textile pattern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Qian Zhang and his wife in Wuxi Qifangqiao in Ming dynasty
2 紡織品紋樣題材構成與造型特征
明代的紋樣在傳統圖案基礎上,凝練升華以至高度樣式化,具有濃厚的裝飾美[2],具象的造型通過適當的夸張與變形,各類題材都得以巧妙地組合運用。七房橋明墓出土紡織品紋樣題材構成相對全面,涵蓋了植物紋、動物紋、自然氣象紋、器物紋、幾何紋樣等中國傳統的紋樣題材形式(表1),并在構圖平衡、造型寫實靈動、元素豐富的共性中展現出多樣的個性。
2.1 多元共生的動植物題材
動物、植物題材是中國傳統紋樣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兩種題材,至明清時期達到繁盛,皆被賦予多樣的吉祥寓意。據統計,七房橋明墓出土紡織品紋樣中植物紋樣的出現次數占總數的60%,動物紋樣占20%,遠超過其他題材圖案的出現頻次。植物題材以花卉表現居多,其品種形態各異,塑造的氛圍及藝術理解也不盡相同,動物題材屬飛禽、蜂蝶最常見。動植物題材在此墓出土紡織品中基本以組合出現,在四季花鳥紋襕裙的織繡紋樣中,由牡丹、荷、菊、梅四季花卉和三種姿態的鳳鳥共同構成豐滿且具有故事性的四方連續紋樣,如圖1所示。同為四方連續的雜寶朵花鳳蝶紋(圖2)元素組成略少,畫面留白,不似前者繁復,但保留了優美的動態流線。鳥銜花枝紋緞取用古代紋樣中一種典型組織形式(圖3),鳥與折枝花造型飽滿,布局均勻[3],形成固定圖形以二方連續形式進行重復,強調了視覺上的秩序感。

圖1 四季花鳥紋織金妝花緞襕裙及紋樣Fig.1 The Zhuanghua satin and woven gold fabric skirt with the pattern of four season’s flowers and birds

圖2 雜寶朵花鳳蝶紋樣Fig.2 The pattern of flowers, phoenixes and butterflies with Zabao

圖3 鳥銜花枝紋樣Fig.3 The pattern of bird holding a flower
值得一提的是,七房橋明墓出土紡織品中動物取材多樣,上述的鳳鳥、蝴蝶紋,以及在襕裙的三道裙襕中作為主要紋樣的獅子、奔鹿紋,還有在日月紋繡緞背袋兩面以單獨紋樣形式出現的三足烏與玉兔紋(圖4),由佛教、異域文化、民間習俗、神話傳說等內容提取而來。取材范圍之廣泛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對于多元文化高度包容與兼容性,精妙的組合與形態描繪更是江南地區織造技術發達、藝術審美獨到的體現,也側面印證了明代中后期求奢求異的社會生活風潮。

圖4 日月紋繡緞背袋Fig.4 The satin bag with sun and moon embroidery
2.2 祥瑞有序的自然氣象題材
明代織物紋繡中的自然氣象題材以云紋最突出(圖5),有四合如意朵云(圖6)、連云、靈芝連云等多種形式。七房橋明墓共出土4件裝飾有四合云紋的紡織品,在作為服飾面料的織造底紋時,通常以二方或四方連續形式進行重復與排列,另有散點式交錯排列和雙向連接等排列方法以呈現不同視覺效果,可與其他題材進行組合,也可作唯一元素鋪滿畫面。四合云紋盛行于漢代與明清時期,但在主體造型上明代更偏飽滿圓潤,延承傳統、追求創新,主體方正而穩重。流動感則由形態各異的云穗實現,這種造型特點在七房橋明墓及無錫錢氏墓出土紡織品紋樣上均有體現,循環偏小且多呈朵云狀,象征高升如意。云紋排布較之其他朝代秩序感更突出,是明代紋樣格局趨于程式化的重要體現。七房橋明墓出土的另兩件紡織品,日月紋繡緞背袋與緞枕中,祥云以角隅紋樣的形式裝飾在中心日月紋樣的周邊,營造主體紋樣的神話氛圍與充盈美感。

圖5 云鳳紋樣Fig.5 The pattern of clouds and phoenix

圖6 四合如意云紋樣Fig.6 The pattern of clouds
2.3 簡練小巧的器物題材
器物題材在中國傳統吉祥紋樣中較有代表性,無論在思想內涵或是表現形式上,都帶有傳統文化中儒、佛、道三家難以泯滅的印記[4]。通過將七房橋明墓出土紡織品紋樣與常州武進王洛家族墓出土作對比,可以發現前者在器物的選用上偏重道家雜寶,后者兼用了道家雜寶與八吉祥在內的佛家寶器,兩者在宗教特色上表現出的個性差異,一方面可視作明代中后期宗教交流盛行的體現,同時也反映著這一時期人們思想的自由多元。明代服飾中的雜寶紋相比清代顯得簡練樸素,紋樣周圍不飾彩帶或其他,雜寶紋內各器物造型都獨立且固定,紋樣體積小巧,基本以輔助其他題材作為組合紋樣出現。根據其他紋樣大小和繁簡,雜寶圖案的應用數量也不同。出土襕裙底紋中有六種道家雜寶,而在緞綿膝褲中,則附加了珊瑚、寶瓶兩種寶物,以填充空余;同樣的題材形象在不同的載體上也有所差異,對比圖7出土的兩件雜寶朵花紋紡織品,可以發現兩者雖在紋樣元素的選用及基本排列方式上多有重合,但在造型的描繪上后者精細復雜,嚴謹穩重,在視覺上實現了飽滿華麗的效果。

圖7 雜寶朵花紋樣Fig.7 The pattern of flowers with Zabao
2.4 靈動百變的幾何紋樣
除裝飾主體的植物、動物、器物及自然氣象紋樣題材外,明代中后期社會流行的紋樣尚有其他豐富的題材選取范圍,在七房橋明墓中出現的較為典型的是裝飾用的幾何題材。幾何題材紋樣多由點、線、面或常規幾何圖形按一定規律排列、交錯、重疊、連續構成的抽象圖案,在七房橋明墓出土紡織品中僅用于服飾緣邊的局部綴飾,以菱格形元素進行二方連續排列,其獨特的結構組織方式相對容易形成重復的節奏韻律,營造簡約且均衡的視覺效果。在菱格小花刺繡棉袖邊中融入植物題材,用幾何形式對花葉紋樣進行改造(圖8),增加了紋樣的裝飾美。明代織繡紋樣中使用的幾何題材花樣尤多,如無錫錢氏墓出土的龜背形幾何“卐”字紋樣(圖9)、嘉興王店李家墳明墓出土的菱格螭紋(圖10),亦反映了社會及個人審美趨于雅致的時代風尚。

圖8 菱格花葉紋Fig.8 The pattern of geometric flower and leaf

圖9 幾何“卐”字紋 Fig.9 The pattern of geometric "swastika"

圖10 菱格螭紋Fig.10 The pattern of geometric legendary dragon
3 紡織品紋樣題材的成因分析
明代社會的快速發展推動了紡織工藝的不斷進步,使這一時期的紋樣圖案進一步繁復而多彩,為社會審美與圖像藝術日漸個性多元化的變化提供了生長環境,帶有新的時代特點和文化內涵。此次墓葬出土紡織品紋樣反映出了時代性、地域性及錢家一門的審美個性,既凝聚了明代中后期的奢華風格與江南地區的文雅玲瓏,亦展示出錢家的文人風雅與名門奢華。
3.1 百花齊放:明代中后期審美的時代特色
在對無錫錢氏一系族譜進行核驗并對照墓葬出土報告記述后,可以基本推定七房橋墓葬主人錢樟夫婦入葬時間在明代中后期的弘治至嘉靖年間,從墓葬出土織物紋樣上就能發現織繡技藝的精細,圖案造型及題材的選用多樣。這與明代早期墓葬出土的紡織品紋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相比于明代初期經濟發展水平限制下全民節儉樸素的服飾風格,明代中后期的服飾趨向于夸張綺麗,這與自英宗以后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有著直接的聯系。以杭州、徽州等地為代表的城市地區商業活動日漸頻繁,這些經濟繁榮地區的生活方式隨之走向奢華,至嘉靖中期,杭州已“奢靡過甚”。這種追崇華麗風潮的盛行是全國性的,在日常頻繁的運輸交通助力下,對服飾華美奢麗的追求之風從江南地區向各個方向傳播,逐漸演變為明代后期社會統一審美。以南端的福建沿海泉州府同安縣為例,明代初“衣皆布素”,然中后期“往時市肆綢緞紗羅絕少,今則蘇緞、潞綢、杭貨、福機行市,無所不有者”[5]。
織繡紋樣圖案追求裝飾與內容的統一和諧,富有吉祥如意的文化內涵是中國服飾藝術的主要特征之一[6]。至明代,更是發展到“紋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花卉草木,因人而活,因人生義。不僅具有審美觀賞的形式意義,而且直接具有了人格的意義[7]。這種吉祥文化的加持也使得人們對于紋樣的追求愈發熱烈,造作者以新式誘人,游蕩者以巧治成習[8],與奢靡的社會風氣共同作用表現出百花齊放、奇思巧意的時代審美風貌。
3.2 士奢漸興:江南地區審美的地域特色
江南地區作為明代經濟最為繁榮的區域,紡織業水平之高更是當時國內代表,發展速度也遠超其他各個地區,一度成為引領服飾時尚潮流的中心。織工高超技藝的支撐,使得江南地區的織繡紋樣相比于其他地區更顯精致,江南水鄉風土下形成的人文風貌也影響了服飾圖案的藝術風格。相比于北方地區飽滿充盈的圖案造型與構成形式,江南地區的紋樣造型整體上偏向嬌小,在構圖上會留備出空白,在視覺效果上與中國畫藝術中的留白技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江南文化所呈現的全面的審美追求及精絕的審美情趣,歷來被人稱道[9]。其地域審美呈現出奢麗與雅致兩種特點:一方面,吳越物質財富的豐富、商品大潮的沖擊、市民階層的壯大,以及富商大賈的增多使人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發生了根本變化,形成了“吳俗奢靡為天下最,暴殄日甚而不知返”的社會習氣并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淳樸儉約之風[10],服飾織繡華麗之盛,堪居當時之首。另一方面,江南晚明士大夫文化引領下形成的社會風氣與生活方式促成其獨特。明代士人群體集結的主要形式是書院和結社,而書院與結社在江南之蘇州、浙江之杭、嘉、湖乃為尤盛[11]。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又對士人的價值取向產生了某些影響,加之來自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這一時期的江南士人在精神層面上出現了疏離傳統“溫良恭儉讓”的儒生形象,轉而追求張揚個性、風流殊異的名士風度[12]。明代后期占有和消費奢侈品逐漸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于是士、商階層便踴躍地成為貴族以外的消費主體[13]。士商關系轉變,交往日益深入,似是趨同,然士大夫保有其文人優越感,又在一些方面刻意區分與從商者的差別,以提高生活方式的品位情趣、藝術文化的方式彰顯才子素養。作為全國最早形成奢侈風尚的江南地區,士人們“求異”“求新”的處世態度與審美情趣引領了脫俗反叛的潮流,當地名門大家的雅致審美更是深刻影響并推進了明代晚期其地域審美流行由一味的追求世俗奢美向雅氣的漸變。在這種獨特的水土文化與社會風氣的作用下,形成了江南地區獨到的玲瓏小巧、富麗華美的審美思想與雅致而破俗的士大夫文化風尚,并融入社會生活方式,表現在服飾紋樣這一載體之上。
3.3 氣質升華:錢樟家族審美的個性表現
明代社會審美經歷了從最初的壓抑到中后期的求新,經濟與技術的實力積累推動了社會思想的自由與解封。七房橋墓葬主人錢樟出身于錢氏家族,為錢镠的二十世孫,其家族在江南一帶極負盛名。錢氏為無錫望族,雖無官職,然與相往來者均為一時名流,尤與鵝湖華氏關系密切。從墓葬出土的服飾紋樣來看,其紋飾所占比例之多,花樣之盛既凸顯了錢家雄厚的經濟實力與較高的社會地位,同時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生活在民間財力富足者對華麗的服飾及紋樣熱情追求的普遍風氣。通過在服飾上應用大量的織金紋樣或其他工藝織成的精細紋樣,彰顯出著裝者個人或家族的經濟實力。在強化服飾紋樣標志功能的整體社會風尚中,主觀審美不斷分化,服飾紋樣的審美從一味地爭華求奢逐漸“雅”“俗”分流,內斂而有節制的紋樣造型成為如錢氏家族這一類大家族內的文人學者追求雅致審美的表現,將著裝者個體對美的感知與生活方式選擇的獨特性具象于平面。
明代中葉以后商業的不斷發展必然促進了其他家族的興盛,形成了繁簡不一、不同取向的紋樣審美風格,并與錢樟夫婦墓出土服飾紋樣共同構成了多元統一的社會審美特性,也印證了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甚至外交都在向著新的歷史高度發展,以及延續幾千年的封建統治階級制度已然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開始出現裂縫的跡象。
4 結 語
無錫錢氏家族作為江南地區具有代表性的望族名門,其使用的紡織品反映了江南一帶的社會發展水平及地域特色。無錫七房橋錢樟夫婦明墓出土服飾紋樣題材構成上多元豐滿,構圖充實均衡、繁而不亂,這與明代中后期矛盾而典型的時代風格相呼應。社會普遍性的奢侈化風尚,以及在追崇欲望的過程中產生的文人個性情趣,在思想的摩擦與碰撞融合中共同展現出這一時期復雜新穎的美學特色。通過成因分析,為人們展示了明代中后期以來江南地區的審美現象特征,也體現著江南紡織業經濟與技術上的發展與興盛。

PDF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