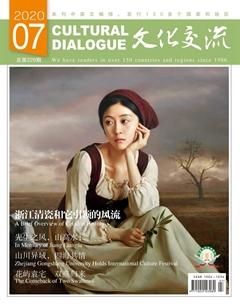云飛江岸白日落海門紅
林新榮



平陽的林景熙,是南宋的詩壇名流。他的《飛云渡》經常印在瑞安一些畫冊上:‘‘人煙荒縣少,澹澹隔秋陰。帆影分南北,潮聲變古今。斷峰僧塔遠,初日海門深。小立蘆風起,乘槎動客心。”
飛云江位于瑞安市,系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為浙江第四大河、溫州第二大河。飛云渡足飛云江上的最大渡口,也足詩路浙江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四曰:“飛云渡,縣南七里,安陽江津濟處也。波流洶涌,橫截南北,有飛云關,往來者必出于此。”昔日熙熙攘攘的飛云江渡口,已慢慢衰落了,這足歷史的必然。作為當年浙閩的重要通道,千百年來,經過了多少旅人,又留下了多少可圈可點的詩作?
陸舜,字符升,號吳州,江蘇泰州人,康熙三年(1664年)進士,官至浙江提學道、舉博學鴻儒科。他足哪一年于此過渡已不可考,但歲月卻留下了他的《飛云渡》:“百尺飛云渡,晴飛滿壑云。滄桑四時變,閩越一江分。海色陰還見,邊聲靜不聞。莫言春汛早,廟算正殷勤。”廟算,原指朝廷對戰事的謀劃,此處指占卜吉兇,祈求神靈的護佑。此詩有所思、有所想,是難得的佳作。
梁章鉅,字閎中,號茞鄰,晚號退庵,福建長樂人。清嘉慶七年(1802年)進士,官至兩江總督,因其子梁恭辰署理溫州知府,梁章鉅也多次往返于東甌:“客子行不息,大江流未央。渾渾夕照沒,四面天容黃。橫空一葉去,太波與低昂。北岸近可唏,東顧何茫茫。魚龍海氣腥,鷹隼風力強。大星掩洪耀,南人真堂堂。如何傳者誤,重碇翻危檣。孤忠會激發,青史當闡揚。愧非濟川楫,臨流相感傷。”(《飛云渡》)。他還可能足渡口留詩的職位最高官員。
平陽的林景熙,淳熙七年(1271年)進士,是南宋的詩壇名流。平陽和瑞安屬隔壁,他在兩地來往頻繁,他的《飛云渡》經常印在瑞安一些畫冊上:“人煙荒縣少,澹澹隔秋陰。帆影分南北,潮聲變古今。斷峰僧塔遠,初日海門深。小立蘆風起,乘槎動客心。”這位宋末的遺民詩人,借景抒情,這種淡淡的愁緒足合乎心境的。
有意思的足,有些沒來過渡口的,也留了詩。如明朝的梁有譽,因為朋友任職,寫了長詩《送同年劉朝宗之任瑞安》,其中有四句“飛云渡口千家樹,梅雨潭邊百丈流。海氣蒸人長似夏,山光依郭迥官秋”。真不愧足嘉靖年間的進士,對仗工整,體物人微,幾乎無可挑剔。可見,飛云渡在歷史上是相當知名的。
所以這個千年津渡,有時就成了送別的“灞橋”。曾任部虞衡司郎中的皇甫汸,足嘉靖八年(1529年)的進士,他寫了一首《發平陽王子追送飛云渡感泣而別因寄》:“相逢忽漫路岐臨,相送停舟酒重斟。目引海云飛處盡,心隨潮水渡時深。芳洲總惜人遲暮,花縣那堪歲載陰。李白從來稀下淚,問君何事獨沾襟。”瀆了不由令人落淚。另一首,足宋代平陽進士林亮功的《送友至飛云渡》:“五里風濤路,人煙隔岸洲。去帆欹綠水,別棹會中流。西峴鐘聲曉,東山塔影浮。何人有機事,驚起一沙鷗。”這個林亮功真足情深意切,令人敬重,送友人竟一路送至渡口。
自稱章安鄭敷榮的樂清詩人,則可謂別出心裁。他的詩叫《峴山登眺》:“峴閣勢崇隆,登臨四望通。風米波浪急,雨過海門空。日落千山外,帆歸一鏡中。眼前無限趣,領略與誰同。”詩中的峴山,即西峴山,古時護城墻跨其上,山外可俯瞰飛云江。他這詩即寫渡口,又寫飛云江,可謂一舉兩得。
本地寫渡口的就更多了。林亭,生卒不詳,字性端,明弘治正德年問瑞安豐湖里人,其《飛云渡》云:“泥涂新甏路何賒,十里長堤涌白沙。病涉無詩歌苦葉,候津有客倚仙槎。拍岸怒潮春雨后,隔江疏樹夕陽斜。湯湯不用愁無限,南北于今總一家。”詩寫得中規中矩,但欣喜多于愁苦。
如再分類,有寫曉渡的,有寫晚渡的,如項傅梅、鮑作雨等人。如項傅梅《云江曉渡》:“鼓椏在舟中,渡頭日未紅。殘星光若月,曙海氣猶虹。島樹微難辨,鄉村遠望通。云江潮落后,天水色澄空。”這個項傅梅,寫一首還不過癮,再寫了一首《曉過飛云江》:“南郭侵星出,乘潮喚渡喧。江空風有影,天曙月收痕。浪靜如行鏡,云開見遠村。茫茫東大海,霞氣暈朝暾。”另有余永森,字庭樹,號蓉谷,乾隆三十九年舉人。他賦詩《曉渡云江》:“聲飛泊泊暮江頭,兩岸云迷水色悠。山雨暗連城廓晚,風濤寒上海門秋。浪飛濺雪千層迭,沙嘴乘潮一線浮。安得御風同快馬,橫飛檣櫓踏中流。”詩作色調沉郁蒼茫,勾勒出一個雄渾、虛幻、壯闊、豪邁的意境,特別是后四句,就像一幅波濤洶涌的巨幅山水畫。李縉云,清朝詩人,他寫的《晚過飛云渡》云:“雖值蛟龍臥,奔流勢自雄。云飛江岸白,日落海門紅。小艇穿層浪,孤帆飽晚風。俄升瓊島月,光射水精宮。”這詩就像一幅精致的工筆畫,滲透出一種悠遠、廣闊、空靈的意境,清悠而浪漫。
當然,稱得上佳作的還有林齊鋐的《晚渡飛云侍文侯伯兄》:“一帶斜陽動海瀾,輕舟鼓棹晚風寒。鵲鸰原上蘆花白,鴻雁洲前楓葉丹。倒盡清尊談未倦,歌余高燭夜將殘。小樓長枕邀余臥,涼月依依照曲闌。”在晚風吹拂中,詩人的心中往事歷歷。文字色彩明麗,意境清遠,情隨景至,清芬有度,特別是后4句,寥寥28個字,生活氣息撲面而來,顯示了詩人深厚的功底。
端木國瑚,字子彝,道光十三年進士,青田人。他有一首《飛云江候渡》:“橫陽潮信上,帆席候多時。江響秋風早,天寒曉日遲。三條官渡急,一剎佛竿危。待上龍山去,琴高訪阿師。”這位周易專家,晚年定居瑞安,在詩中他急著過渡去訪友人。我很奇怪,他是定居在飛云江畔嗎?不知他到隆山訪的是哪位禪師?端木百祿,端木國瑚長子,道光己酉拔貢,他有一首《渡飛云江》詩:“一葉云江外,天青接海門。風追帆勢猛,潮人市聲喧。客夢煙巾寺,鳩啼雨后村。孤行不得泊,愁絕易黃昏。”真的足有其父必有其子,連脾氣都差不多,因潮急,不能靠岸,也是心急如焚。
最有意思的是俞樾,作為瑞安人孫鏘鳴的好友,在瑞安,他一邊留戀東海的黃花魚,一邊想家:“瑞安學士最依依,夜雨留賓靜掩扉。杯酒清淡偏有味,黃花魚小墨魚肥。”“飛云渡口水茫茫,歷歷風帆海外檣。江面亂流行十里,依稀風景似錢塘。”他“自福州還杭過瑞安”,不過半日,就給瑞安留了兩首詩。
瑞安還有詩僧。曉柔法師,字廣和,號卍蓮,俗姓楊,平陽縣鳳巢人,清時為常寧寺和尚。常寧寺在江溪,初建于唐成通年間,現在改建為瑞安市農業技術學校,僅存兩根石柱,甚惜。他有一首《晚過飛云江候渡》:“日落江亭晚,參商得未曾。萍波流不定,蘆筏愧無能。月向空舟度,城懸隔水燈。參差愁里望,郁郁老僧膺。”短短的候渡時光,心里還在想著參禪。釋大川,號小默,光緒間天王寺和尚,有一首《江口待渡》:“日暮江頭霽色開,行人欲濟待潮回。落霞孤鶩齊飛處,無數歸舟點點米。”盡管第三句似曾相識,但并不妨礙我們對詩意的理解,短短四句活畫出了一幅日落江頭的興旺景象,使飛云江的生活情景再現。另一首《漁婦賣魚》就更有生活氣息了:“幾多小艇蓼汀歸,無數沙鷗水面飛。泛宅漁婆皆上岸,沿街叫賣鯽魚肥。”
這自古興盛的渡口,自大橋通車后,就繁華不再了。但足它豐厚的人文積淀,特別是古今詩文,卻值得我們整理與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