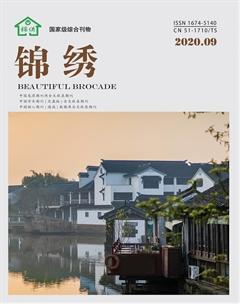含道暎物,澄懷味像
摘 要:南朝宗炳(375年-443年)的《畫山水序》是一篇重要的山水畫理論著作,它是中國傳統山水畫注重主體精神以及理性思想的基礎來源。他的探尋之路深耕于中國傳統藝術文化語境之中,首次將藝術與社會聯結點寄托于“道”,通過對于“道”的探索,進而實現藝術領域“審美烏托邦”的建構。所以本文擬從宗炳《山水畫序》文本出發,探求其文本中對于“道”的定位,以及“審美烏托邦”社會建構的內在機制。以期對于宗炳藝術畫論進行深層內核的探尋,同時實現對當代藝術發展方向的指引。
關鍵詞:《山水畫序》;道;審美烏托邦;含道暎物;澄懷味像
一、“審美烏托邦”建構的本始——“含道”
對于山水畫創作的本始,宗炳聚焦到了對于“道”的討論,他認為只有審美主體胸中“含道”才能進行審美活動。對于“道”的理解,成為了探討宗炳美學藝術觀點的起點。
宗炳關于“道”的理解受到魏晉文人隱士“玄學”的直接影響,同時兼具儒釋道等文化的交融性影響,所以他關于“道”的理解帶有了一定的融合性和開創性。他的“道”,尚自由,是從現實生活中升華提煉而來的,但是最終又歸依與精神世界的完滿和諧,從而規避了道家的虛無夸偽,儒家的社會功利束縛,因而體現出了與儒道兩宗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藝術的精神正在與透過現實的繁蕪,超越有限的生命,去追尋審美活動的自由。”他將“道”的自由精神,從現實引向了繪畫,使得其后的山水畫的發展帶有了人性的靈動和天人合一的靈氣。從“道”出發,寄情于現實山水的壯美審視,在山水意境中遨游暢神,從而獲得美的體驗,使審美主體在現實與虛境之中,以山水藝術為媒介建構起了“審美烏托邦”的雛形,從而達到“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審美意境。
二、“審美烏托邦”建構的前提——“澄懷”
“含道”與“澄懷”都是宗炳在現實生活中對審美主體進行審美活動的前提限定,都是為實現關照自然山水而進行的自我凈化,但是兩者也存在著本質性的區別。“含道”更側重于人性的本原的限定,是對世界本原和人類本原的內在聯結。但是,“澄懷”更突出的的是人主體意識控制下的精神狀態,是每個人都可以調整接觸的人生姿態。對于兩者的辯證來說,審美主體擁有“含道”之質后,可以主動的選擇“澄懷”的運行機制;但是,缺少了“含道”之質的支撐,“澄懷”的意義便不復存在了。可以說,“含道”是“澄懷”的本源基礎,但是兩者的作用層次和方向又存在著差異。
對于“澄懷”究其字義而言,乃“澄凈胸懷”之意,是在審美主體精神控制之下達到一種“虛靜”的狀態,而這種“虛靜”狀態雖然受“含道”的影響,但實則是在“澄懷”功效之下的直接產物。宗炳所提出的“虛靜”受時代的限制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諸多學派的影響,但是對于“澄懷”之效是統一集中的。“澄懷”提倡虛其懷,靜其心,以致“虛靜”。“澄懷”強調的是一種在主體控制之下的超功利性,虛靜空明的無我之境,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能夠實現現實向理想“審美烏托邦”引渡的可能。這里的“虛靜”其實與康德提倡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有著相似之處,都強調放空主體的欲望和功利意識,以進行純粹的審美活動,進行美的關照,同時也為審美途徑的預設進行鋪墊。
三、“審美烏托邦”建構的途徑——“味像”
審美主體“含道”、“澄懷”等限制已然確立,對于審美客體的自然山水的“質有”、“趣靈”也進行了討論,那么將兩者相聯結的現實路徑就顯得尤為重要。所謂“味道”,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老子,他說“‘道之出口,但乎其味”,這里所說的“味”是聽他人述道的思考和體現,是一種精神的愉悅和審美性的體驗。“像”的本體是“道”,通過“味像”能夠使山水以‘形顯“道”進而形成審美活動中符合主客體審美需求的審美對象。
關于“味”的在審美活動的運行機制,宗炳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含道”的基礎之上,面對審美客體的存在,如何關照欣賞成為了影響審美功效的重要原因。對此,他提出了面對自然山水欣賞時的“二重構境”,即“眼觀”、“心味”。對于自然山水的欣賞首先是要建構在自然之物的移置,將審美客體轉化為主觀印象。宗炳提出的“味”并不是將自然之物等大、等形的移置,而是要達到“畫家的眼睛流動著漂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把握全境的陰陽開闔,高下起伏的節奏。”從而將自然山水自由靈動的游動到審美主體的印象之中,通過收縮或擴展以達到自然山水的時空轉化,從而實現“眼觀”的目的。緊接著,在審美主體的身心調動之下,對移置進的自然山水印象進行審視關照,結合自身的審美經驗和審美習慣,通過“心味”以達到與自然山水的共情,使得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之間能夠達到自然交融,促進審美活動的超自然運行。
因此在“眼觀”與“心味”的二重構境之下,宗炳的自然審美路徑得以實現和發展。結合個體生命體驗和審美體驗的交匯,使得基于個體性的“審美烏托邦”建構形成了雛形,具有了勾連自然與理想之境的現實化路徑。
四、“審美烏托邦”建構的回溯——“暢神”
在審美主體的“含道”與“澄懷”已達到內在提升凈化后,通過對于審美客體的“二重構境”以進行“味道”,從而實現了基于個體層面的單向審美歷程,勾連起了個體的生命視覺和個體的主觀感受。但是這種基于個體生存體驗的審美歷程,創作者和欣賞者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主體,那這種個體嘗試下的“審美烏托邦”如何能夠通向現實的普遍性和超越時空的神圣之感,便是宗炳接在《畫山水序》中所論述的焦點。
關于“暢神”的定義眾說紛紜,但關于其本質性的內涵都是大致相似的,因而本文將“暢神”探討的重心聚焦于其在審美活動中的功效發揮,以此來進一步梳理宗炳的思想。對于“暢神”超功利性和超現實性的精神自由,其價值上與“含道”存在一定的黏連性。但是其可貴之處在于,它在哲學層面的“泛靈化”,它賦予宇宙萬物以靈性,并且進一步引申為美學領域的精神氣韻的范疇,與審美本體和自然萬物相呼應,以達到“個體與‘道冥合、與物具化、與神物游的境界。這是人的心靈在自然山水中獲得真正自由的狀態。”話句話說,就是使得宗炳“審美烏托邦”的“道”化建構具有了現實的普遍性支撐,并且形成了審美主體與“審美烏托邦”社會的雙向互動性。因而使得“審美烏托邦”的現實性功效能夠借“暢神”得以反饋,使得世間的獨立個體都能夠得到“道”之感化,從而規避了唯圣賢才能夠進行審美活動的限制。
通過已得“道”之圣賢的凈化超脫,使得“審美烏托邦”的現實建構得以實現,進而反饋現實社會,促進審美經驗的廣泛傳播,提升普泛個體的審美積淀,從而也能夠參與“審美烏托邦”的建構。這樣在宗炳的山水畫序中就形成了一個依托于“道”的“審美烏托邦”的建構循環路徑,從而將“道”之精神由精神領域引入山水畫作的藝術領域,實現了“道”之精神的重要探索。
作者簡介:
蓋平運(1999-);性別:男,籍貫:山東煙臺,學歷:本科,現就讀于山東師范大學;現有職稱:無;研究方向:美學、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