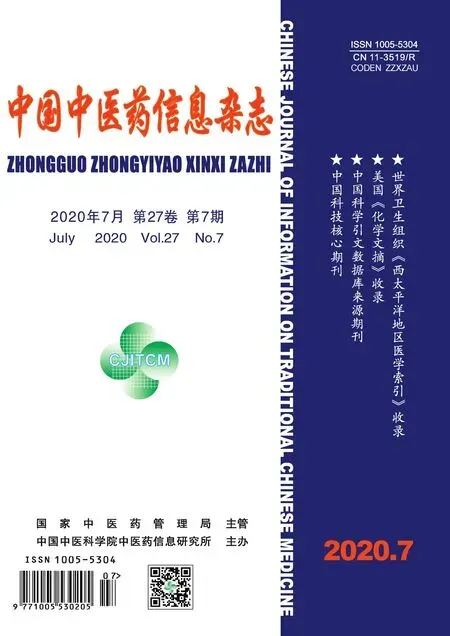重慶市萬州區80 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臨床特征及證治分析
龔新月,魏大榮,龔雪,熊燕,汪譚,牟方政
重慶大學附屬三峽醫院,重慶三峽中心醫院,重慶 404100
2019 年12 月以來,我國湖北省武漢市陸續發現多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2019,COVID-19),隨著疫情蔓延,我國其他地區及境外也相繼發現此類病例[1]。因重慶萬州與湖北接壤,湖北務工返鄉人員較多,導致COVID-19 在本地流行。COVID-19 屬中醫學“寒濕疫”“濕溫”范疇,疫毒外侵,肺經受邪,正氣虧虛而致病,病理性質涉及濕、熱、毒、虛、瘀[2]。本病具有強烈的傳染性和流行性,《溫疫論》曰:“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從口鼻而入。”
重慶大學附屬三峽醫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重慶市集中收治COVID-19 的定點醫院,疫情發生后,中醫內科迅速成立中醫會診專家組參與一線臨床會診任務,保證患者早期、全程、規范使用中藥。在臨床救治同時采集患者中醫證候并及時分析病機演變過程,這對于確定疾病的證型及治法十分重要,早期運用中醫藥對疾病進行精準干預,有利于疾病恢復,降低疾病轉化成重癥的幾率。本研究通過對重慶市萬州區80 例COVID-19 患者臨床特征、中醫證候及相關指標進行分析,為相關治療提供借鑒。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按入院順序納入本院2020 年1 月23 日-2 月9 日80 例COVID-19 患者。本研究經本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2020-7 倫)。
1.2 西醫診斷標準
依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四、五版)[1,3-4]制定COVID-19 西醫診斷標準。按照標準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
1.3 中醫辨證標準
參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四、五版)[1,3-4]及重慶市萬州區衛生健康委員會《萬州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藥診療推薦方案(試行第一版)》,結合本地患者情況制定COVID-19辨證標準。①邪犯肺胃證。主癥:惡寒發熱,酸痛乏力;次癥:或咽痛干咳,或口干口苦,惡心嘔吐,腹瀉;舌脈:舌質淡紅或紅,舌苔薄白或白膩,脈濡。②濕毒郁肺證。主癥:反復發熱,中低熱為主,身熱不揚,或高熱,或無發熱,胸悶,活動后氣喘;次癥:或咳嗽咯黃痰,或白痰,或口干口苦,便秘;舌脈:舌質紅或淡紅,苔黃膩或厚膩而少津液,脈滑數。③氣陰兩虛證。主癥:熱退乏力,氣短汗出;次癥:唇干納差;舌脈:舌質紅,苔少或苔薄少津,脈細或細數。④肺脾氣虛證。主癥:神疲乏力,氣短,納差;次癥:咳嗽無力、咯白色泡沫痰,口中無味,大便稀溏;舌脈:舌淡紅,苔薄膩,脈細。
1.4 資料采集
所有參與資料采集的醫生均經前期統一培訓。于患者入院第1 日由固定的副主任醫師采集患者流行病學史、實驗室指標[白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C 反應蛋白、白細胞介素-6(IL-6)、CD4+計數、CD8+計數]、胸部CT、舌象、脈象。在充分光線下用手機拍攝患者舌象圖片,8:00-10:00 由固定的副主任醫師采集脈象,由4 名主任醫師進行中醫辨證。實驗室指標由本院檢驗科統一檢測;胸部CT 由本院放射科完成,報告書寫由放射科主任醫師統一審核。
1.5 納入標準
①年齡≥18 歲;②符合COVID-19 診斷標準的輕型、普通型、重型住院患者;③患者對本研究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6 排除標準
①危重型COVID-19 患者;②合并其他慢性呼吸道疾病、呼吸系統細菌感染如化膿性扁桃體炎、急性氣管-支氣管炎、鼻竇炎、中耳炎等影響臨床試驗評估的呼吸道疾病;③合并嚴重心腦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慢性肝腎功能損害、腫瘤及重大手術病史者;④伴有嚴重原發性免疫缺陷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先天性呼吸道畸形、先天性心臟病、肺發育異常等基礎疾病;⑤情緒抑郁、過度焦慮、精神障礙不能配合者。
1.7 療效標準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四、五版)[1,3-4]制定療效標準。①臨床治愈:符合解除隔離和出院標準,即體溫恢復正常3 d以上,呼吸道癥狀明顯好轉,肺部影像學顯示炎癥明顯吸收,連續2 次呼吸道病原體核酸檢測陰性(采樣時間間隔至少1 d),可解除隔離出院或根據病情轉至相應科室治療其他疾病;②有效:體溫逐漸下降,5~7 d 內體溫正常,咳嗽、納差、腹瀉、乏力、氣促、口干、頭痛、惡寒、咽痛癥狀經治療后逐步好轉;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冠狀病毒2(SARS-CoV-2)核酸咽拭子檢測在第12 日后隔日1 次,2 次陰性;③無效:體溫不降或持續升高,5~7 d 不能恢復正常,咳嗽、納差、腹瀉、乏力、氣促、口干、頭痛、惡寒、咽痛癥狀不能好轉并進一步加重;SARS-CoV-2 核酸咽拭子檢測在第12 日后隔日1 次,任何1 次陽性[5];④死亡。
1.8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采用描述性統計方法,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x±s表示,計數資料以頻數/百分比表示。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80 例COVID-19 患者中男45 例,女35 例,男女比例為1.29∶1。年齡18~82 歲,平均年齡(54.20±12.76)歲。西醫分型以普通型居多(62.50%)。62 例(77.50%)有明確武漢/湖北旅居史,13 例(16.25%)有明確與確診人員接觸史,5 例(6.25%)無明確流行病學史。20 例(25.00%)有基礎疾病(糖尿病、高血壓、乙型病毒性肝炎)。詳見表1。
2.2 臨床癥狀分布
80 例COVID-19 患者臨床癥狀按頻次分布由高到低依次為咳嗽64 例(80%)、發熱54 例(67.50%)、納差32 例(40.00%)、腹瀉30 例(37.50%)、乏力22 例(27.50%)、氣促21 例(26.25%)、口干20 例(25.00%)、頭痛10 例(12.50%)、惡心8 例(10.00%)、惡寒7 例(8.75%)、咽痛6 例(7.50%),少數患者無明顯臨床癥狀。詳見表2。

表1 重慶市萬州區80 例COVID-19 患者一般資料

表2 重慶市萬州區80 例COVID-19 患者臨床癥狀分布
2.3 中醫證候特征
80 例COVID-19 患者舌質以紅舌、淡紅舌為主,舌苔以厚/膩苔多見(56.25%),脈象以滑脈為主(60.00%)。中醫辨證分型以濕毒郁肺證最多(53.75%),其后依次為氣陰兩虛證(25.00%)、肺脾氣虛證(11.25%)、邪犯肺胃證(10.00%)。詳見表3。
2.4 實驗室檢查
80 例COVID-19 患者胸部CT 以多肺葉下野外帶病變為主,白細胞多無明顯變化,多見C 反應蛋白升高,淋巴細胞計數降低,CD4+、CD8+計數降低;重型患者表現為白蛋白偏低、IL-6 水平明顯升高。詳見表4。

表3 重慶市萬州區80 例COVID-19 患者舌脈及中醫證型分布

表4 重慶市萬州區80 例COVID-19 患者實驗室指標不同分型情況(例)
2.5 方劑使用情況
從分型看,輕型患者應用頻次最多的方劑為麻杏石甘湯、荊防敗毒散、銀翹散;普通型患者使用頻次最多的方劑為麻杏石甘湯,沙參麥冬湯次之;重型患者使用頻次最多的方劑為麻杏石甘湯,其次為三仁湯。從辨證看,邪犯肺胃證使用頻次最多的方劑為麻杏石甘湯,其次為銀翹散;濕毒郁肺證使用頻次最多的方劑為麻杏石甘湯,三仁湯次之;氣陰兩虛證使用頻次最多的方劑沙參麥冬湯,肺脾氣虛證使用頻次最多的方劑為六君子湯。詳見表5。

表5 重慶市萬州區80 例不同病情程度COVID-19 患者方劑使用情況
2.6 臨床療效
80 例COVID-19 患者痊愈34 例,有效42 例,無效3 例,死亡1 例,總有效率95%(76/80)。
3 討論
3.1 實驗室指標分析
白蛋白由肝臟合成,是一種分子量為66~69 kDa的中小分子,是血漿中最豐富的蛋白,在許多生理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白蛋白可調節內皮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的相互作用,減輕肺損傷,是重癥肺炎預后的保護因素,其水平與多種危重癥疾病、急性感染性疾病的病情發展和預后相關[6]。研究表明,白蛋白可預測肺炎的預后及疾病嚴重程度[7]。白蛋白是一種負急性時相反應蛋白,血清白蛋白的降低程度與炎癥反應的觸發程度關系密切[8]。本研究顯示,重型患者白蛋白水平明顯降低。我們推測,血清白蛋白水平可能與患者肺部炎癥滲出程度相關,在重癥患者中可參考血清白蛋白水平,判斷疾病預后及病情嚴重程度。目前針對COVID-19 患者白蛋白的研究較少,其與COVID-19 患者預后、病情嚴重的相關性還有待研究。
T 淋巴細胞在胸腺中發育成熟,能有效發揮免疫調節作用,介導細胞免疫,其不僅為免疫反應的效應細胞,也是免疫調節細胞。其中T 淋巴細胞亞群在機體免疫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CD4+、CD8+是T 淋巴細胞免疫核心,CD4+/CD8+反映機體的免疫狀態,在免疫狀態受抑制后,CD4+/CD8+水平明顯下降[9]。細胞免疫功能低下直接導致患者易患肺炎,目前認為過度炎癥反應和全身免疫抑制在重癥肺炎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研究表明,COVID-19 患者尤其是重癥患者CD4+、CD8+計數顯著降低,在治療COVID-19 患者過程中,提高患者CD4+、CD8+計數可能有利于疾病康復,減少輕型患者轉為重型。
3.2 中醫證候及處方分析
本研究顯示,80 例COVID-19 患者平均年齡(54.20±12.76)歲,男性多于女性,大部分患者有武漢/湖北旅居史或有確診患者密切接觸史。但本研究樣本量較小,對于COVID-19 患者不同性別間的證型分布、不同證型的實驗室指標差異性分析及療效評價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患者多有咳嗽、發熱、納差、腹瀉等癥狀,《溫病條辨》曰:“凡病溫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陰……故首郁遏太陰經中之陰氣,而為咳嗽、自汗,口渴、頭痛、身熱、尺熱等。”從本病病機而言,發病初期系外感濕邪疫毒所致,從口鼻而入,以侵犯肺系為主,導致肺氣不利,宣降失司,脾胃升降失調,病位在肺,與脾、胃有關。《諸病源候論·溫病令人不相染易候》“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指出疫毒是主要致病原因。重慶氣候陰冷潮濕,寒濕之氣是疫毒賴以生存的環境。本研究表明,濕毒郁肺證為本病最主要證型,15 例重型患者中12 例為濕毒郁肺證,故以宣肺化濕、解毒祛邪為總體治療原則。從中藥處方來看,初期以麻杏石甘湯、銀翹散、荊防敗毒散為最多,麻杏石甘湯宣肺透邪,銀翹散清熱解毒,荊防敗毒散祛濕解表;中期以麻杏石甘湯、三仁湯處方最多,麻杏甘石湯為太陽陽明合病之方,三仁湯宣暢三焦,清熱利濕。治療過程中要注重先安未受邪之地,防止疾病進展至后期,毒邪傳變入里,變為危候。本病患者中氣陰兩虛證亦常見,究其原因,本病發病和發展過程中以發熱為主要特征,具有溫熱病性質,同時在發病過程中有熱邪燔灼呈陽熱之象及熱性升散易于耗氣傷津,恢復期患者多見氣陰兩虛證或肺脾氣虛證,多兼余毒未盡,故多選用竹葉石膏湯、沙參麥冬湯以清解余熱、益氣養陰。《靈樞·百病始生》有“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發病后正氣尚盛,轉歸較好,反之則差。因COVID-19 患者常伴腹瀉,故不宜使用大劑量苦寒藥物,以免涼遏冰伏,治療應在清熱解毒同時酌情補益肺脾,以扶正祛邪兼施,協助機體康復。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中醫藥治療應扶正祛邪結合,在祛邪同時注重顧護正氣。
大量基礎研究表明,中醫藥可調節機體的免疫功能,多機制、多靶點及多環節綜合治療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從而達到防治病毒性感染的目的[10]。從疾病預防而言,因重慶地區氣候潮濕,可以健脾祛濕為用藥指導原則,體現中醫治未病思想;從疾病治療而言,為避免輕型發展至重型,對COVID-19 患者應加強早期中醫藥干預,加強輕型患者的中藥應用,阻斷疫病傳變;從辨證論治而言,對COVID-19 進行中醫證候總結,將中醫藥治療融入COVID-19 的全程,從預防、治療到后期康復,突出中醫藥治療優勢,中西醫結合,以期為本病的防治提供臨床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