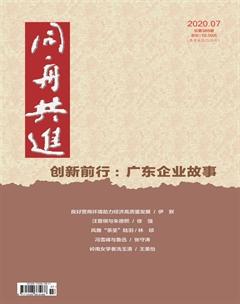迷失“滿洲”
王龍

滿頭白發(fā)的牛島春子又一次從夢中驚醒。盡管已封筆多年,可那個創(chuàng)作于60多年前的中國男人祝廉天,還是無數(shù)次闖入她的夢境。直到人生晚年,她作品中塑造的這個男人還無數(shù)次在夢中對她窮追不舍。幾十年了,他們同樣戴著血淋淋的精神鐐銬,同樣扛著無比沉重的十字架,匍匐在被戰(zhàn)爭改變的命運之路上。這是上天的安排,一位作家竟然和她筆下的主人公同途異運,又同病相憐。
堅定的革命者
牛島春子的文學道路之初充滿純正的革命色彩。早在30歲那年,她就成為日本社會反叛的異端。
20世紀30年代席卷世界的經(jīng)濟危機,也嚴重威脅著日本。生產(chǎn)停滯、工廠倒閉、失業(yè)驟增,社會危機日益加劇。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產(chǎn)黨帶領(lǐng)工人、農(nóng)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運動和抗爭。眼見無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如同干柴烈火,天皇制政府從1930年開始瘋狂地逮捕迫害左翼人士,日本共產(chǎn)黨處于生死存亡的關(guān)鍵時刻。
那時的牛島春子是一位十足的理想主義者,她在白色嚴冬時期毅然選擇了一條危險的革命之路。廠方很快發(fā)現(xiàn)了她的左翼傾向,她因為參加工人運動而被解雇。但這不僅沒有嚇倒牛島春子,反而更加激起了她的革命熱情。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日本國內(nèi)狀況急劇變化。法西斯勢力急遽膨脹,緊張的空氣令人窒息。為了強化專制統(tǒng)治,日本當局加緊對內(nèi)進行血腥鎮(zhèn)壓,大批無產(chǎn)階級運動的活躍分子被逮捕入獄。1932年2月,在新一輪抓捕左翼進步人士的高潮中,牛島春子也被投進了監(jiān)獄。監(jiān)禁了兩個多月后,她被釋放出獄。牛島春子身患肋膜炎,在病痛和精神的雙重高壓下,她不但沒有放棄信仰,還積極為九州地區(qū)的日本共產(chǎn)黨做些力所能及的宣傳工作。這年底,面對山雨欲來的政治烏云,牛島春子逆風而行,決然加入了日本共產(chǎn)黨,并成為無產(chǎn)階級作家同盟的成員。
當時日本文壇的法西斯逆流已經(jīng)十分猖獗,革命隊伍嚴重分化,有些動搖彷徨的文人已主動向軍部暗送秋波,攀親結(jié)緣。牛島春子偏要在這充滿白色恐怖的艱險時刻,選擇跟風雨飄搖的共產(chǎn)黨陣營站到一起,確實需要一份非凡的勇氣。
1933年,日本當局的殘酷鎮(zhèn)壓達到了頂峰。3月10日,在抓捕共產(chǎn)黨人的狂潮中,牛島春子再度被捕。在暗無天日的監(jiān)獄里,她不斷聽到許多同志被殘忍虐待直到被殺,仍然不肯屈服投降。牛島春子決心抗爭到底,絕不投降。
沒想到,這些義無反顧為真理獻身的殉道士,卻變成了擺在革命祭壇上的犧牲品。正當他們不屈不撓地抗爭時,日本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佐野學、鍋山貞親于6月9日在監(jiān)獄中發(fā)表了著名的“轉(zhuǎn)向聲明”。這無異于釜底抽薪,徹底擊垮了絕大多數(shù)日本共產(chǎn)黨人的精神防線。日本共產(chǎn)黨短期內(nèi)出現(xiàn)了大批的思想“轉(zhuǎn)向者”,表示從此擁護天皇制度,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zhàn)爭。日本共產(chǎn)黨員開始排著隊在“轉(zhuǎn)向書”上簽字投降。在長長的隊伍中,就有拖著鐐銬的牛島春子。
偽滿洲國的“新生活”
雖然后來在個人專訪中,牛島春子堅稱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轉(zhuǎn)向者,只不過寫了“理由書”而已,但她在軍國主義甚囂塵上的狂潮中選擇了隨波逐流,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1933年11月16日,牛島春子被保釋。1935年,長崎檢察院判處牛島春子兩年徒刑,緩期五年執(zhí)行。這一年,日本的共產(chǎn)主義者停止了組織活動,左翼作家們紛紛向政府當局投懷送抱,變成了一群為侵略擴張大唱贊歌的乖巧鸚鵡。
經(jīng)歷了這場恍然如夢的精神浩劫,牛島春子走出監(jiān)獄時,已陷入麻木迷茫的狀態(tài)。信仰迷失后的真空,使她頭腦中一片空疏,郁悶的心中積滿了“低迷與虛無的恐懼”。
萬幸的是,那段孤獨晦暗的痛苦歲月中,還有一個善解人意的男人,成為牛島春子唯一可以依賴的精神支柱。此人便是她后來的夫君牛島晴男。
1935年秋天,牛島晴男被任命為“滿洲國”奉天省屬官,婚后的牛島春子也跟隨丈夫來到了“滿洲”,開始了另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
作為日本政府極力標榜的“五族協(xié)和,王道樂土”,當時的“滿洲國”已云集了近百萬日本人。竭力主張向滿蒙開拓移民的軍國主義者,向日本國民天花亂墜地鼓吹中國東北是一片“流淌著奶和蜜”的神奇沃土,是大和民族新的希望之所。一時間,不但瘋狂逐利的資本家們紛紛朝“滿洲”飛奔而去,連窮苦的日本底層老百姓,也爭先恐后移民去當“滿洲”的新主人,甚至連大批還沒有長槍高的青少年,也被鼓動成為“滿蒙開拓義勇軍”的主流。
對于那些在政治上備受打壓的左翼人士來說,逃到“滿洲國”不啻為一條重新生活的美好之路。在這種情況下,在日本已經(jīng)沒有安身之地的牛島春子,要擺脫軍國當局的監(jiān)視控制,“滿洲”自然也成為她首選的棲身之地。
投奔“滿洲”后的牛島春子,上演了一出灰姑娘搖身變成“文壇公主”的神話。她徹底拋棄了自己曾經(jīng)為之奮斗的政治信仰,一改從前反對日本侵略擴張的政治立場,轉(zhuǎn)而以高亢熱情,竭力描繪一個“新滿洲”形象,狂熱迎合日本殖民者“滿洲建國”“五族協(xié)和”的國策。她一躍成為“滿洲國”著名女作家,這一過程充滿了暴發(fā)戶般的傳奇。
牛島春子非常慶幸自己“生正逢時”。當時要在日本國內(nèi)成為知名作家,可謂難上加難,而在偽滿洲國成名機會卻變得唾手可得。在東北14年的殖民歷史中,日本政府格外重視“滿洲文學”的發(fā)展,日本人的作品發(fā)表十分容易,有些才華平平的人很快成了“知名作家”。當時所謂的“開拓文學”,很多就出自“開拓團”中的普通日本農(nóng)民之手。在這支浩浩蕩蕩的“滿洲文學”隊伍中,牛島春子無疑是受到格外垂青的幸運者之一。日本文學界享有盛名的權(quán)威獎——芥川龍之介獎也增加了“滿洲文學”的比例。牛島春子影響最大的作品,便是獲第12回芥川獎“候補”提名的《祝廉天》。
“異人種”的命運
1937年10月,牛島晴男調(diào)至龍江省拜泉縣出任副縣長,牛島春子隨夫移居拜泉,在這里生活了一年。雖然時間短暫,但這一年決定了她前半生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向。在官方支配下,牛島春子拾起在拜泉搜集到的素材,創(chuàng)作完成了最重要的代表作、中篇小說《祝廉天》。
祝廉天的原型祝廉夫,是拜泉縣公署的一位真實人物,當時任牛島晴男的翻譯。祝廉天》中的副縣長風間真吉,就以牛島晴男為原型。他和翻譯官祝廉夫之間的交往和故事,被如實地寫進這部作品中,具有極強的歷史可信度。
身處“滿洲國”的日本人雖然是統(tǒng)治者,但作為初來乍到的異鄉(xiāng)人,無法克服異族文化帶來的隔膜與鴻溝。他們必須借重“以滿治滿”的策略,通過一幫精通日語、行事干練的中國雇員實施統(tǒng)治。“滿洲國”成立后,當時偽滿各縣的縣長名義上都是中國人,但實際大權(quán)牢牢掌控在出任副縣長的日本官員手中。“再壞的地主也得有幾個好長工”,副縣長牛島晴男也物色了這么一位得力助手,那就是祝廉夫這位能人。
祝廉天的原型,就這樣進入了牛島春子的視線,她對這個性格奇異的人物進行了長期觀察,因此創(chuàng)作起來如同撰寫回憶錄一般得心應手。
盡管日本當局一味粉飾“五族協(xié)和”,但“滿洲”社會的民族矛盾異常尖銳。中國雇員在日本人面前人人自危。正像牛島春子作品中描述的那樣,滿系公務員與日本人的關(guān)系非常微妙。一方面,中國雇員吃著日本人的飯,就必須察言觀色遵循日本人的規(guī)則;另一方面,做著違背民族良知的事情,他們只求茍活于世上,“以巧妙的社交技術(shù)避開,來應酬日本人”。但祝廉天卻完全我行我素,孤傲無比。他精明強干,勇于進取,辦事總是雷厲風行,出言總是咄咄逼人。他在日本人面前也不讓三分:“譏嘲日系,憎惡滿系的怠惰,發(fā)霉似的痛罵那些橫行惡法的樣子。”
祝廉天的日常生活全然日本化,平時穿著白色的日本和服,腰上纏著大帶子,腳下拖拉著粗陋的木屐,以致于當他從自己那四周養(yǎng)滿雞、鴨、豬的中式家中走出來時,一派混搭的景象令人啼笑皆非。
在當?shù)匕傩蘸腿毡竟倭胖g,祝廉天應付裕如的高明本事也讓所有人刮目相看。小說中有一個精彩情節(jié):真吉所在縣里下達了必須購買三百來匹軍馬的繁重任務,但“村民們對于軍馬購買一事,不太高興”。因為馬匹是東北農(nóng)民必備的農(nóng)用工具,以往日軍前來購馬價格偏低,強買現(xiàn)象常常出現(xiàn),實質(zhì)是近于掠奪。
祝廉天對村民們的抵觸情緒十分清楚。當日軍下士官暴怒地虐待抽打馬匹,馬主們非常恐懼,“顯出張慌失措的樣子”。祝廉天走到下士官面前,制止了他的行為,村民們十分感激。該談價格了,這是件棘手的事情。真吉談了三次仍交涉不下來。這時祝廉天走到村長們面前只說了幾句話,一個村長就主動走到真吉面前說:副縣長為我們著想的這種心意,都很明白我們對于軍方所定的價格有苦難言,但對于這件事請不必再掛慮了。”
價格一定,馬主們也十分滿意,“不僅如此,而且在他們很認為是在預想之外”。
購買軍馬一事就這樣圓滿地完成了。真吉對祝廉天的本事更是刮目相看。祝廉天成為日本人的一名優(yōu)秀“師爺”。
牛島春子塑造的祝廉天這一形象,如同一面鏡子,反映了當時偽滿社會的真實狀況。祝廉天是一個被日本殖民者徹底“皇民化”的變異者。難道說,牛島春子真的相信祝廉天這樣的“第三類人”,能夠融入丈夫牛島晴男那樣的日本人圈子?他們真的能夠在“滿洲國”創(chuàng)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其實牛島春子早已從自己編織的“滿洲神話”里,嗅到了不祥的氣息。對于祝廉天這個人物的悲劇命運,她早有強烈的預感。正如戰(zhàn)后橋川文三評說《祝廉天》其實表現(xiàn)了“滿洲緊張的民族問題”。評論家小島政二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說法:“祝這個男人我仿佛親眼所見,能認識到他這種‘異人種的存在是難得的收獲。”
“異人種”——這個特殊的詞語十分準確地表達了祝廉天的身份與處境。祝廉天不是一個普通的漢奸形象,而是日本殖民者一手熏陶培養(yǎng)出來的政治畸形兒,更是一個從外部到靈魂都徹底異化了的“異人種”。盡管他對“滿洲建國”的理想那么忠心耿耿,但這種一廂情愿的自作多情,注定不會得到日本主子內(nèi)心的認同。
在偽滿洲的日本開拓團中,只有日本人有資格吃大米,中國農(nóng)民只配吃粗糧,甚至連日本小孩都可以居高臨下地指揮命令中國人。日本人宣揚的所謂“五族協(xié)和”的虛偽和欺騙,一覽無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無論牛島春子如何粉飾太平,渲染“日滿親善”,營造“滿洲國”和諧氛圍,最終也無法回避民族壓迫下的尖銳矛盾。牛島春子連自己都無法欺騙,所以她無法給祝廉天安排一個自圓其說的結(jié)局。
一言難盡的“滿洲情結(jié)”
祝廉天和風間真吉這個“民族協(xié)和”的神話終于破滅了。在牛島春子的《祝廉天》完成三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就被中國人民趕出了國門。
牛島春子對戴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鎖無能為力。身處戰(zhàn)爭中的“滿洲”,她無時不在百般糾葛中努力掙扎,急于逞強般證明自己的“能力”。為此,牛島春子承認“我最后還是隨波逐流了”。她是軍國主義政權(quán)下的受害者,而對殖民地人民來說,又是為虎作倀的加害者。
歸根結(jié)蒂,她也是不折不扣的精神“異人種”。不同的是,她和丈夫牛島晴男屬于統(tǒng)治陣營的“異人種”,而祝廉天則是被統(tǒng)治陣營的“異人種”。
由于戰(zhàn)局不斷惡化,1944年3月,牛島晴男被征召進入“滿洲駐屯部隊”,開赴沖繩附近的宮古島參戰(zhàn)。前線日軍慘敗的消息雪片般飛來,牛島春子心灰意冷,逐漸失去創(chuàng)作的動力。從1943年開始,就很難再見到牛島春子的作品了。
1945年8月11日,由于得知了蘇聯(lián)對日宣戰(zhàn),牛島春子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乘車經(jīng)由朝鮮歸國。途中在沈陽換車時,牛島春子聽到了日本戰(zhàn)敗投降的消息。她頓時悲欣交集,莫可名狀,先是放聲大哭,繼而又笑了起來。從戰(zhàn)爭重壓下解脫出來,她陶醉于“強烈的喜悅”。牛島春子回憶說,那時大多數(shù)日本人在聽到戰(zhàn)敗消息之后,都會感慨道:“啊,終于自由了!”
1946年秋季,幾經(jīng)周折后,牛島春子回到日本福岡的丈夫老家。上帝再次眷顧了她,讓她等到了1947年丈夫從戰(zhàn)爭中生還回國。
此后牛島春子繼續(xù)從事創(chuàng)作。有意思的是,夢里走了很多路,醒來還是在床上,1948年她再次加入了左翼團體——新日本文學會久留米支部。
1980年8月,一支“日中文化交流使節(jié)團”到訪中國東北地區(qū),滿頭白發(fā)的牛島春子也加入了這支隊伍。舊地重游,無人能夠理解她的心情多么復雜。祝廉天的悲慘下場,重新浮現(xiàn)在她眼前——
1944年隨著戰(zhàn)局吃緊,日本動員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線。拜泉縣公署也成立了動員課,直接受命于關(guān)東軍,能力突出的祝廉天被任命為股長。眼看日本軍隊漸漸不支,祝廉天也許覺得自己的命運與日本帝國息息相關(guān),于是工作更加拼命賣力。他對征兵不合格者進行嚴懲,成立了集中營般可怕的勤勞奉公隊,很多當?shù)匕傩帐鼙M折磨,丟掉了性命。戰(zhàn)爭結(jié)束時,老百姓恨透了祝廉天,他被處決于拜泉縣西門大街的十字路口。
牛島春子回憶,直到1994年,當年生活在拜泉縣的日本人組成“拜泉會”故地重游,盡管接待方出于禮貌對他們熱情有加,但60歲以上的當?shù)乩夏耆藷o不對他們怒目而視。
二戰(zhàn)結(jié)束后某年,有個中國文化使節(jié)團來到日本訪問,座談會上,牛島春子和一位中國婦女同桌。她的全家人都被日軍殺死,牛島春子回憶說“她少言寡語,不斷露出謹慎的微笑,這深深打動了我”。
從那一瞬間,她開始了對侵略戰(zhàn)爭的反省。1969年,牛島春子發(fā)表了隨筆《某種微笑——為日中不再戰(zhàn)所想》。她坦言道:
準確地說,我開始自問對于自己來說,“滿洲”是怎樣一個地方,那是在被遣返到日本之后的事情。的確“滿洲國”是日本為了侵略大陸而虛構(gòu)的國家。并且毫無疑問,我是稀里糊涂坐上賊船的愚蠢的國民之一。
遲到的懺悔也彌足珍貴。她說:“很羞愧,我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才意識到,自己的狂妄和自私,也意識到一個民族對另外一個民族的統(tǒng)治是沒有什么正當理由的。”
這一年,在福岡縣太宰府市的觀音寺內(nèi),日本反戰(zhàn)人士為發(fā)誓“日中不再戰(zhàn)”而建立了紀念碑,牛島春子便是發(fā)起人之一。1993年,牛島春子發(fā)表了她的封山之作《我的故地“拜泉”》和《遙遠的拜泉》。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