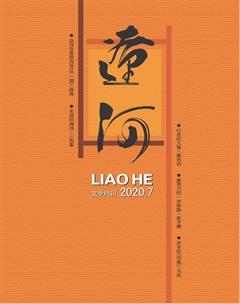風車
王哲

正是楊柳飛花的季節,天氣好像忽然熱了起來。我們村是個大村子,主街很長,從東邊到西邊要走二十分鐘。我背著書包用手不斷地劃拉著落在頭頂上的楊花柳絮,從東邊向西邊走去。忽然一陣搖轆轤的聲音,吱吱嘎嘎吱吱嘎嘎,在午后寂靜的村子里顯得格外響亮。我趕緊向井沿兒走過去。
搖轆轤的是個女子,身上穿著一件藍色的碎花襯衫,她見我來到跟前微微一笑走下井臺。
她挑水的樣子太好看了,一副纖纖秀秀的身子隨著竹扁擔上下顫悠左右來回擺動,讓你不自禁地會想起扭秧歌人踩著鑼鼓點兒那明快的節奏。很多年以后,每當我想起這一幕的時候,我都能感受到她在生活重壓下,那副身軀所蘊含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由此爆發出來的鄉下婦女那種共性的悲壯美。我一直在想,她木桶里裝的也許根本不是水,而是對未來歲月和命運的深切希望……
當時,我忘記喝水了,一直跟在她的后面,聽竹扁擔壓在肩頭發出好聽的聲音,看她微微佝僂的背影緩緩向前移動。
看她那力不可支的樣子,我以為她隨時都會把擔子撂下,可是我錯了。我一直看著她挑水進了院子,才發現我已經到家了。
她住在我家東院。二叔搬走以后,父親把東院留下了,他本來是打算等我長大了娶媳婦用,現在正好閑著便借給她住了。
我從母親的嘴里得知,她叫雙鳳,一個有點俗可又很好聽的名字。后來我還漸漸知道她是從關里和一個男人跑過來的,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私奔。這讓我覺得好奇,也更想關注她。
雙鳳平時很少出屋,大門也總是關著,他的男人來這兒沒幾天便到煤礦打工去了。家里剩下她一個人。
我沒事兒的時候故意在東院門前溜達,希望再次看到她挑水的樣子,可這樣的機會畢竟太少了。有兩次看她隔著墻頭兒和母親說話,等我走到跟前她又回屋了。
母親看著我嘆一口氣說,真是一個可憐的孩子!
那天晚上放學,我剛到村口便看見雙鳳了,她正探著脖子向遠方瞭望,看我過來就笑著和我打招呼。
我說,這陣子怎么沒看你挑水啊?
她說,我一個人也用不了那么多水啊!
我知道她肯定是想她男人了,她男人走后一直沒有回來,只給她寄過一次東西。
入冬以后,雙鳳忽然在一天夜里來到我家,和我母親說,半夜的時候有人敲她窗戶。母親沉吟半晌說,那你就把門栓緊了,沒事兒。
雙鳳有些害羞地看著母親,然后又把目光投向我。我趕緊低下頭假裝在寫作業。
母親早就看出她的意思了,她是想讓我去跟她作伴,可是又不好意思開口。她一直在我家待了很長時間。
母親只好說,長峰已經十六歲了,這不合適。
雙鳳趕緊說,嬸子,你還不相信我嗎?
母親再次嘆一口氣,算是同意了。
其實雙鳳剛滿二十歲,但她還真像個姐姐。在我跟她作伴的日子里,她什么也不讓我干,對我也很關心。雖說我想跟她一起去挑水,可她說什么也不同意。
后來我說,雙鳳姐,其實我就是想看你挑水的樣子,真好看!
她聽完這句話就咯咯地笑了。
雙鳳姐最后終于拗不過我,才答應晚上和我一起去挑水,我知道她是想避開母親,怕母親不樂意。
雙鳳姐把水剛裝滿,我便把扁擔拿在手里,我說是看她挑水,其實我是想幫她干點兒活兒。不知為什么我只想幫她一把。
雙鳳姐一個勁兒在后邊叫我放下,但我還是一口氣把水擔進屋子,倒進缸里。
雙鳳姐說,長峰你這要讓嬸子看見,不是害我嗎?
每到晚上我們倆臨睡前都說一會兒話,當說到她男人的時候,雙鳳姐便一臉幸福的期待。
一鋪炕中間放一張長條桌子,我在炕頭兒她在炕梢兒,我的鞋墊兒她總是頭天夜里放在褥子底下,第二天再給我放到鞋里。
這年的冬天很冷,我的腳被凍了,她立即掀起衣服的前襟兒,把我的雙腳抱在她懷里。此時,我覺得她就是我的姐姐——我從未見過面的親姐姐。我很感動,只想流淚……
那天晚上我們睡得很晚,半夜解手的時候,我忽然發現雙鳳姐不見了。
我家隔街對面的院子里有一個風車,在夜風的吹拂下,風車在高高的木桿子上轉動,發出了嘩楞楞嘩楞楞的金屬碰擊的聲音,很好聽。我走到雙鳳姐身后的時候,她正看著風車發呆。
我說,雙鳳姐,天冷呢,回吧!
雙鳳姐說,你聽,多像車輪在冰面上滾動!
后來我費了很大的勁兒特意給雙鳳姐做了一個風車,為此我還偷了父親自行車上的滾珠兒。當我把風車用鐵絲綁在木桿子上立在院兒里,雙鳳姐滿臉都是開心的笑容。
我們一起站在木桿下看風車轉動,想歲月的流失,很多時候雙鳳姐看著看著會流出眼淚。當我看向她的時候,她又趕緊把淚擦干了。
我說,雙鳳姐你怎么又哭了?
雙鳳姐說,人家還不是高興的!
一掛晝夜不停轉動的風車讓雙鳳姐寄托了太多的思念和期盼,這是我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
有很多夜晚,雙鳳姐都一動不動地站在風車下。她對我說,來年開春我就跟你姐夫回關里。
我忽然很沖動,想一把摟住雙鳳姐,讓她永遠留在這里……
春天說來就來了,可姐夫打工的煤礦塌頂了,姐夫被永遠地埋在了里面。聽到這個消息雙鳳姐一聲也沒哭,只是望著院子里轉動的風車呆呆出神……
后來雙鳳姐一個人回了關里,我又和父母住在一起,風車依然在轉動,只是聲音越來越小也不那么好聽了。
那天夜里我忽然第一次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