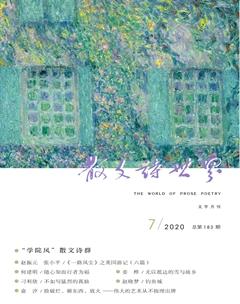觀鳥小札(二篇)
祿永峰
跳躍的蒼鷺
春天里,我喜歡跳躍的事物。
一陣輕風過后,滿樹的杏花、桃花、杜梨花跳躍起來,沒有一點兒聲音。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怒放了,成群結隊的蜜蜂在一朵朵油菜花上跳躍著,它們纖細的腿上一定沾滿了蜜。一群蒼鷺掠水而過,落在村口的一棵大楊樹上,它們在樹梢上愉快地跳躍著,或修補舊巢,或孵育生命。
樹梢上的蒼鷺跳躍起來,我也跟著它們跳躍的節奏,繞著樹一圈一圈地跳躍著。
一樹的蒼鷺,像是在春天里遇到了什么特別喜慶的事情,一會兒飛走了,一會兒又飛回來了。蒼鷺的每一次飛翔,像是我在村莊的每一次奔跑。它們的雙翼鼓動緩慢,脖頸前傾,縮成“Z”字形,兩腳向后伸直,恰似對村莊的一次次擁抱。我相信,一棵棵楊樹露出嫩綠的枝丫,一定是一只只蒼鷺喚醒的。甚至連同整個村莊,也是飛來飛去的蒼鷺喚醒的。
春天的天空很干凈,穿過村莊的小溪很清澈。附近的山頭、坡地,由遠及近地披上了淡淡的綠衣裳。大地綠了,一塊一塊的白云便跳躍起來,我常常佇立在楊樹下,凝視豁然洞開的那一大片藍天。藍天下是一對對蒼鷺修葺一新,開始準備孵育幼雛的一只只鳥巢。樹梢上有幾對蒼鷺相依在一起,沐浴著陽光,像一朵朵綻開的花兒,滿樹盈香。一只只蒼鷺,讓春天提前來到了村莊。
春天的陽光照耀在大地上,楊樹是透明的,一只只鳥巢是透明的,連同整個春天也都是透明的。待蒼鷺的幼雛破殼而出的時候,楊樹的葉子也快要綻開了。樹綠起來了,綠得自然,綠得濃郁。一片片楊樹葉子,像一把把心形的小扇子掛滿樹枝。整個村莊,沒有哪一棵樹上的葉子像楊樹那么稠密。一天里,一整棵楊樹的綠蔭更多的時候在向樹身收攏、向樹梢上的一只只鳥巢收攏。在一棵大楊樹上,蒼鷺修筑的那些巢里,不斷有幼雛破殼而出,一個個幼雛在巢里成長的速度,比楊樹上冒出的葉子還要快。
午后的氣溫驟升,幾只蒼鷺站在巢沿上,打開翅膀,為巢里嗷嗷待哺的幼雛們遮擋烈日。呵護子女,蒼鷺像人類一樣,精心陪伴幼雛成長。站在巢沿上,雌蒼鷺始終保持同一個姿勢,長時間站立不動,翅膀之下呵護著一只只幼雛。蒼鷺的母愛,在樹上,樹一定能夠感覺得到。
用不了幾日,長大了一點兒的小蒼鷺,便開始在雌蒼鷺或者雄蒼鷺的陪同下,在樹梢上練習跳躍。村莊里所有蒼鷺的飛翔,都是從樹梢上的跳躍開始的。小蒼鷺開始跳躍,戰戰兢兢,像是怕自己落不到巢里,或者落不到樹枝上似的。慢慢起跳,慢慢回落。它們一次次跳起來,又落到樹梢上,就像我跳起來落在大地上。
這依土而生的黃土高原呵,最適合跳躍了。周圍嘰嘰喳喳飛來飛去的鳥兒,一跳躍起來便再也停不下來。我最喜歡跳躍著追逐一群鳥兒。鳥兒想飛到哪兒是哪兒。鳥兒的世界像黃土高原那么遼闊,空曠。
我喜歡仰望小蒼鷺跳躍起來的樣子,它們先是在巢里慢慢地跳動,再是從巢里跳動到巢邊的樹枝上,跳著跳著,再從一枝樹枝跳動到另一枝樹枝上。小蒼鷺一旦跳起來,就會像我一樣再也停不下來。它們在整棵楊樹上跳躍著。滿樹有幾十只巢,都是蒼鷺筑就的,整個楊樹的樹梢便成了它們樹上的村莊。
蒼鷺的巢,只能遠觀,不能靠近。我不止一次掏過麻雀的巢。麻雀筑的巢多是修筑在低矮的屋檐下,或者老鼠遺棄的洞口。不像蒼鷺,它們的巢都筑在高大的楊樹梢上。曾經看到一只盤旋的鷹從高空劃來,準備攻擊正在孵化的蒼鷺,樹上的幾十只蒼鷺迅即站起來,鳴叫著,一同凝視著那只鷹,像是做好了反擊準備。鷹繞大楊樹盤旋一周,飛走了。目送那只遠去的鷹消失在天際,我卻從沒有順著楊樹的枝干靠近蒼鷺的巢,盡管早已經學會了爬樹。
在村莊,楊樹發木快,木質軟,并不算什么好樹種。楊樹的高度,都是村莊人去除偏枝后一節一節冒高的。爬樹的人爬到楊樹上,頂多把身體架在靠近樹身的樹杈上,再不敢沿分開的枝杈朝上爬,若繼續爬,樹枝易折。而蒼鷺的巢,恰恰修筑在樹梢的頂部和中部。別說大人,就是小孩也無法靠近。
蒼鷺是村莊里最大的鳥。它的頭、頸、腳和嘴都比較長,身體看起來比一只高空翱翔的鷹還要大出許多。洋槐樹、梨樹、杏樹、椿樹、杜梨樹,都是村莊木質較硬的樹種。蒼鷺卻對楊樹情有獨鐘。它們只選擇在大楊樹上筑巢,而且還是群體性的。我曾驚喜地發現一棵大楊樹上竟然有五十多只巢。幾十只蒼鷺把那么大一冠樹當成一朵花來纏繞,不知蒼鷺是喜歡楊樹的氣息,還是看好楊樹木質軟人不易靠近的特點。楊樹的木質那么軟,那些巢在風風雨雨中依舊安然無恙。或許,村莊的楊樹就是為蒼鷺而生的。
蒼鷺是一種大型水鳥,以水里的魚蝦、泥鰍、蜥蜴、昆蟲、蜻蜓等為食,它們的食物多在水邊淺水處或沼澤地上,或在人造水壩和水塘中。而水草并不多見的黃土高原上,蒼鷺覓食確實不易。
我想,蒼鷺之所以每年春天早早都要從南方飛回北方,恐怕更多的原因是奔著村莊里的一棵棵大楊樹而來的。村莊人也甚是喜愛蒼鷺,建造房屋,打造家具,在砍伐樹木的過程中,大多人家都會把大楊樹留下來。蒼鷺把巢修筑在村莊附近的大楊樹上,遠離村莊的那些楊樹上,卻沒有一只蒼鷺修筑的巢。蒼鷺樂于與人為鄰,應該是村莊人與鳥為善的緣故。
遺憾的是,蒼鷺把巢修筑在大楊樹上,七八年過后,楊樹就會葉敗枝殘。架著幾十只鳥巢的大楊樹枯衰,像一個暮年的老人。蒼鷺不在死樹上繁衍生息,它們集體搬家,選擇在另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楊樹上筑巢。村莊人說,蒼鷺一旦在楊樹上修筑了巢,就會縮短楊樹的“壽命”。按說,一棵楊樹幾十年壽命是有的。每隔七八年,修筑了蒼鷺巢的楊樹死去。后來人們說是蒼鷺的糞便腐蝕性較大,大楊樹是緣于腐蝕而死。不知道村莊人的說辭是否有科學依據。
即便如此,村莊里的每一戶人家,仍希望自己家栽植的楊樹上能夠早日筑上蒼鷺巢。蒼鷺就像村莊里的吉祥鳥一樣,與村莊人和睦相處。蒼鷺來到村莊,就該有蒼鷺的家。蒼鷺的家在楊樹上,樹成了蒼鷺在樹上的村莊。
我喜歡看蒼鷺筑巢、孵育、跳躍、飛翔的過程。它們在樹上一代代孵育、成長,就像田里一茬茬莊稼種植和收獲。這些跳躍的事物,都算是大地上的豐收。
在村莊,我也要給蒼鷺栽植幾棵楊樹,讓一只只蒼鷺在樹梢上跳躍,然后飛翔……
膽小的鷸
第一次在北方幾位攝影師的組照里見過這類水鳥。再美麗的水鳥,似乎也很少有村莊人關注。攝影師說,這鳥兒就出現在我們黃土高原的村莊,叫黑翅長腳鷸。
乍一看,它們修長的身材,全憑那雙紅色的細長腿支撐著。成鳥,大概40多厘米的身高,單那雙細長的紅腿就超過30厘米。在鳥界,它們的腿長與身高極其不成比例,簡直像是民間社火表演中那一排踩高蹺的人。踩了高蹺的人,游走在展演的隊伍中,引人注目的絕對是那一對對高蹺,而非表演者。但是,奇怪的是,這長腿長在了鳥的身上,卻讓人覺得不怎么別扭不說,還平添了另一番趣味。我估摸,黑翅長腳鷸要是在水邊一站,無論誰,先看到的,一準是它那雙細長腿。
關于鷸,《戰國策·燕策》記載有“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寓言故事。本義是,鷸被蚌夾住了嘴巴,雙方爭斗,僵持不下,漁人將鷸和蚌都捉了回去。此番情景,不知漁鄉捕魚者是否偶遇過。但可以肯定,鷸與蚌的生存離不開水。在黃土高原的村莊,我曾經見過蚌出現在淺水中,卻從未見過鷸。
鷸的故鄉不在黃土高原。
鷸幾乎是突然出現在黃土高原的村莊,它們的魅力正在那雙紅色的長腿,遠遠地觀之,令人驚喜。我想,鳥如人,長在身體上的,沒有多余的。鷸邁著細長腿,腿部關骨節折得像個朝左開口的“V”字形狀。它們整條腿沒有大腿小腿之分,像兩根干枯的樹枝支撐在大地上。整條腿,一點肉也沒有,給人的感覺,鷸的成長過程中,腿部只是往長長不長肉似的。
風輕云淡的時候,鷸喜歡群體性站在水邊,雙腿筆直,站成一排,個個身體不算太大,卻將一雙雙長腿撐得直直的,姿態絕對優雅,與別的鳥相比,它們算得上鳥界“超模”。即便不邁出一步,也算得上是一個個“長腿娘子”“紅腿娘子”。
我喜歡隱藏在遠處觀看鷸在淺水中覓食的樣子,鷸瞅準魚蝦,翅膀、尖嘴和長腳并用,蹚水行走,很是輕巧,邁出每一步毫不費勁兒。鷸捉魚撲蝦,身手那么敏捷,若不是長腿,說不準身體在水中會失去平衡,遭到水嗆。
鷸的膽量出奇的小。只要人稍微一靠近,它們就會群起飛走。受到驚擾,它們并不是慌不擇路,各奔東西,而是漸次跟隨頭鳥起飛,不僅飛得高,而且飛翔的姿勢整齊劃一,像是先前在哪兒專門訓練過一樣。每一只鷸的脖頸、身體和腿部直成一條向上傾斜的直線,朝前疾速劃去。我朝空中仰望,一只只鷸鼓動起黑色的翅膀、蹬直著紅色的長腿,很是有力。它們身著潔白的羽衣,黑色的翅膀像件黑色披風,鮮紅而修長的雙腿,黑白紅三種顏色,特別分明。
鷸的膽量,比起村莊的麻雀來,真是遜色不少。麻雀雖小,膽量卻大,有時候我與它近在咫尺,它卻并不飛走。若是秋收季節滿院子里堆放了糧食,常常攆也攆不走。有幾年它們還把巢修筑在我們老房子的屋檐下,天天清早嘰嘰喳喳個沒完沒了,像是跟我們傾訴它們一天的心事。對于它們,我也不反感,畢竟,村莊的麻雀并不是愿意到誰家的屋檐下都去筑巢的。
麻雀,一年四季都會把村莊當成它們的村莊。村東頭村西頭,它們都熟悉。哪塊田地里的糧食顆粒豐滿,哪棵大樹綠蔭濃密,它們比村莊人還清楚。一個村莊,那么多的田地、溝壑和參天大樹,夠一只只麻雀飛奔了,它們很少飛到村莊外面去。而鷸呢,春季從南方遷徙到北方的村莊,見人就會匆匆飛去。在整個村莊和大地上,人反倒像成了一個個不速之客,擾亂了它們的生息秩序。我不止一次疑惑不解:來到北方村莊,鷸究竟會是奔什么而來呢?
村莊是有大樹,許多鳥都喜歡把巢修筑在樹上,但鷸卻不會,它們總是把自己的巢修筑在水草邊的雜草叢中。巢也不講究,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個順地平躺著的草窩,一點也不像樹上其它鳥類的巢那般精致。在村莊水草并不豐盛的河邊,鷸總是暴露在草叢里那些粗糙的巢,不知是不是因為村莊的水草太過于薄瘠呢。
記得小時候,村莊的河邊或者溝底的沼澤地里,總會長滿了密密匝匝的蘆葦。蘆葦是那時候長在村子里最壯實的水草。常常有青蛙及別的水鳥出沒。直到深秋蘆葦枯干,人們才將蘆葦采割打捆扛回家,晾干編席(貧窮年代,鋪在炕上,直接睡在上面,很是耐用)。如今,村莊席匠已經遠去,村莊人也不興在炕上鋪席。昔日村莊里一塊塊豐盛的水草——蘆葦也蕩然無存。如今再次走過早年的那塊茂盛的蘆葦地,感覺大地上就像塌陷出了一個巨大的窟窿,空洞洞的。
我在想,膽小的鷸,要是它們在黃土高原的村莊里偶遇一塊塊蘆葦林該多好呵。蘆葦叢里筑巢,一定隱蔽,也一定暖和。事實上,鷸每年在村莊才僅僅停留一月多時間,村莊更像是它們一路北遷的一個驛站。
近些年,村莊修筑了水庫,鷸每年春末夏初在水庫周圍翩翩飛舞,到五月底前全部又繼續北上了。它們在村莊不過多停留,村莊像是它們遷徙中的一個“補給站”。待冬季向南遷徙的時候,它們并不原路返回村莊停留,南遷可能是另外一條路線吧。我不知道,村莊留不住鷸的真正原因,會不會是由于水草不夠豐盛呢?!
從時間上說,膽小的鷸在村莊只算得上是個過客。對于過客,我們就該多些待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