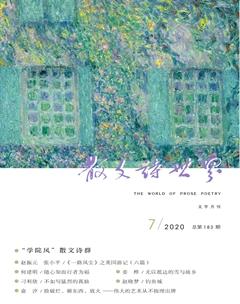一首長詩的三種寫法和一個向度
劉清泉
我一向以為,抒情是中國詩歌顯著而光榮的傳統,在這一點上,新詩與古典詩歌的氣質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可以說抒情是中國詩歌區別于西方詩歌的最重要標志。這倒不是說西方詩歌不注重抒情,而是說從總體性特征和整體性面貌來看,西方詩歌是說出來的,而中國詩歌則是唱出來的。說出來講究有條有理,而唱出來更強調聲情并茂。如是觀之,古往今來,從《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木蘭詩》,到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再到艾青的《火把》《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等等,雖然語言形式上是敘事,但骨子里、質地上仍是抒情,因此應將這些經典詩篇納入抒情詩的范疇來加以品鑒和研究。
也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趙曉夢長達1300行的《釣魚城》是一部抒情長詩、英雄史詩、人文大詩。不能因為《釣魚城》針對的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而將其歸結為敘事詩體,也不能因為《釣魚城》涉及侵略與投降、忠君與愛民等尖銳矛盾而輕易否定其作為英雄史詩的歷史價值,更不能因為詩人趙曉夢的選擇性介入而無視其探索中國長詩寫作新向度的良苦用心和人文情懷。恰恰相反,因為趙曉夢的《釣魚城》精準回答了如何把史詩寫活、把長詩寫短、把大詩寫小等關鍵性問題,我更加堅定了把抒情作為中國長詩未來發展唯一正確走向的核心判斷。
一、作為史詩的《釣魚城》是鮮活的
何謂“史詩”?史詩是一種“莊嚴的文學體裁,內容為民間傳說或歌頌英雄功績,它涉及的主題可以包括歷史事件、民族、宗教或傳說。”(《辭典》)這是傳統意義上的史詩,把它簡單理解為“有歷史的詩”、“逝去之詩”,似乎也未嘗不可。根據所反映的內容, 史詩可分為兩大類:創世史詩和英雄史詩。創世史詩, 也有人稱作是“原始性”史詩或神話史詩,多以古代英雄歌謠為基礎,經集體編創而成,反映人類童年時期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或者神話傳說,如世界最古老的史詩——古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英雄史詩則是一種講述英雄人物(來源于歷史或神話中)的經歷或事跡的長詩,如荷馬的史詩作品《伊利亞特》,中國的《格薩爾王傳》等。相比較而言,英雄史詩更為常見,所以在現代語文中,“史詩”主要指的是英雄史詩,是一定歷史時代條件下的人或人群生活的全景反映。據此,我們不難發現,史詩有題材厚重、宏大敘事、篇幅較長等基本特征。《釣魚城》顯然就是這樣的一部“現代史詩”。
應該說, 每一部史詩都是具體歷史的和具體民族的。不能用一個籠統的歷史時代的抽象的模式去解剖特定的史詩, 也不能用一般的人類社會的尺子去裁量史詩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史詩與歷史有特殊關聯性, 但是即使史詩的歷史印記十分鮮明, 它也不是編年史式的實錄,甚至也不是具體歷史事件的藝術再現。史詩對歷史有著特殊的概括方式, 體現了史詩的創造者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和表現特點。也就是說,史詩是歷史的,但又不單單是歷史的。《釣魚城》再現的歷史是著名的“釣魚城之戰”,從1243年余玠決定復筑釣魚城至1279年守將王立帶領釣魚城軍民投降,計36年,其間尤以1259年蒙哥汗在釣魚城下的敗亡最為引人矚目,這一事件使得氣數已盡的南宋王朝又殘喘了20年,更為重要的是,因為蒙哥之死,蒙古軍隊的第三次西征被迫停滯,大部隊東還,其大規模擴張計劃從此走向低潮。釣魚城之戰不僅影響了中國歷史發展,更是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西方人稱釣魚城為“上帝折鞭處”,所言非虛。36年尤其是后20年的歷史不算長,但它所反映的人心、人性、人情之紛繁復雜,具有超越于歷史之上的普世價值。更何況,我們所談到的“歷史性”指向的從來就不是簡單的時間刻度,不是史冊上沉睡的文字,而是生態的、社會的、人文的歷史。
歷史往往是凝固的,但詩人趙曉夢“十年磨一劍”,在充分占有、研究史料的基礎上,讓釣魚城之戰這一段“沉重殘酷的歷史充滿了人類心靈的體溫,成就了一種血色浪漫的審美特質,既厚重大氣又顯靈性充盈。”(《名家云集合川!研討趙曉夢長詩〈釣魚城〉》,2019年5月15日—華文作家網)也就是說,趙曉夢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觸摸、感知、還原了一段廣為人知而又獨屬于他的歷史,這段歷史因此而變得鮮活,也因此而成為“詩史”和“個人史”。
作為史詩的《釣魚城》,其鮮活之處首先在于對“時間”的獨特把控。一章三人,三章九人,均以人物獨白的方式出現和淡出,你方唱罷我登場,每個人的開頭都是“再給我一點時間”。時間是戰爭這一特定環境下所有人關注的焦點,它充斥著焦慮、折磨、苦痛、勝敗、生死,自然會折射出忠誠與背叛、軟弱與堅強的較量,進而深刻影響到退縮與進擊、抗爭與妥協等等行為選擇。在詩人如此戲劇化的設計中,我們可以窺見不同人的性格與命運,同時跟隨這九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去追問更多人的生死以及家國的存亡,為釣與被釣而糾結,為“石頭”和“魚”這兩個中心意象而沉迷,如臨其境,難以自拔。
作為史詩的《釣魚城》,其鮮活之處還體現在對“空間”的巧妙設置。美國歷史學家彼得·蓋伊在《感官的教育》中說,“完美的虛構能夠創造出真實的歷史,”作為一位詩人,趙曉夢其實也是“歷史的說書人”,把釣魚城之戰這段歷史當作自己想象和描述的對象。他以人物獨白的方式給歷史中的人提供了表演的舞臺,也就是設置了少則三種多則九種甚至更多更繁復的空間。我們當然知道這個空間是虛擬的,但是我們更知道詩人的真實意圖正在于突破傳統的史詩寫作范式——一個中心一個主體——史詩寫作因此而變得更加開放,詩人因此可以更加主動地“牽著歷史走”(學者王本朝語),而非相反。這種多維的空間設置加上步步緊逼的時間調度,就使得《釣魚城》不僅是結構的藝術,也不僅是對錯的價值判斷和愛恨的情感判斷,而是“回到了詩人作為想象能力的主體互動”(評論家霍俊明語)。詩歌和歷史從來都在互相致意,只不過有的人許多時候自造了“雷池”。詩人趙曉夢的大膽探索,對于中國史詩寫作的啟示意義無疑是深長的,這也是我堅持把《釣魚城》認定為一部抒情長詩的重要理由。
二、作為長詩的《釣魚城》是精短的
《釣魚城》洋洋灑灑1300行,在中國的長詩文本中是比較少見的。而且,從資料占有、實地考察、專家咨詢、創意構思到文本撰寫,趙曉夢整整用了十年時間,這個創作周期也是超長的,少有人能如此篤定,如此認真。據我所知,長詩《釣魚城》完成后,從在《草堂》詩刊發表到出版單行本再到推出精裝本,趙曉夢一直在不斷聽取各方意見,對文本進行修改和訂正,他為把釣魚城之戰這一段重要歷史寫進詩史和文學史進而以特別致敬的方式把這段歷史存留下來、傳揚開去,付出了艱辛的努力。試問,當今詩家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如果僅僅把趙曉夢的所有努力歸結于他作為合川人對故鄉的深沉情結,我以為站位還是偏低。透過《釣魚城》,我們應該清醒看到,趙曉夢所展現的長詩寫法,打破了敘事長詩的傳統和套路,彰顯了中國詩學一以貫之的抒情精髓,形成了新的人文邏輯和抒情倫理,為中國抒情長詩的寫作開創了一條別開生面的新路,這才是我們應該予以特別關注和仔細研讀的。
從寫作的操作性策略來看,《釣魚城》的一個顯著特點就在于:寓長于短,通過精短來構建長詩的厚度和韌性。相比于36年的時間跨度,詩人截取的華彩片段是短的;相比于三組九人上演的一場別致“詩劇”,每個人的獨白式詠唱是短的;相比于這場戰爭中千軍萬馬慘烈廝殺的場面和千絲萬縷復雜糾纏的態勢,《釣魚城》所容留的停頓和遲滯也是短的。在以“抒情的復調”(詩評家張德明語)為特征的結構形式下,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短兵相接”,這就確保了歷史敘述的“觸目驚心”,也極大地豐富了歷史的人文內涵。
從詩歌語言的表呈來看,正如著名詩人吉狄馬加所言,“《釣魚城》這一首長詩仍是若干短詩的合成”,但與眾不同的是,這些短詩保持了相當一致的韻味和相當諧和的調性,詩中每一個人的獨白既具有獨立性卻又共同聚焦于“釣魚城”這一個制高點,一路讀來,讓人興致盎然不覺乏味。也就是說,趙曉夢用短詩的寫作手法,多少令人匪夷所思地完成了一部史詩巨制。短詩的語言講究爆發力,強調靈感,畫面感強,節奏趨于簡捷明快。拿當代著名詩評家呂進先生的話來說,當字詞不再僅只具有詞典意義,那么它們就構成了“詩家語”。這樣的“詩家語”在《釣魚城》里俯拾皆是。比如蒙哥在長詩開篇就迎來了“彌留之際”,慨嘆“再給我一點時間……長生天!/讓我醒來,給草原的遺囑留點時間。/彎弓揚鞭,這一趟走得有些匆忙和/自信,忘了誰來繼承/成吉思汗的江山?”“白鹿洞書生”余玠踞守“用石頭釣魚的城”,在兩軍對峙時說出“寬恕兩條江的無知,不如扶住/桅桿上的帆,停靠眼睛的疲憊,/停靠江水游蕩的往昔”,興元府都統兼知合州王堅感嘆“酒液熨過肺腑,山風吹來烏云,/胸中的詩句亂花飛絮,錦袍上的/神韻拾不起散落的月光”,人稱“四川虓將”的張玨在困境中堅信“濺落在時間刻度上的火星,注定/不會悄然熄滅。即使遁入塵埃,/也會成為滄桑黃卷中淡淡的殘痕。”攻守之間,人物的性格與命運躍然紙上,牢牢地攝住了我們的眼睛和心靈。
以精短而致跌宕起伏,在長詩建制中敢于讓每一個人物的詩性獨白在十幾行、二十來行的分節排列中不斷爆發,且能氣韻不失,趙曉夢做到了把長詩寫短,其實也巧妙地達成了“短中見長”。這一稍顯“冒險”的舉措,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為我們的長詩寫作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三、作為大詩的《釣魚城》是小而具體的
所謂“史詩”,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重大歷史事件之詩”。我國著名的民俗學家、民間文學大師、現代散文作家鐘敬文認為,“史詩用詩的語言, 記敘各民族有關天地形成、人類起源的傳說, 以及關于民族遷徙、民族戰爭和民族英雄的光輝業績等重大事件, 所以, 它是伴隨著民族的歷史一起生長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一部民族史詩, 往往就是該民族在特定時期的一部形象化的歷史。”其間言及的天地形成、人類起源、民族遷徙、民族戰爭、民族英雄等等,無事不大,所以詩界常常將史詩稱為“大詩”。從題材上看,《釣魚城》無疑是一部“大詩”。
從內容和思想價值來看,《釣魚城》也無愧“大詩”之謂。或許在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眼里,釣魚城之戰應是諱莫如深的,這也是釣魚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顯得沉重而寂寞的根源。趙曉夢對此心知肚明,但他并不回避。他讓蒙族人蒙哥、蒙哥夫人、汪德臣,漢族人余玠、王堅、張玨、熊耳夫人、李德輝漸次登場,站在攻城、守城、開城這三個不同的立場和維度之中,吐露心聲,感時抒懷,論事究理,不同的政治理念、民族情感、人生價值等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最終一一展現。而詩人作為導演或觀察者,也在這個過程中表達了“不言之言”——對人性之光的擦亮和深度審視。趙曉夢自己說過,“歷史已經過去,我們只能無限還原它,而不能武斷地認為我們掌握的就是歷史。”所以他的視野、胸懷和氣度是十分開放的,他既無意于為家鄉釣魚城代言,也不想藉此完成所謂的“自我精神救贖”。他只是在致力于“還原”,讓讀者看到“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中‘何者為人、‘人能何為”,并且引導讀者去思考“華夏文明何以綿延不息等命題”(詩人、歷史學博士李瑾語),我非常認同李瑾博士的觀點,“《釣魚城》相當于‘活化石,它既秉持了時代對歷史的反思,也承載了歷史對當下的投射,從而具有了文獻和文明的雙重價值。”
從藝術創新來看,《釣魚城》也有“大詩”質地。學者王本朝說“詩人趙曉夢把‘釣魚城之戰這段重要歷史帶進了文學史”,我更認為,因為長詩《釣魚城》,這段歷史從此可以被稱之為“詩史”,閃爍著與別的歷史不一樣的光彩。誠如著名詩人、作家、評論家宗仁發先生所言,詩人趙曉夢的“文學觀、歷史觀因此有了非常合適、合理的把握尺度”。同時還要看到,但凡關涉歷史人物的寫作,很容易落入英雄贊歌式、正義審判式的窠臼,或者被簡單的勝負、結果所左右,使得作品呈現出“高大上”或“扁平化”的樣態。而《釣魚城》采取的是個人化的視角、個性化的語言,設身處地,為九個人物安排了不同的境遇,設置了相對應的關系,進而通過獨白凸顯了各自不同的思想沖突和情緒表達,整首詩就像一部多幕劇,高潮迭起,十分生動,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我曾在一篇文章談到過,“大詩”多為“宏大敘事”,而“宏大敘事”往往遠離日常的生活體驗,作為一種描述和揭示世間真理的理論體系,與其說是一種歷史敘事,不如說是一種追求完滿的構想,不免帶有神話的色彩。所以,從史詩寫作的操作性層面來看,“大而不當”是一個值得深思且需引起注意的問題。趙曉夢的《釣魚城》在這一點上是清醒的,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小而具體。
《釣魚城》從一開始就是奔著“把大詩寫小”的路子去的,他以“再給我一點時間”來調度全篇,把九個人物置于攻城、守城、開城的不同任務環境和具體場景之中,這就為讀者的進入打開了方便之門。其次,《釣魚城》中有兩個反復出現的意象——魚和石頭,這是其作為抒情詩的重要標志。正如著名詩人、詩評家唐曉渡認為的那樣,“魚和石頭的關系發生了反轉,釣和被釣的關系也發生了反轉,這里面更多體現了詩歌的力量。”呂進先生也認為,“‘石頭與‘魚給全詩增添了簡約性和生動性,給讀者以想象空間的遼闊”。必須指出的是,《釣魚城》只是一首與歷史有關的詩,其重心不在寫史,而在寫史中人物,在詩人以史為憑的想象中展現人物的命運沉浮,閃射人性之光。正因為寫得小而具體,我們能感覺到這些人物是生動鮮活的,并與讀者自己心中設計的人物形象形成互動。比如著名詩人尚仲敏就認為,九個人物里面寫得最好的是熊耳夫人,里面最好的一句是“如果你想我/就到后院竹林來吧”。
關于“把大詩寫小”,還必須注意細節。《釣魚城》的小而具體,也歸功于詩人趙曉夢對細節的精心琢磨。人物所處的環境有細節,說話的語氣有細節,語言中投射的心理變化也有細節……如果這首“大詩”能在每個人物出場前確切交代一下其身份、背景以及與其他人物的關系,而且在九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外,設置一、二個小兵或平民,讓處于戰爭中的小人物“一展身手”,或許既可以豐富整首詩的細節,更能增強讀者的“代入感”。
總之,一部《釣魚城》把史詩寫活了,把長詩寫短了,也把大詩寫小了。正如中國作家網有關“《釣魚城》長詩單行本首發式暨研討會”的新聞報道所及,“宏大敘事與個體抒情有機融合,歷史意識與生命體驗互滲互補,體現了詩人趙曉夢對復雜歷史全新的解讀能力,對抒情長詩罕見的掌控能力。”更為重要的是,趙曉夢的《釣魚城》,注入了新的文人氣質,構建了新的寫作模型,為中國抒情長詩寫作昭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向度,堪稱新的長詩藍本甚至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