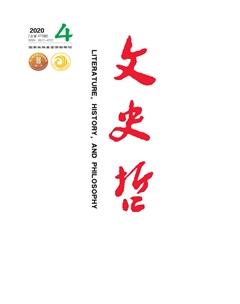古今之變與公私德行的現代理解
編者按:本刊2020年第1期所刊載陳來先生《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一文,指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是政治公德取代、壓抑、取消個人道德,并相應地忽視社會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會公德和個人道德之間失去應有的平衡。文章進而認為,恢復個人道德的獨立性,并大力倡導社會公德,是反思當代中國道德生活建設的關鍵所在。此論即出,遂引發人文學界強烈關注與反響,蔡祥元、任劍濤、肖群忠等先生積極屬文參與討論。在編者看來,這一話題的挑出,無疑切中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倫理變遷的流弊。不過,道德雖然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但如黃仁宇先生所言,道德非萬能,它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換言之,道德問題從來就不僅僅是個倫理問題,它不僅關涉人們的價值理念,更關涉法律、規則與制度,諸元素之間互為制約,共同決定著社會演進的方向。當此社會諸領域皆面臨深刻變革的新時代,這種互動與約制,尤其顯明。鑒此,本刊自本期始,開辟“道德、理念與制度”專欄,圍繞相關話題,展開更具開放性與持續性的深入討論,誠邀方家貢獻學術智慧,共饗思想盛宴!
摘 要: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是一個需要辨析的問題。循內部解釋脈絡,公私德行的關聯與偏重需要一個平衡擺;以外部解釋的理路,公私德行的功能與效用需要確定兼綜性。如何平衡與兼綜,需要一個社會坐標。古今之變,是分析公私德行狀態的前提條件。在古代視角,私德的決定性顯而易見;在現代視角,公德的優先明確無誤。在現代處境中,不存在從私德直接貫通到公德的可能性。古代儒家以私人德性理解德行“公共性”的進路,需要轉進到公私德行分流的現代結構,但私德的社會倫理效用與公德的政治倫理功能必須分別確認。這不是一個在中西差異角度審度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古今變局的角度才能夠深切理解的問題;公私德行分流,是一個人類的普遍處境,而不是一個地域的特殊遭遇。
關鍵詞:古今之變;公德;私德;儒家倫理
陳來教授近期發表的大作《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①,提出了一個切進中國現代道德建設的方向性問題。他的論述,在中西比較、古今對堪的框架中,以自覺的歷史辨析顯示出他的思想史功夫,以中西比較和當下針對展現出他的現實關懷。可以說,該文論及的問題,是所有關注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處境,關注當代中國道德建設和政治發展問題的人們應予重視的問題。筆者受其啟發,試圖沿循陳來教授的思路往下思考,縷析一下古今之變大局中的公德私德之作為思想史、倫理變遷與政治轉型問題的復雜內涵,以便幫助自己厘清一下公私領域分化、公德私德所指,以及背后指向的中國現代轉型及其道德建設進路。
一、公私分界與公德私德
陳來教授對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偏向的指陳,重在近代思想史描述和當代政治史表現。他的解決之道是重啟儒家傳統道德,以有效對治中國現代道德建設的偏失。他的眼光,緊盯的是儒家倫理的現代處境,投向的是近代以來思想家重視公德、輕視私德的論斷,落點則在當下中國道德建設的糾偏。從總體上講,陳來教授是要解釋中國現代道德建設的適宜方案為何的問題。在他的解釋中,各種求解方案相互交錯,引導人們在紛繁復雜的求解線索中去思考相關問題的究竟。其中,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重要思想家,以及在相關論述中的西方重要思想家論及公德私德問題的觀點重述,可以說是他對設定問題的靜態解。這是一種就中西思想家論及公德私德之為思想史的既定事實的解釋模式,是不為解釋者意圖所能變更的歷史重述。這樣的解釋與他力圖從中引申出對治中國當代道德建設偏失的解釋即動態解聯系在一起。這一解釋進路是就中西互動、傳統與現代互動的交互關系作出的解釋。靜態解也可以是說是一種局部解,而動態解則是一種整體解。關乎公德私德問題的局部解,是一種就倫理而言倫理的解釋,即在撇除倫理的外部社會要素及其變化的情況下,對公德私德論述的演進進行描述和分析;而關于公德私德問題的整體解,是就社會言倫理的進路,這一解釋進路將倫理作為社會要素之一對待,一旦嘗試解釋它的變化,便須在諸社會要素(政治、經濟、文化等)之間求得解釋理由。陳來教授在幾種解釋模式之間跳躍,當然是想獲得幾種解釋方式的優勢,以求對公德私德問題,尤其是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有一個較為可靠與可信的解釋。但從分析的側重點來看,他更重視靜態解和局部解。因為他強調所要矯正的重公德輕私德偏向主要源自思想家的既定論述,而且主要是從倫理自身的公私德行平衡視角著眼的。相對而言,他對諸思想家論及公德私德的現代條件,以及公德與私德問題的現代社會變遷背景著墨不多。
陳來教授的論述,在其清理關乎公德私德的思想家觀點重述上,也就是他設定的主題即重公德、輕私德的思想家觀點的重述上,以及在政治史角度對當代中國關于道德建設的國家權力謀篇布局的描述上,對人甚有啟發,但在西方思想家何以如此論述的理論條件與社會背景,以及中國近代以降何以會更加重視公德的深層理由上,給出的論述則讓人產生興味無窮的追究沖動。換言之,陳來教授的論述在描述一個倫理思想史與政治史的部分事實上,具有可靠性與可信性;但在思想與社會互動的分析上,留下了太多需要進一步辨析的問題。
從思想史與政治史相關角度看,公私德行及其關系,存在三個解釋框架:一是傳統框架,二是現代框架,三是傳統與現代的關聯框架。首先,從中國傳統的解釋框架來看,乃是一個關乎公私德行的傳統知識梳理。公德私德的傳統規定是清晰明確的。從字義上看,私,《說文解字·禾部》:“禾也。從禾,厶聲。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段玉裁注:“蓋禾有名私者也,今則叚私為公厶。倉頡作字,自營為厶,背厶為公。然則古只作厶,不作私。……北道,蓋許時語立乎南以言北之辭。《周頌》:‘駿發爾私。毛曰:‘私民田也。”許慎撰,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562頁。在《韓非子·五蠹》,私有“自環”“自圍”的意思。從理念上講,公的含義分為兩組,在《韓非子·五蠹》,是“‘背厶,即‘解開圍圈的意思,由此產生與眾人共同的‘共,與眾人相通的‘通。在《說文解字》中,是作為‘私,自環的反義——‘公,平分也;而第二組,是從《詩經》的例子推出的:‘公是對于‘共所表示的眾人共同的勞動、祭祀場所——公宮、公堂,以及支配這些場所的族長的稱謂,進而在統一國家成立后,‘公成為與君主、官府等統治機關相關的概念”溝口雄三:《中國的公與私·公私》,鄭靜譯,孫歌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56頁。。
就前者言,公私的相對界定已成定論。就后者講,溝口雄三枚舉式列出呂不韋、《禮運》和賈誼的詮釋,可知公的中國傳統含義。呂不韋說:“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呂氏春秋·貴公》)其義曉暢,不必再釋。《禮記·禮運》的相關表述更為明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里所謂公,鄭玄的注解為“猶共也。禪位授圣,不家之。”孔穎達疏解為:“為公,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圣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朱彬撰:《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331頁。賈誼所說,也呈現同一宗旨,“為人臣者,主而忘身,國而忘家,公而忘私”(《漢書·賈誼傳》)。可見,公德是君政時代的君權踐行為政治共同體謀利的政治理想而凸顯出來的德行。當“帝政成功,君政廢墜”參見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2頁。以后,這樣的公便轉移到皇帝身上,一家之姓的私權被涂上了公權的色彩。其時,行政層面的官僚階層行使具體權力,私心自用,也就很難有什么公心了。私心自利,而公心利人參見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第56頁。,兩者就此分流。
公與私、公心與私心、公德與私德,可以從行動形態與觀念形態兩個視角來審視。一方面,在行動形態上,如果將公德與私德理解為與中國特定的公私劃分相聯系的德性,那么可知,就君政理想情形言,私是一己的偏私性,公是以權謀共;就帝制確立以后的現實情形言,私德乃是與君主、官府以外的民眾各自的謀生相關聯的德性;而公德則是與君主、官府等統治機關聯系在一起的德性。在觀念形態上,儒家倫理思想對之進行了系統的闡釋。這種闡釋,圍繞兩個面向展開,一是在君政時代確立的天下為公的理想,二是在帝制時代矯正私心自用、權力偏失的去私理念。前者在先秦儒家那里得到充分闡揚,后者在宋儒那里得到系統發揮。“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己欲立則立人,己欲達則達人”(《論語·雍也》),“博施濟眾”即“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老安少懷”“子路曰:‘愿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的仁心仁政機制,體現了前一論述宗旨。“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人只有一個公私,天下只有一個邪正”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三《學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28頁。,體現了后一論述旨趣。對公、私與公德、私德的上述闡釋,陳來教授也作了縷述,但對倫理含義揭示較詳,對政治含義著墨不多。
其次,從現代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的相關角度看,這是一個關于公私德行現代闡釋的知識依托視角。在此視角,需要確立兩個相關審視角度,一者,只要討論公德與私德,就必須先行探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立。二者,公私德行是與社會變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德性結構,只要是在現代社會的特定視角觀察這一問題,就必須將現代社會結構作為探究公私德行的前提條件。就前一個問題看,公私德劃分與公私領域的分野,是兩個緊密關聯在一起的問題。一般而言,脫離了私人領域,就無所謂私德;離開了公共領域,也就無所謂公德。從貫通古今的理論線索上講,公私德行具有緊密關聯的存在論特性,但在古代社會,私人德行之產生公共效能,即私德對公德發揮影響力,大致限于政治性人物。因為只有他們才能以權力貫通私人性空間與公共性世界。必須注意,這里是以“私人性”與“公共性”這種在形式上仿照“私人”與“公共”的概念來看待古代社會的公私分界的。在實質上,除開古希臘以外的古代社會,公私世界并不存在清晰的分野,公私德行的分流因此也不是那么清晰。在古希臘,因為家政問題這些“私”的因素被隔離在城邦政治的“公”的空間之外,因此具有較為清晰的界限,但古希臘公私領域的互動關系并沒有呈現出來,而且其族群公共的特殊結構,也明顯妨礙了公共世界平等接納成員的公正性。一旦因為戰功等因素,奴隸與外邦人獲得公民資格,反而發揮出顛覆古希臘公共生活秩序與公共德行的作用這在當代西方的公民人文主義、公民共和主義者那里,得到了深入系統的描述與分析。為不致模糊論述焦點,這里不對其進行思想史的梳理。參見任劍濤:《公共的政治哲學》第三章《古典公共與現代公共》第一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51169頁。。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結構分野,公私德行的相應分流及其互動結構的呈現,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事件。這是因為,神人關系或教權與王權的分野、家庭父子關系與政治君臣關系的切割、現代個人的挺立、個人財產權的凸顯、國家與社會的分流、立憲民主制度的建構、個人與社會和國家距離的保持,才真正將一個各具獨立意義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有效區隔開來。盡管這兩個領域及其德行模式在存在論的意義上是不可分割地依存在一起的,但在社會認識論意義上,兩者的邊際界限已經能夠為人們清晰地加以把握,并且在德行實踐上展現出構成特征大為不同的樣態。如果要對公私領域給出一個最簡明扼要的界定,按照漢娜·阿倫特仿照古希臘公私領域劃分給出的公私定義,可以說公共領域就是曝露在眾人面前的領域,而私人領域則是家庭或家庭式關系的隱蔽性領域參見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44頁。本段引號中文字見第3235頁。。阿倫特就公共含義明確指出:“首先,它意味著任何在公共場合出現的東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聽到,有最大程度的公開性。”在其中,親密生活的最大力量,如心靈的激情、精神的思想、感性的愉悅,都會將不確定性轉換為公共顯現的形式,同時去私人化(deprivatized)和去個人化(deindividualized)。“其次,‘公共一詞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是共同的,并且有別于我們在它里面擁有的一個私人處所而言”,它“把我們聚攏在一起,又防止我們傾倒在彼此身上”。換言之,公共領域就是政治權力領域。就后者即私人,阿倫特也指出,為私密而存在的家庭私人領域,必然處于公共領域以外,它是隱蔽的,與公共領域的公開性特點恰成對照。
在阿倫特的論述中,寄情古典公私關系,失于省察古今之變,是其對公私的明確分界之外需要知曉的得失。在現代處境中,公私領域得以分界并積極互動,是從洛克、密爾到羅爾斯的西方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所確立的理論原則。當個人轉讓權力給國家的時候,保留了不可分割、褫奪和轉讓的生命、財產、自由權利(洛克)。這是一種為傳統社會所無的社會自由(密爾)。在立憲國家中,國家權力必須公平公正地對待自己所有的公民成員,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應當向先天與后天都處于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傾斜(羅爾斯)。循此,國家便具有了健全的公共建制、充分的權利保障和有效的限權機制參見任劍濤:《公共的政治哲學》第四章《公權、私權與政治、非政治公共領域》(第217278頁)及第七章《國家、公民與公共的政治機制》(第413477頁)。。在公共政治領域中,掌握或潛在掌握權力的人群,自然就必須具備高度自覺的公德意識,并恭謹地循公德規則行事,否則就會受到社會的譴責與法律的制裁。至于其私德如何,那是這一人群在社會空間和私人生活領域被人關注,甚至于是自我嚴格約束的問題。而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公私德行如何,完全是自主、自治和自律的社會公眾在私人領域與社會公共(共同)領域中自守與相互督促的問題。一般來說,國家權力不應直接干預社會事務與私人事務。就此而言,個人、社會與國家的三層結構,成為現代國家道德儀軌的三類載體,不能像古代社會那樣對不同德行載體不加區分地以私德和公德來抽象處置。尤其是其中的個人,在家庭或家庭式生活世界中,屬于絕對的私人領域,而在面對他人、社會和國家的時候,才成為現代政治哲學所處置的“個人與國家”軸心論題中的獨特主體。私人與個人不能混同論述。在這一方面,陳來教授對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描述與分析,以及對西方學者關于兩類道德的論述上,重視是明顯不夠的。似乎在他作為論述中國公私德行問題的西方理論背景上,古今之變不是一個所論問題的前提條件,而僅僅是一個虛化的背景而已。這正好印證了陳來教授的相關論述確實有一種靜態解與局部解的特點。
從傳統與現代關聯的角度看問題,應當是陳來教授論評公德私德問題預設的解釋框架。這一解釋框架,與設定古今之變為前提的解釋框架差異甚大。因為傳統與現代的配置選項,可以是對立的,也可以是直通的,還可以是轉進的。古今之變將傳統之為傳統、現代之為現代作為兩個問題對待,以避免需要重視的邊際界限被輕率地忽視。同時,這不一定會使傳統與現代發生對立,因為在將傳統與現代的邊界清晰呈現出來的情況下,才足以清楚論述兩者的關聯性;重視古今之變,當然拒斥傳統與現代的直通說法,因為現代相對于古代確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現代降臨豈能在傳統中求解;至于從傳統轉進到現代,則需要確認傳統轉變為適應現代形態的先行性,否則,一種原教旨的傳統戒條是不可能有效作用于現代道德生活的。如果強行以原教旨的方式將傳統楔入現代,那就只會導致明顯的認知錯誤,甚至引發社會政治悲劇。由于陳來教授大致圍繞公德與私德孰輕孰重及其平衡關系展開論述,基本脫離了公德私德據以呈現的社會前提,因此由其論述可以導出的結論必然是傳統倫理可以直貫現代社會。盡管他論及儒家私德傳統可能在當下,尤其是中國當下道德建設中發揮怎樣的積極作用時,似乎有一個現代社會的預設前提,不過因為他對此吝于下筆,因此留給人們一種儒家私德主張可以直接作用于現代社會的印象。這就明顯表現出將公私德行作為抽象的觀念問題對待的“脫嵌”缺陷,即脫離現代社會與國家建構的具體需求,將公私德行作為與國家狀態與社會處境關系不大的獨立化社會要素處置了。但陳來教授恰恰是在當下中國社會與國家需要什么道德規范的主旨下展開論述的,設定中國當下社會是在努力建構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那么他的解釋框架必由第三框架主導。在三種框架中,第二框架是連接第一框架與第三框架的必須中介,而陳來教授似乎從第一框架直接跳到了第三框架,第二框架差不多是一帶而過,這就使得其論述的自洽性成為問題。
不是說陳來教授完全忽視了第二框架的解釋,他為切入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論題,對其知識背景,也就是現代西方重要思想家的公私德行論述,先行下了一番功夫。但由于他基本上遵循一條關注直接論及個人道德與社會道德劃分的論述線索,如其選擇性敘述的亞里士多德、休謨、康德、邊沁、密爾、涂爾干、斯洛特及日本學者的論斷,而對那些關系到公德私德分流及其社會政治背景論述顯得必不可少的思想家的言說,則沒有提及或甚少關注。這樣的論述進路直接明了,但重要遺漏就很難避免:古今之變與公私德行的關系線索,因此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這恰恰應該是他論斷公德私德問題缺一不可的另一個重要維度。
二、以傳統解現代偏執?
具體講來,陳來教授對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論述,主要是基于兩個事實陳述:一是近代以來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思想家基本上都表現出這樣的致思偏向,二是當代中國的道德建設大致體現出如此這般的行為導向。分別地看,這兩方面的描述都是比較符合事實的。就前者言,他依序敘述和扼要評論了梁啟超、劉師培、馬君武、章太炎對公私德行的看法。舉其大者,可以歸納為這樣幾個共性:一是公私德行高度相關,二是公德與私德是兩種德行規范,三是中國古代高度重視私德,中國現代必須轉而重視公德。梁啟超的幾段話,基本上反映了幾個論者大致趨同的看法,值得單獨提出來重述。梁啟超指出:“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于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為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539頁。這里對公德私德進行了一般界定,也對公德私德的關聯性作出了強調。
落實到中國傳統來看,“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第539頁。。他列出儒家重要典籍中的諸德性,通通歸于私德范疇,基本屬于“一私人之所以自處”之德,這就沒有呈現出應有的、公私德行皆具的道德體系全貌。在梁啟超看來,相對于現代國家而言,中國所表現出的那種公德缺乏定勢,對現代建國發揮了消極作用。“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第541頁。而現代國家的道德特征恰好相反,如英國、法國、美國,各自憲法的德性落腳點有異,但基本精神則高度一致,那就是“為一群之公益而已”。這就是現代道德的特質。“是故公德者,諸德之源也,有益于群者為善,無益而于群者為惡,無益有害者為大惡、無害亦無益者為小惡。此理放諸四海而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第541頁。為此,梁啟超特別強調道德的變遷性質:“德也者,非一成不變者也(吾此言頗駭俗,但所言者德之條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亙萬古而無變者也。讀者幸勿誤會。本原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范圍天下萬世者也(私德之條目變遷較少,公德之條目變遷尤多)。然則吾輩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敢進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第541542頁。在將公德與新道德相提并論的情況下,梁啟超把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尚武都作為公德主題進行論述。
在這樣的視域中,他仍然論及私德的公共影響:“夫所謂公德云者,就其本體言之,謂一團體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構成此本體之作用言之,謂個人對于本團體公共觀念所發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故一私人而無所私有之德性,則群此百千萬億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視于眾而忽明,聾者不能以聽于眾而忽聰,怯者不能以戰于眾而忽勇。故我對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對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團體,無有是處,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學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國民之私德,有大缺點云爾。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欲從事于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第633頁。在這里,梁啟超沒有表現出任何輕視私德的意味,相反極為重視私德,以及私德對公德的重要奠基作用。公私德行的相伴而在、相互為用,正是他申論的核心觀點:“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謬托公德,則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養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焉矣。”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第634頁。他進而分析道:“私德之墮落,至今日之中國而極。”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第634頁。而專制政體、近代霸者、國家戰亂、生計所迫、學術失救等種種因素,皆是造成這一窘迫局面的導因。據此,梁啟超對“人人之糧,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第642頁。的私德進行了專門論述,他認為,“以新道德易國民”,非借助“泰西新道德”不可,但其只能久久為功。因此,“吾祖宗遺傳固有之舊道德”成為維持道德秩序的一線生機,但這需要正本清源以立志、慎獨而為以去賊、謹小而行以積善,由此以私德輔成公德。
陳來教授對梁啟超的公私德行觀的敘述比較詳備,何以筆者還要縷述梁氏之論呢?原因有三:一是通過對梁氏公私德行論斷的再次敘述,可以確知,梁氏在倫理學的一般視角而言,并沒有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他在中國建構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的特定角度,確實強調過公德的重要性,但并沒有因此忽略私德的重要性,以及它對公德建設所具有的意義。二是梁氏所論,基本的社會政治參照系是現代社會與國家。換言之,即是筆者所重視的古今之變。如果忽視梁氏作出相關論述之關涉古今之變的背景條件,那么就基本上脫離了梁氏論斷的語境,變成評論者自己對相關論述的選擇性重述了。三是梁氏認為,現代社會與國家的建構,需要具有新道德的新國民,而這必須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但由于這種借鑒歷時長久、緩不濟急,因此需要從舊道德中汲取現成可用的資源。梁氏所論,對轉型中國的道德建設,可以說是抓住了關鍵問題的不易之論。因此,陳來教授以梁氏之論作為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偏向的標志性人物,有些委屈梁氏了。即便從梁氏看開去,陳來教授所列舉的其他幾位重要思想家,也同樣是在現代轉變的參照系中,才著重指出中國缺失公德傳統,僅重私德建構;甚至在現代公德框架中來看私德,中國舊道德中的私德也不是建立在自由、權利、自尊與自治基點上的現代私德,其確實不足以支撐現代公德。如果忽視了這幾位論述者論及公私德行所設定的古今之變前提,僅從直接的文字表述上看,似乎確實存在重視公德、輕視私德,尤其是輕視舊道德中的私德的缺陷。但在古今之變最具張力的晚清、民國階段,現代社會與國家建構成為中華民族面對的最為緊要的任務,私德確實在任何意義上都很難直接擔負起推動社會轉型與國家建構的任務。因此,在公德與私德總體、長遠的平衡機制中,當下與相對意義上的傾斜性就自然會擺動到公德一端。這正是陳來教授列舉的幾位著名人物將公德的功能置于私德之前和之上的原因。
陳教授似乎忽視了中國的現代轉型處境,而僅僅著眼于倫理理念的范圍中公私德行兩者之間的孰輕孰重問題。因此,他認為,只要這幾位思想家強調公德的重要性,而沒有同等強調私德所具有的同等重要性,似乎就陷入了打破公私德行平衡結構的僵局,因此必須矯正公私德行的傾斜結構。這就可能蘊含一種非歷史,甚至是反歷史的萬世一系的理論預設:僅僅看到了公私德行都有助于“群”的作用,沒有看到群自身建構的歷史演進所呈現的公私德行偏重程度的變化。而且,如前所述,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相關論述,尚且沒有像陳來教授認定的那樣重公德、輕私德。即便是馬君武認為的國人缺乏私德之論,也是針對現代私德作出的相應批評,而不是針對中國傳統倫理結構作出的判斷參見陳來教授《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一文中對馬君武公德私德觀的評述。。因此,陳來教授的相關批評頗留人以論點主觀先設,而與論述對象的主張似乎關系不甚緊要的感覺。
陳來教授對重視公德輕視私德的述評,并不都是針對思想家而來。他的論述,其實可以分為兩截來看。當他將論述筆觸轉到公私德行建設的國家導向上來的時候,便脫離開思想史線索轉到了政治史脈絡。這是陳來教授論及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偏向與流弊的另一個歷史段落,一個相對于近代而言的當代段落。他將兩個階段的兩條論述線索一貫而下,有些讓人費心琢磨。因為,姑不論近代思想家論及公私德行的學術立場與對策思維的特殊性,當代的政治家與治國者涉入公私德行領域的時候,肯定不是基于學術理解的進路,而是針對立國需要與政策思路作出的相關決斷。這是兩個很不相同的歷史階段與政治局面,其思想很難作直接的貫通審視,而群性政治就更是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形式上看,在這兩個歷史階段或兩種政治狀態下,公德建構的倡導相對于私德建設的關注,似乎具有某種共同的優先性特征,但這種優先性的定位,一是學理分析和議程設置,一是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其間的結構性差異毋庸多言。就形式相似性而言,陳來教授切中肯綮地指出:“新政權重視政治性公德,輕視個人的私德,主張道德是意識形態,強調道德的政治功能,這些都已顯示出此后幾十年在道德和公德問題上的基本導向和偏向。”陳來:《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但就兩個歷史段落的差異性及其形式上的重公德輕私德的共同性怎樣關聯起來的問題,陳來教授沒有進行相關分析。
陳來教授從兩個歷史階段、兩種集群結構的公私德行定位中,得出了非常強勢的“近代以來”中國一直重公德輕私德的結論,并就此給出了他診治這種偏向及其流弊的方案。這一方案的直接藥方是建構政治公德、社會公德與個人道德的平衡機制:“我們的視角是真正倫理學和道德學的,以個人基本道德為核心,認為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是政治公德取代個人道德、壓抑個人道德、取消個人道德,并相應忽視社會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會公德和個人道德之間失去應有的平衡。因此,恢復個人道德的獨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導社會公德,是反思當代中國道德生活的關鍵。”不論陳來教授對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偏向的描述與分析本身有什么偏向的問題,他診治重公德、輕私德這一偏向的藥方可謂對其癥下其藥。進而看他開出的這一藥方中對診治偏失思想病癥最為緊要的一味藥,正是儒家倫理:“至于公共道德,也是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維度,在我看來,公共道德自然很重要,但相比于個人道德而言,公共道德的問題并不難解決,關鍵是政府和社會組織要像明治后期的日本一樣,全力抓住這個問題,使之成為社會和媒體的關注焦點,持之以恒,必然有效。……我們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問題則是,政治性公德擠壓了社會性公德,使社會公德始終很難成為社會的關注焦點,而政治公德和意識形態論題永遠成為關注焦點。……我們以大陸為主,強調最重要的是加強私德中的個人基本道德,這不僅與我們對中國大陸道德生活史的判斷有關,亦是我們的儒家文化立場所決定的。”陳來:《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儒學美德論》,第80頁。陳來教授終于在文末展露出關注近代以來中國重公德、輕私德偏向的思想宗旨:以私德為核心結構的儒家倫理,才能診治中國近代以來道德建設的偏向與流弊。非此,則這一偏向與流弊無法救治。
分析起來,陳來教授的這一結論與其證據之間,有些錯位和跳躍:從歷史演進的維度看,相對于民國時段思想家關于公私德行的論述而言,其實沒有那么緊要的偏失與流弊需要救治;相對于人民共和國階段,國家權力方面確立的道德建設方案,本是國家權力方面期待社會公眾和公民個人如何忠誠于國家的德性要求,因此并不是一種學理商討,而是一種政策導向。將兩者放置到一條線索上論述,似乎有些差強人意。從陳來教授的儒家立場來看,他在公私德行論題上所論及的民國思想家,并沒有從傳統之為傳統的角度怠慢儒家的意味,因此他對之伸張自己的儒家立場,有些缺乏針對性;如果是在當下政治情景中看待問題,其實需要從政治公德、社會公德與個人道德的全方位學理檢證來審視道德建設問題,而不僅僅是從儒家個人基本道德的角度觀察和分析問題。
如前所述,以陳來教授對公私德行的論述進路來講,他是在傳統與現代相即性的框架中切入論題的——他關注中國傳統公德私德的構成狀況,關心現代倫理發展中對公德與私德關系的論斷,關切中國現代道德建設中儒家傳統倫理精粹的激活及其效用,但當他將所有關懷都落到儒家個人基本道德如何冰釋現代道德建設難題上面時,其為自己先行設定的結論逆溯歷史依據的話語策略,就很難具有說服力了。這一方面是因為現代道德建設難題的解決,需要在現代脈絡中來求解,而不可能以回到歷史中的方式求得答案;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儒家個人基本道德是與中國傳統社會與國家相融無間的道德構成面,如果要抽離它的歷史語境,成為解決現代道德問題的可用資源,那就必須對其進行現代闡釋;再一方面則是因為儒家基本個人道德的現代闡釋缺少不了現代思想家與現代制度的重塑。因此,只是在儒家立場上斷言儒家倫理就可以診治現代個人道德缺失,未免有一種拒斥思想市場,一家包打天下的意識形態取向,而這正是陳來教授所要拒斥的道德建設進路。如果說陳來教授費心對近代以來中國公私德行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加以論述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引導出儒家診治時弊的排斥性地位與功能,那么他事實上也就堵塞了因應現代邏輯解決現代問題的通道,這就成了近代以來文化保守主義抗拒現代變遷的通常表述。
問題還有另一面。像陳來教授那樣以儒家傳統倫理為現代道德生活補偏救弊,不僅需要將儒家傳統倫理提純,將之再造成具有跨越傳統與現代空間的普適性倫理;而且需要將儒家倫理完備化,使之具有全方位的適用性;進而還需要將現代道德生活延續自身邏輯改善自身的可能性杜絕掉,這樣才能為儒家傳統倫理出場解決現代道德生活困境提供思想地盤。試圖做到這三者,都會遭遇一些特定的困難。首先,一個現代處境中的人,面對儒家倫理,會遭遇兩種必須厘清的解釋進路,以免相互干擾的解釋讓兩種解釋都不可靠:一種解釋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儒家傳統倫理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相宜關系,另一種解釋是為了疏通儒家傳統倫理直貫地作用于當下的進路。前一解釋比較容易切入,解釋結果也比較容易被人們接受;后一解釋比較困難,因為無論解釋者如何費盡心機,那也是對儒家倫理的一種現代求解,因此與傳統的關系究竟有多大,本身就是一個需要闡明的問題,而且因為必然遭遇現代處境中價值的諸神之爭參見任劍濤:《拜謁諸神:現代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導論”第118頁。,即便是最溫和的解釋也難以被人接受。如果限于立場申述儒家的現代價值,恐怕就既無以保證儒家傳統倫理的可靠解釋,也無以幫助人們基于現代需要尋求儒家傳統倫理的現代啟迪。毋庸諱言,對這兩者的混淆,是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常見的“理性狡計”,因為這樣可以為解釋者提供解釋的極大便利,從而占盡通吃傳統與現代的便利。
其次,如果面對中國現代國家與道德建設局面,嘗試以儒家理念作為解決兩大問題的思路,勢必要將儒家學說完備化,而完備化的儒學(comprehensive Confucianism),是一種古代結構參見任劍濤:《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導論”第813頁。。換言之,儒學的古代結構是與國家權力直接勾連的古代意識形態,它是一種試圖全方位解釋古代社會政治問題的思想體系,既為所有個體提供知行指引,也為整個社會提供秩序設計,還為國家權力提供正當性與合法性支持。在前者,儒學傳統對私德論之頗詳,恰如陳來教授枚舉的諸個人德行,如個人品格方面的四德、九德、三德,基本人倫關系方面的五教、七教、八政、十倫、四道、五達道、三行、六行,以及兩者結合意義上的德行如六德、三達德、四德、九德、九行、九守為免冗雜,這里不具引每一系統中的具體道德節目,具體的臚列可參見陳來:《中國古代德行論的分類與分析》,《儒家美德論》,第81100頁。,均屬此類。儒家之所以提供了如此完備的道德學說與實踐體系,是因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被接受為國策后,先秦諸子的思想都被儒家化為統一的古代意識形態。因此,三綱八目的完備性理念,才有了與國家運行高度契合的政治機遇:“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政治與教化統合于至善境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才將內外、人己、國家與天下整合為漸次遞進的完備體系。這在私權與公權難以分立、私德與公德內在嵌合的帝制時代,令儒家的私人倫理與社會政治德行高度整合起來,兩者成為儒家完備性學說相得益彰的構成面。家國天下的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結構由此凸顯。但在現代的處境中,這樣的完備結構不可能存續下來,因為家庭與家庭式關系直接擴展為國家公權的通路不再通暢,國家公權必須以社會契約與政府契約的形式建構起來。國家公權不再能夠以家長權威性地對待子輩那樣對待公民。這正是約翰·洛克闡述憲制政府的立約起點,也正是現代政治致力于限制國家權力以保證公民權利的基本安排洛克指出,“我認為官長對于臣民的權力,同父親對于兒女的權力、主人對于仆役的權力、丈夫對于妻子的權力和貴族對于奴隸的權力,是可以有所區別的。由于這些不同的權力有時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如果我們在這些不同的關系下對他考究的話,這就可以幫助我們分清這些權力彼此之間的區別,說明一國的統治者、一家的父親和一船的船長之間的不同。”見氏著《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頁。。任何試圖重光公私倫理直接貫通為一,且盡力讓私德修為發揮公德效用的嘗試,都是一種無視古今之變、悖逆現代定勢的懷古與虛擬。
再次,現代道德有自己的生成機制,因此也就有自己的延續、改善與矯正機制。如果一定要采取以古代方案矯正現代方案的進路,那么就必須論證清楚古代方案全面優于現代方案,這就與古代方案逐漸發展到現代方案的歷史進程相左,而這一進程無論如何是不可逆的了。同時,如果試圖以古代道德建設方案矯正現代道德建設方案,勢必全面終止或部分阻止現代道德按照自身邏輯演進,轉而讓其進入古代方案偏好者的主觀意愿的軌道,以期成為一個更令古代道德方案偏好者滿意的現代發展樣式。先不說這樣的扭轉是否可能,僅就希圖者的意愿來講,其大時代的錯位之思也讓人頗有些風馬牛之感。如前所述,古代的德行系統是與古代社會相宜的,脫離開古代社會而被抽離出來的德行理念與行動方略,乃是一種現代的東西,是闡釋者基于現代認知的古代投射。因此,它已經是一種假借古代之名的現代理解。在此,古代的德行理念與實踐僅僅是闡釋者針對當下診治流弊的思想資源,而不是古代理念與行為者的原初意欲。正如前引梁啟超指出的那樣,公德的構成性特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道德之外形,則隨其群之進步以為比例差,群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為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為道德者亦自不同”梁啟超:《新民說》,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第541頁。。如果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存在論德性直接作為應對隨社會變遷而變化著的認識論德性,那就肯定無法理解并開出應對道德建設缺失的有效藥方。
三、“推”己如何“及”人?
陳來教授切中肯綮地指出了儒家倫理中公私德行的高度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具有兩種可能的聯系途徑,一是公私德行統納于私德修為之中,由私德貫通德性的公私端口,從而一并解決德性的私人修為與德行的社會政治建構。這是一種以私德貫通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私德與公德的古代社會進路。二是合理分流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公德與私德,將其視為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與德行系統,但在社會的總體結構中,以社會成員的相互性建制即公共建制和公共道德作為觀察道德狀況的窗口。這是一種不否認私德作用而以公德回觀私德的進路。不過,這已經是一種基于現代性的論斷了。
在陳來教授關于中國近代以來公私德行偏向與流弊的論述框架中,上述兩種關聯方式是同時出現的。這是一種跨越傳統與現代邊界來理解公私德行問題所可采取的便利性進路,但在較為嚴格的理解中,兩種關聯方式必須加以甄別,才會對以私德或個人道德糾偏只重公德的流弊發揮幫助作用。首先,需要指出,以私德貫通公德的古代理解與公私德行分流而為的理解不可通約。在儒家的傳統理解中,三綱八目的德性是一個漸次遞進、一以貫之的系統,無所謂公私領域之分,因此也就無所謂公私德行之別。按照現代公私領域及其相宜的公私德行劃分來理解,三綱八目的儒家倫理體系,從修身回溯格致誠正,都是私德功夫;從修身進至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公德導向。基于這樣的理解框架,可以說取前一理解視角,根本就取消了儒家究竟是偏重私德,還是傾向公德言述的問題;即便取后一理解視角,儒家怎樣實現由私德向公德領域的穿透或突破,需要滿足實現這一突破的內外部條件。
在儒家傳統倫理體系中,三綱八目作為德性擴展的總體綱要,展現了一個統納公私領域與公私德行的宏大結構,但畢竟個體的修身功夫,要進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他者共鳴狀態,需要處理一個從我之身修,演進到他人感應或共振的境地,這就不是一個身修的個體單方面所可能處理的問題。于是,社會關系與政治互動的命題就浮現出來了。這是一種具有公共性特征的關系,其成功完成從身修的個體轉換為家庭成員的呼應、治國過程的呈現與普天之下的同氣共求的連貫進程,需要身修的個體勢不可擋地擴展到家庭呼應、國家統治與天下太平。這幾類道德節目得以遞進的關鍵,就是實現“推己及人”。推己及人的難題不在于擬往外推的德化個人的動機,而在于如何保證外推的德性不致失真,而且真正獲得被推的一方或互推的雙方與多方的積極呼應,進而達成德性的共振,并因此晉入更為高階的德性境界。其中,身修的個體可控的只是自己的道德修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后三個進階,都需要或主動或被動響應德性感召的對方在德性上的感同身受、堅韌踐履,以便實現身修的個體之間圍繞家庭、國家和天下三種由小及大的結構浮現廣泛而內在的呼應。這對身修的個體來講,勢必具有不可控的特性,這讓儒家陷入了一個踐行倫理道德的困境之中:儒家為了貫通個體、家庭、國家與天下的德行,要么必須凸顯一個超卓的偉大道德個體,以求打通諸種德行,貫通身家國天下,要么提請個體盡心、知性、知天,但這可能就無法打通身家國天下,從而滯留在個體的道德修為范圍之內。在前者,一切仰仗最高權力人物的有力牽引;在后者,一切依賴于道德楷模的完美垂范。但這兩種人不常有,德行實踐則常在。于是,牽引與垂范的缺口很難補足。
對儒家來講,必須走上的德行論述進路是前者。因為儒家設定了三綱八目的德行遞進目標,那就必須實現身家國天下德行的貫通進路。因為這一設定,德行的個體修為就不是獨善其身的道德修養與德行踐履事務,而必定是超出個體德行修為的社會與政治事務。由于中國古代社會是家庭家族宗族的關聯結構,因此身修的個體可以在血緣性社會結構中擴展。但倫理規則的這種擴展,不過是私德的范圍擴大,而不是社會公德的另起爐灶。至于治國與平天下,有一個掌握國家權力、以權力推行儒家道德的制度前提。于是,身修的個體就必須是既有高尚的倫理修為,又有國家重器在手,還有惠及天下的博大情懷才行。這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可想象的事情,當然就更不是他們所可以實現的道德修為目標。從社會政治機制角度看,只有掌握了國家重器的道德楷模才有希望登達治國、平天下的次高與最高道德境界。這對掌握國家重器的人來講,也是一個難于企及的偉大目標。因此,從身修的私德進至治國、平天下的公德,便依賴于能夠從私德自美進至公德共美的罕見偉人。將之付諸政治史事實檢索,正劇不多,悲劇不少。
儒家創始人自己也意識到這種外推非為一般人設計,而是為超凡脫俗的魅力型領袖專設。孟子的仁心仁政論述,即呈現出這樣的特質。在人心的定位上,孟子以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確立人心之善的本質特征,并在人禽之辨的視角規定了此心是為區分人類與禽獸的基準“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體現了孟子的人性本善論特質。這在見孺子入于井、見嫂溺于井的例證中得到呈現。,但即便是劃分人禽界限的本然善心,在人與人之間也具有實踐上的重大差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人禽之辨的善性標準是確定不移的,但庶民將之丟棄,君子將之保存,唯有舜那樣的“圣君”才能依照這樣的道德感知事物、治國理政。可見,從私德修為邁入公德實踐,是有道德境界與實施權力的限制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人皆有善心,這是對人人皆可承載善性、實施善行的一般承諾,但施之于政,則只有掌握國家重器的君王才能擔負——君政時代是與民同樂、與民共苦的堯、舜、禹承載,帝制時代則由帝王一力承擔。可見,一旦由私入“公”,權力就成為八目從齊家向治國平天下繼續推進的杠桿。這就與非權力人物的道德修為關系不大,甚至全無關系了。由此將個體道德修為與公共道德徹底分流為掌權者與一般人實現不同目標的兩類。如果僅僅著眼于形式上的陳述,人們會將三綱八目作為普適道德對待;如果加入從一己外推到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條件,三綱八目的道德普遍主義就變成針對具有平治天下的掌握國之重器者的特殊倫理。也許這正是《大學》僅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并不強調之后的道德節目同樣具有普適性的原因。
按照現代倫理回溯性地理解,個體德性修為臻于善的境界,屬于私德范疇;而推己及人,則屬于社會政治公德范疇。孔子主張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孟子所謂仁心仁政之推,都遵循的是這一邏輯。至于這樣的外推過程,在孔子那里是消極性表述,在孟子那里則是積極性表述了,而積極推展的展開情形,也被明確闡釋:“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于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于饑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餧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傅玄:《仁論》,《傅子》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7頁。在這里,推的進路、方式與結果,都呈現而出:自己所不欲的不外推,自己所欲的必外推;父子、夫妻、饑寒的自我體認,一旦外推他人并廣及天下,則國家天下之治可運于掌。尤其是這些都屬于“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也就是屬于常識倫理、日常行為,因此一己的善心及其外推,就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公共”道德得以建構并施行的保證。其間,從個體修身到天下太平的外推事務,似乎都可以依靠一己善心得到落實而不會遭遇任何障礙。這中間似乎不存在一個私人領域、私人道德與公共領域、公共道德的劃分問題,當然在兩者之間也就不存在什么跨越障礙。
這樣推己及人的邏輯,在中國古代可能不會遭遇什么挑戰。因為在君政時代,君王確實身體力行,將仁心推向仁政,博施濟眾,老安少懷;在帝制時代,由于天下歸于一姓,“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黃宗羲:《原君》,《黃宗羲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頁。,因此,公私直接合一于帝王之私,皇帝的私德也就順勢成為政治體成員必須謹守的“公共”德行。君政時代公權公用與帝制時代的公權私用,前者以公統合公私,后者以私統納公私,都是以公私的其中一端“吃掉”另一端,不過前者盡顯利益上的公而忘私之崇高、道德上的私德修為進至天下楷模;后者盡顯利益上的私利歸趨特性、私德上的權力垂范特質。就傳統之為傳統而言,這是一個事實指認,不必要對君政時代極盡推崇,也不必要對帝制時代極盡貶抑。因為現代人所持的分立公私德行的姿態,大都是由于他們不能有效處理公域私域、公權私權、公德私德之間的張力所致。只要承認古今之變這個存在論處境,那么就不必去苛刻地要求古人為現代人提供一個處理好公私問題的現成方案。
在現代視野中,如果嘗試堅持古代儒家“推己及人”的施展功夫,就不能不看到,其推展是很難在打通個體、社會與政治三大領域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為現代社會形成了高度分化的社會機制,現代政治造就了分權制衡的體制,私域與公域不再簡單直通,私權公權不再直接相連,私德公德不再合于私人。因此,試圖以私德或個人道德為公德或社會政治德行奠定可靠基礎,便必然遭遇此路不通的尷尬。就此而言,梁啟超認為私德與公德的關系,關鍵在于一推,便是對現代理解不確的表現。而馬君武的論述,也就是現代德行體系中,私德也是獨立自主、具有權利意識的個體的道德,其引導的社會公德便是以此奠基,而無其他解釋的可能馬君武對傳統私德與現代私德的區分具有明確的現代意識:“若徒指束身寡過、存心養性、戒慎恐懼諸小節為私德完全之證,是乃奴隸國之所謂私德,非自由國之所謂私德也。”馬君武:《論公德》,曾德珪選編:《馬君武文選》,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90頁。。梁啟超試圖以“推”來解決現代公私德行的貫通問題,從而以私德修為解決公德建設,在倫理思維方式上持守的還是傳統儒家進路。而馬君武認定中國傳統道德之私德,顯非現代具有獨立不易價值的個人之道德,因此極而言之,這樣的私德根本無從推出現代公德。這是一種脫離了儒家傳統倫理思維的現代倫理理念。可見,就私德與公德關系而言,由梁啟超申述的“推出論”與馬君武提示的“推不出論”,勢必成為關于中國私德與公德關系現代建構的兩種迥然不同的進路。
更為關鍵的是,在較為嚴格的現代背景中,古代的私德不能被簡單地定位為現代的個人道德,更不能被理解為涉及他人時就成為了社會公德,甚至是政治公德。因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私德,在倫理學或道德哲學意義上,基本上是限于個人一己所能決斷范圍的主體德行,他具有惻隱之心,在私德修為上,上能達到養出“浩然之氣”的境界,下能防止賊心浮現、識別來賊、抓住來賊“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五《大學二》,第301頁);政治上能夠“說大人而藐之”“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后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盡心下》),社會上能夠以君子之風影響小人德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這是一種以私德貫通個體、社會與政治世界的古代系統。而在現代國家中,個人道德之面向家庭與家庭式的隱蔽世界時,才能稱為私德;個人道德在面向他人、社會時,就不再是私德,而是公德了。前者以私密性為標志,后者以公開性為特征。因此,在一個曝露于眾的社會政治世界中,個人道德、社會道德和政治道德,圍繞其分別依托的社會之個體空間、人與人相互交往的社會空間、人與國家權力互動的政治空間,就是分別呈現出來的德行體系。其間,不存在忽視個人道德的社會政治德行,因為三者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一個殘缺的道德結構。在合一結構中,甚至馬君武認定的私德構成公德基礎的說法也不能成立。因為它們三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塑造的關系,馬君武認識到了沒有自由權利的私德之為奴隸道德,但沒有意識到自由私德的形成不是先于自由公德的,它并不構成現代公德的前置基礎。除非在一個自由社會與立憲政制體系中,自由私德才能浮現,而自由的社會政治德行也才能相應塑就。或許這使陳來教授有理由批評馬君武抽離出中國古代社會的私德并將之定位為奴隸道德的看法。
現代社會一方面將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劃定為界限確定不移的兩個領域,就此將私德限定在私隱的作用范圍內,因此公德便廣泛地呈現于社會政治這樣的公共領域之中。其中,既有作為社會政治單個成員的個人道德,也有作為社會中的一員的社會公德,當然更有作為政治社會及國家成員在掌權或不掌權時都需要堅守的公共權力道德。這里不存在誰更為根本,誰推導出誰的問題。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的公域與私域又處在互動狀態,公共權力的責任就是保護私域不受侵害,尤其是不受國家權力的侵害;而公民的社會政治參與,又使公民在私域之外盯住公域,審查公共權力人物是否忠于政治受托責任,會否忠心耿耿地履行公德。因此,人們一般著意區分的社會公德與政治公德,前者主要訴諸社會個體成員各自的自主、自治與自律,相互的友愛成為維持社會公德的良性氛圍;后者則主要指向掌握或有意掌握國家權力的公共人物,這些人物的私德水平怎么樣,都不影響人們對他們剛性的公共德行要求。在此,他律成為維護政治公德的決定性手段。在現代條件下,以為私德好,就必然公德好,或者公德好就必然私德正,都是一種似是而非之論,是一種忽視現代社會特質的含混主張。如果試圖強行將私德塞進公德體系中,并視之為公德水平高低的基礎性條件,那么就只能從現代社會回流到傳統社會,回流到儒家設定的君政時代的理想德性結構之中,才有可能。
其實,陳來教授雖然對梁啟超關于公私德行的論述作了富有啟發的分析,但他卻不知不覺中與梁氏共享同一個論述方法:那就是將良好的私德與值得期待的公德直接掛起鉤來,似乎善人之德直接就會呈現為公民德行。這是一種由私德直接通向公德的進路,是一種沿循由私德推導出公德的儒家傳統道德遞進邏輯的進路。因此兩人實際上都會不由自主地重視由私德推出公德的結果,輕視從私德推出公德的復雜條件。在現代國家,無論是就個人道德,還是社會公德,抑或是就政治公德來講,如前所述,不存在一個由誰推出誰的問題。三者的基本關系可以理解為:各自存在、相互影響,邊界清晰、功能有別,缺一不可、互相激發。這就必然會拒斥任何形式的推出思路:從私德推出公德固不可能,從公權的公德意愿推出社會德行與個人德行更不可期,即便以社會公德來善意連接個人道德與公權道德,也不可能落實。自由個體具有自主、自尊、自愛的德性,是平等社會和公正制度必然促成的主流德性;社會成員之間的友善、互愛和守則,是相互承認的成員間必有的公共德行;政治機制中握權者與公眾對權力的慎重以待、公權公用、謹守法治,是國家建構時刻的剛性約定。現代社會不會出現皇權專制時代以一姓之私冒天下大公的悖謬,也不會出現君政時代以絕對的克己奉公來苛求政治人物的過高要求。
17、18世紀出現的超越服從、凸顯自治決定性作用的道德體系,確立了這種讓個人、社會與政治不同德行各自發揮作用的健全機制。這不僅對西方國家是一個重大突破,對人類社會的道德建設亦是一個重大突破。自治的意味是:“我們所有人都同樣有能力明白,對我們自己來說,道德需求些什么;并且,原則上,我們都同樣有能力促使我們自己作出相應的行為,而對他人的獎勵或懲罰不予理會。”J.B.施尼溫德:《自律的發明:近代道德哲學史》,張志平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4頁。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力推動了一個現代社會道德體系的成立:“作為自治的道德概念為社會空間提供了一個概念性框架;在其中,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在沒有國家、教會、鄰居以及那些認為他們比我們更好、更理智的人的干涉下,自主地行動。而舊的、作為服從的道德概念卻缺少這些含義。因此,作為自治的道德概念從中生發出來的早期的近代道德哲學,為在個人和社會之間建立恰當關系……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J.B.施尼溫德:《自律的發明:近代道德哲學史》,第5頁。可見,自治個人是典型的現代產物。在傳統社會中,并不存在具有自治意義的個人,當然也就不存在與這樣的個人相伴的個人道德。一旦在現代社會背景中討論個人道德,也就必須首先承認這樣的個人主體是如何挺立起來的。循此可知,推己及人的“推”也就沒有存在理由了。否則,就會預設先知先覺的道德個體對后知后覺的道德個體的居高臨下、權威支配和道德優勢,而這就與現代道德精神完全背離了。
四、公德何以優先
陳來教授對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偏向及其流弊的批評,是在一個更大的思路中得到表述的:他實際上是在藉批評中國近代道德的偏失,全面批評現代道德的缺失。這從他論及梁啟超主張的公私德行觀念時,所指出的那是受到現代道德推手的影響而致觀點上可以得到印證。他明確指出,梁啟超所闡發的社會倫理之為個人對一群之倫理的觀念,所伸張的現代社會個人之間交往的頻繁催生群性道德,群性道德不得不設定“傷害原則”以呈現人際倫理的觀點,“這樣的說法與密爾論自由的思想完全一致,必然是受密爾《論自由》一書思想的影響所致”陳來:《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沿循其中西比較的思路,我們有必要重視陳來教授在描述分析中國近代道德偏失時,對西方現代道德哲學論及個人道德、社會公德與政治公德思想的先導性縷述與分析。他從西方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第一個系統闡發者亞里士多德開始相關學理敘述。對亞氏,他著重論及“好人”與“好公民”的德性差異。亞氏指出,好公民的品德是針對他所在的政治體系的,而好人(善人)的品德則是針對一個人作為人的普遍品德而言的,“好公民不必統歸于一種至善的品德,但善人卻是統歸于一種至善的品德的。于是,很明顯,作為一個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備一個善人所應有的品德”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21頁。。好公民的品德是要求城邦所有公民都具備的品德,而好人(善人)的品德則是對統治者品德的要求。在現實的城邦生活中,好公民與好人的品德差異明顯;在理想的城邦中,好公民與好人趨近一致。陳來教授對此指出:“亞里士多德對公民道德與善人品德的區分,以及他的觀點,對近代以來公德和私德的討論,對現代社會偏重公民品德,忽視善人品德,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忽略善人品德,只注重公民道德,正是現代社會道德危機的根本原因。”陳來:《西方道德概念史的自我與社會》,《儒家美德論》,第7頁。這一評論可以說呈現出了陳來教授論述西方道德,進而論及受現代西方影響的中國近代以來的道德,乃至于整個現代道德所具有的缺失的基本立場。
在點出亞里士多德觀點在西方所具有的長遠影響之后,陳來教授分別討論了休謨“對他人”和“對自己”的道德區分,康德對“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的區分,但著墨較多的是西方現代倫理思想的主流代表人物邊沁與密爾的相關論述。他特別點出了邊沁對“私人倫理”概念的明確表述,那是一種旨在指導個人自身行動的藝術,是一種自理藝術。只有立法藝術才屬意于共同體的幸福。后者與公德庶幾可近。陳來教授附帶指出,亞里士多德與邊沁為近代東亞社會的公德私德討論提供了概念基礎,不過“這一‘對自己對他人的框架并不能成為私德公德區分的合理基礎”陳來:《西方道德概念史的自我與社會》,《儒家美德論》,第14頁。,因為人的實際德行表現,有時候無法在公私德行上明確歸類,在公與私的邊際上,存在無法歸類的模糊或相交的德性形式。他繼續分析密爾的“個人道德”與“社會道德”。密爾區分了個人在僅僅涉及本人時的最高主宰地位,他只需要在涉及他人時對社會負責。個人固然具有一己范圍內自把自為的權利,但如果因此便顯得魯莽、剛愎、自高自大、自我放縱、耽于獸性享樂,他也會被人冷落和厭惡。不過,即便如此,社會與法律不能對他施加懲罰。
在這里,密爾確立的群己權界之傷害原則就凸現出來:“每人既然事實上都生活在社會中,每人對于其余的人也就必得遵守某種行為準繩,這是必不可少的。這種行為,首先是彼此互不損害利益,彼此互不損害或在法律明文中或在默喻中應當認作權利的某些相當確定的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于遭受損害和妨礙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中擔負他自己的一份(要在一種公正原則下規定出來)。這些條件,若有人力圖規避不肯做到,社會是有理由以一切代價去實行強制的。社會所可做的事還遠不止于此。個人有些行動會有害于他人,或對他人的福利缺乏應有的考慮,可是又不到違犯其任何既得權利的程度。這時,犯者便應當受到輿論的懲罰,雖然不會受到法律的懲罰。總之,一個人的行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響到他人的利益的時候,社會對它就有了裁判權……但是當一個人的行為并不影響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每人應當享有實行行動而承當后果的法律上的和社會上的完全自由。”約翰·密爾:《論自由》,許寶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8990頁。密爾對“群己權界”的劃分是非常清楚明白的,這是對現代社會公德、政治公德與個人道德邊界的明確陳述。其中,以他律(社會輿論與法律制裁)作為公德維系的動力,以避免傷害他人作為私德的自律導向。不過,陳來教授認為密爾的區分并不足以解決公德私德劃分所遺漏的他人道德問題。他認為儒家,尤其是孔子建構的私人他人公共的三聯序列,比公德私德的兩分法更為周全。因此這種影響了中日兩國的公德私德二分法,就無法有效指引人們處理倫理與道德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而且容易把他人道德與公共道德混為一談參見陳來《西方道德概念史的自我與社會》一文對密爾觀點的評論(《儒學美德論》,第1819頁)。。
由上可見,陳來教授對西方道德哲學政治哲學論及公私德行的思想家的述評,旨在強調相關論述在區別公德與私德的基點上,表現出了明顯的二元思維的缺陷,對中間狀態的他人道德缺乏關注,僅將“對自己”和“對社會”作為區分公德與私德的依據,乃是一種不周延的論述。而受之影響的中國近代公德私德觀,相應也就存在這樣的缺陷不說,而且丟失了儒家傳統中最周延的德行論述。他由此提示人們,儒家論及公私德行的三分法,比之于西方的二分法更為周全,完全能夠彌補現代道德建構的公私德行觀表現出的基本缺陷,“公德私德的區分雖然有一定意義,但如果把公德私德作為全部道德的基本劃分,則會遺失一大部分基本道德,證明這種公德私德劃分法的重大局限”陳來:《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他的這一結論,不僅著意向人們強調現代公私德行劃分的理論缺陷,更為在意的是提醒人們,儒家倫理是一種較現代西方相關論述更為周全的論說。因為儒家論述在公私德行的邊際上,指出了非私德、非公德歸類的邊際道德類型,從而既保障了道德類型論說的豐富性,也保有了人生實踐上的周詳性。
在上述斷言的基礎上,陳來教授推出了三個似乎具有連貫關系的結論:一是在道德哲學上的公私德行劃分,由于將人類豐富的道德生活干癟化,將公私德行相互嵌合的德行硬生生地塞進公德與私德的論述模子中,因而事實上無法有效引導健全的人生。他倡導以人格修養論或人生哲學取而代之。二是近代中國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導致人們普遍重視的其實是政治公民道德,而不重社會公德,也就是不重處理社會領域中人際倫理的道德,這讓二者嚴重失衡。因此,發展社會公德的緊要性超過倡導政治公德的側重性。三是中國道德建設的焦點既然是社會公德,而社會公德的奠基性德性由個人倫理供給,因此具有極為豐富的人生實踐論述的儒家傳統倫理,就成為善處非公德的“對人”,以及非私德的“對己”關系的觀念與行為指南參見陳來:《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第一節,《文史哲》2020年第1期。。這是一種相較于現代道德哲學的公德私德劃分更為健全的人生哲學智慧。至于梁啟超念茲在茲的中國所缺的公德,在陳來教授看來,那屬于不是問題的問題,“至于梁啟超所說的近代公德在我國闕如,這是事實,因為社會發展在當時尚未進至近代社會故”參見陳來:《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第一節,《文史哲》2020年第1期。。這一斷定的潛含結論是,一旦中國進入近代社會,近代公德就自然而然地具備了。歸納起來講,陳來教授討論公私德行的論述宗旨,就是為中國儒家傳統張目,認為儒家具有超逾西方現代公私德行論述水準的人生哲學,其在理論上更為周延,在實踐上更為周全。因此,唯有儒家,能夠為現代補偏救弊。
為此,他借用李澤厚的命題“和諧高于正義”來申述的關于德性建構的主張,頗具有畫龍點睛的意義。因為這一論說有助于理解陳來教授為什么拒斥公德私德二元劃分的主張,所以有必要略加討論。陳來教授指出,李澤厚的這一命題是針對“權利高于善”而提出的,但李本人的倫理學體系對這一重要命題并未提供支持,“只有完全奠基于儒家倫理,這個口號才能找到其堅實基礎,彰顯其偉大作用”陳來:《理性支配感性 和諧高于正義》,《儒學美德論》,第251頁。。和諧作為宗教性道德,不是一般社會性道德所可范圍;和諧作為傳統型價值,不屬于現代性價值;和諧不是相對倫理,而是普遍的絕對道德價值;和諧是善本身,是人類社會的絕對價值。“和諧作為價值,是仁的表達和延伸,以仁為體,以和為用,從而和諧高于正義,歸根結底,是仁愛高于正義。”陳來:《理性支配感性 和諧高于正義》,《儒學美德論》,第251頁。從理論上講,仁愛之所以高于正義,是因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這可以說是一個存在論的理由;而在德性構成方面,仁包四德(自由、平等、公正、和諧),無所欠缺,圓融圓善。“‘仁有多種表現形式,在倫理上是博愛、慈惠、厚道、能恕,在感情上是惻隱、不忍、同情,在價值上是關懷、寬容、和諧、和平,萬物一體,在行為上是互助、共生、扶弱、愛護生命等。”陳來:《仁學本體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421頁。可見,包含萬有的仁愛,自然高于專注社會政治問題,并為之確立軸心的公正論說。
不過,這種將社會政治問題僅僅作為萬物構成的一個方面來對待的哲學立場,并不能順帶消解社會政治問題的獨立性價值、專門性探究與針對性求解。而且,在知識上講,一個包容萬有的存在是否就高于一個具體的存在,還是需要探究的問題。因為離開每一個具體的存在,這個包容萬有的存在就是一個虛化的存在。就此而言,如何在社會政治領域凸顯保證公正的價值體系、制度安排與基本程序,才是切實解決社會政治秩序供給的根本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取決于中國古代社會從君政走向帝制的急驟性,因此一直是處在傳統儒家視野之外的問題。對現代新儒家來講,認取科學與民主價值,就是適應帝制轉向民國之后的儒家價值補強需要。當下大陸新儒家嘗試以古代的包納萬有體系順帶處置社會政治問題,則是一種回避儒家面臨的現代挑戰,以高位的哲學本體論思考消解低位的社會政治難題。如果說在哲學本體論層次上,儒家可以表述“和諧高于正義”的理念,那么在社會政治論層次上,儒家就必須確立以正義實現和諧的理念。
為什么儒家必須確立社會政治致思的正義宗旨呢?簡單講,這是古今之變對儒家提出的無以規避的新問題。在社會政治世界,古典和諧,是個體與家庭、群體與國家同構的和諧。此種和諧,由家國同構主導(或呈現為君政時代的公而忘私形態,讓人們在政治理想上對之無限眷顧;或呈現為一家一姓皇權的以私為公形態,讓人們在形式上趨近公的符號而對之心懷向往),無需正義理念的引導。現代正義,是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個人與國家的公正相待。此種正義,不僅構成社會政治和諧的價值基礎,也構成社會政治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則,當然也就構成處置社會政治具體事務的結果導向。就中國古代社會講,無正義也可和諧;就人的現代處境講,無正義則無和諧。對前者,因為正義缺席,無所謂和諧高于正義,還是正義高于和諧的問題;就后者論,正義先于并高于和諧,無正義的和諧,勢必是權力強加的和諧。這不是一個倫理概念間的抽象推導所可以抹掉的問題。“正義是任何社會秩序中核心美德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我們如何分擔維持社會組織的負擔,以及如何分配從中獲得的收益。因為,沒有任何人應當由于他人的不公正對待而過得更糟,也沒有任何人應當從對他人的錯誤對待中得到好處。”哈里·布里豪斯:《正義》,林毅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頁。在這樣的正義理念引導下,一個立憲民主的政體,需要確認每一個成員自由權利的優先性,并確認羅爾斯所說的制度建構兩個正義原則:“第一個原則,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羅爾斯對正義兩原則有所謂首次表述與最后表述,為避論述冗雜,這里引用的是他的最后表述。見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37頁。這是一種對政治體所有成員公正相待且促其相互友愛的現代制度思路。如此,方能保證社會政治體的成員得到平等善待。這不是哲學本體論的談論可以消融的問題,也不是在問題的廣納型、包容性上可以消解的問題。如果說儒家的古典仁愛原則所具有的現代價值必須肯定,那么它在現代社會政治世界中,就必須與正義價值疊合,并“開出”一個相較于君政與帝制中國更加復雜可行的現代正義制度體系。如果以高于正義的和諧原則將正義的政治理念與制度設計一筆帶過,那么不僅實現不了正義,也達不成和諧。循此為儒家作出的辯護,也就失去了現代準星,變成無的放矢了。
從規范的意義上講,公德與私德是社會完整道德結構的兩個構成面,并不需要突出哪一個方面的絕頂重要性,其有效互動,是最為健康的道德機制。這讓陳來教授嚴厲批評公德偏向、致力吁求私德建設的主張,在學理上完全能夠成立。但是,對一個正在致力建構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的國度而言,所呈現出的公德建設的先導性與主導性地位,也需要因應群性變化加以確認。這正是前述梁啟超指出的一切道德都在于利群,但群的處境令公私德行的側重點必然有所不同。由于古代儒家處理的是家國同構時代的德行問題,因此在家國分立的現代建國處境中,需要確立與之相宜的德行理路。就現代轉型的基本道德處境而言,相對于私德而言,公德具有優先性。
公德何以是優先的呢?其一,就德行的自身結構來講,個人道德、社會道德與政治道德交錯而在,誰也不能取代誰,誰也不能包容誰。因此,在一個自由、公正的社會,一個立憲民主的政治體中,公民們友善相待、守望相扶,國家對公民秉行公正、公權公用、盡忠職守。據此,個人可以在其隱蔽的那個生活世界中自主強化人生修養、提升德行境界;在其公開的生活世界中自由交往、友好相處、融洽對待。倘若社會秩序供給短缺、國家立憲機制有缺,那么個人就無法獨善其身,也很難友好相處。這就是人們通常在轉型社會中看到個人為謀利不計手段,不同立場的個人之間相互敵視的導因。在此情形中,公德的優先性是可以承諾的。
其二,從現代社會與國家結構方面來看,依據社會契約論的解釋,人們之所以建構社會,就是因為需要杜絕“一切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或解決個人“完美無缺的自由狀態”下合作的不便,因此個人交出權力給一個人或機構行使,保留自己不可分割、不可轉讓、不可褫奪的權利,這些權利指向生命、財產與自由。這樣,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較為清晰地劃分開來。國家不能侵入公民的私權領域,公民具有監督國家行使公共權力的責任。因此,個人道德主要依賴于自主公民的自我治理,社會道德主要依賴于自治公民以及社會組織的相互維系,政治道德則主要依托于立憲制度的剛性規約。三種道德,各入其軌,相互促進,但并不為國家權力包辦,也不為社會組織給定,更不由思想家賜予。如果社會公眾人物與國家公權人物沒有展現預期中的道德水準,那么社會輿論與行政倫理法規就會予以軟性或剛性的懲罰。由于公共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主要呈現于公眾人物和權勢人物身上,至少說他們的呈現具有廣泛的社會關注度與公共影響力,因此人們會瞪大眼睛緊盯著這類人群,這便是相對于公德的結構優先性表現出來的公德評價的優先性。
其三,由于現代社會對分立開來的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界限必須尊重,因此,受法律和社會習見保護的私人領域,尤其是私隱領域,人們不會過度關注。在這個范圍內的私德,涉及的是個人一己之私,品行好壞,人們自有公論,但絕對不予干預,這是國家權力與社會公眾需要守持的行為界限。即便是曝露在公眾面前的私人領域,或者是謀利性的,或者是利他性的,或者是高尚化的個人德行決斷,都是自主個人及其相互交往范圍的事情,既不由社會施加,也不由國家強制。相對于人們緊盯住國家公權與社會公眾人物的公德表現來講,個人道德情形確實是呈現社會道德與政治道德狀態的一個指標,但卻不是國家與社會所可以隨己所愿塑造的東西,因此也就不成其為一個政治體道德關注的核心問題。這是從關注度的高低上凸顯的公德優先性。
當代中國正處在建構現代國家的關鍵時刻。所謂關鍵,基本含義有二:一是國家正處在由傳統治理模式向法治國家轉變的緊要關頭,二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處于一個建構的緊張階段。前者關系到國家現代結構的落實問題,后者關涉國家權力運用的方式與績效。基于這樣的國家處境,人們高度關注公德問題,就具有了深厚的現實支持理由。如果在現代國家建構的關鍵時刻,無視公德建設的優先性,轉而強調私德的決定性,那么不僅很難支持現代社會與國家的建構,而且無法走出家國同構情況下德行結構遭遇的兩種尷尬:一是君政時代由圣君展現出的公而忘私的過高道德理想,成為一個無法由社會普通成員實踐的虛懸道德模式;二是帝制時代由專權皇帝呈現的“天下之大公乃天下之至私”的踐踏公德現象,讓人們表面上對道德傾注極大熱情,但內心對道德報以一種冷漠和拒斥。這種情況下的個人道德,便成為一種個體精巧地擇定其社會行為、政治目標的軟工具與裝飾品。
在理論上講,公私德行的二分,是一種道德類型學的劃分;而公私德行的交錯存在,是一種事實描述。二者的論述旨趣,并不在同一個問題針對上。因此,后一種論述并不構成對前一論述的顛覆。同時,對儒家道德所作的公德與私德區分,也是一種撇開古今道德理念的根本差異性,著眼于兩者在形式上體現的一致性進行的劃分。因此,從古代倫理之為古代倫理,現代倫理之為現代倫理的實質規定性來講,所謂儒家公共道德,應當更為準確地命名為儒家的公共性道德關于公共與公共性兩個概念所具有的不同含義,可參見任劍濤:《公共的政治哲學》第二章第一節《公共與公共性》,第98113頁。。儒家將公私德行整合為一的古代倫理體系,其中也存在類似現代公共領域道德規則那樣的內容,但不能將之直接命名為公共道德。因為正如前述,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流、公共道德與私人道德的分化,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事件。在古代社會,即便是在古希臘羅馬社會,也沒有出現規范意義上的公私分化、公德與私德分立。西方國家也不是直接延續古希臘羅馬傳統就順暢地進入了現代天地。公私領域的分化、公德私德的分立,對西方也是一種現代突破。這對所有進入現代狀態的國家來說,都具有先導式的引領作用。而一切轉出古代社會政治結構,轉進現代社會政治體系的國家,也就需要慎重對待,慎言超越。作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生成并塑造的儒家倫理體系,廣博精深,其現代活力需依靠人們在現代實踐中激發,而不是在書齋中甄別。是否能夠促成中國的現代突破,恐怕是關系到儒家倫理生死存亡的決斷。
中國面臨古今之變,但卻一直被改換為中西之爭。這是中國解決現實難題不力,轉而導向書齋功夫的結果。就公德私德這個觀察窗口來看,與其重視倫理理解的中西之爭,不如看重倫理理解的古今之變,但近代以來,古今之變的重大主題幾乎被中西之爭的激揚情緒所遮蔽。不說是理性認知與情感認同直接沖突,即便是理論解釋與實踐決斷之間,也相隔千山萬水。為此,校正中國德行爭辯的現代坐標,可能比爭論儒家與西方德行論述水平究竟誰高誰低要來得更為緊要。
[責任編輯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