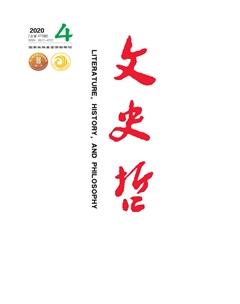觀念的轉變與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
韋森
摘 要: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是人類社會歷史上一場偉大的革命性的制度變革,已經孕育了過去4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過去40年的中國經濟改革是如何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現在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經濟運行體制?當下這種經濟體制的實質、優長和問題是什么?在現行經濟體制安排下的經濟高速增長能否持續?未來中國經濟與社會將向何處去?所有這些都是整個社會沒有深刻反思的問題。回顧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過程,無論是國有企業的改革、農業經營制度的變遷和民營經濟的成長,還是現代金融體系、現代政府宏觀管理體系、現代公司制度的生成與變遷,抑或對外開放在中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生成與發展中的作用,無不一再證明,在經濟改革的試錯過程中不斷轉變觀念和提高理論認識,才是經濟改革的原動力;建立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秩序,才是未來中國當走的路。
關鍵詞:觀念體系;制度變遷;經濟改革:對外開放;農業改革;國企改革;民營經濟;金融體系
一、引 言
庚子年春節期間,新型冠狀病毒正在肆虐中華大地,并向世界部分地區蔓延。時下,全國上下都投入到對這場新型冠狀病毒的阻擊戰之中。筆者相信,這場威脅與危害國人的生命健康、經濟發展乃至財產安全和家庭幸福的病毒惡魔終將被制服,一個經歷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中國,終究會回到自己正常的軌道上來。封閉在紹興鄉下的書房中,案頭擺著兩本新近出版的著作:一本是吳敬璉先生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8年版);一本是筆者的同事和好友張軍教授的《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兩本著作,都是論說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史,也都包含著深刻的經濟學思想。一口氣讀下來,均感獲益良多。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經濟體相比,中國政府所掌控的資源占比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高,國有部門資產的總量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和經濟體都大,但是中國經濟的整體資源配置形式(包括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政府購買)已經市場化了。經濟的市場化改革,或者說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遷,已經帶來了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GDP總量已經從1978年的2119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36萬億美元;人均GDP也從1978年的222美元,提高到2018年的9769美元。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總量、進出口總量等都穩居世界第一。從人均GDP來看,中國也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過去四十年,經濟增長率之高、社會變遷之大、人民社會福利相對提高之快,乃至人們的思想觀念改變之巨,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前所未有。這一切都是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結果。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是如何一步步艱難地走過來的?對此,許多年輕人可能并不是很清楚,只是在享受著過去四十年市場化改革的成果。直接參與經濟改革進程、在理論和實際操作層面作出過諸多貢獻的吳敬璉先生,在2018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對這一過程作了全面的歷史的回顧,可謂是最權威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史的研究之前,吳敬璉老師還出版過《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0年),《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這里放在一起與張軍教授的著作一起閱讀并評論。另外,張軍教授也在2019年下半年出版了專著《深圳奇跡》,這篇書評里的許多材料也出自該書。。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張軍教授,則剛剛出版了新著《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從另一個層面對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和中國經濟學人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理論貢獻,作了歷史的回顧和理論的反思。正如張軍教授在這部著作的“修訂版前言”所說:“中國的改革經驗概括為已有經濟理論的實驗室,也被認為可以成功拓展現有經濟學理論的分析范圍,可對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對改革結果的觀察,而對那些為推動改革作出貢獻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沒有給予同等的關注。在改革經歷四十年后的今天,對于那些需要深入理解中國改革的讀者來說,這是一個缺憾。”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頁。
四十年,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只是一瞬間,但對于直接參與到這場偉大的改革過程的政府領導人、經濟學家、企業家和工人、農民來說,這個過程是如此漫長,如此驚心動魄,如此波瀾壯闊。改革開放四十年后的今天,許多領導和參與這場改革的領導人和經濟學家已經辭世,仍然在世的也都進入了耄耋之年。對于生活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各界人士來說,中國經濟改革艱難而輝煌的歷程,無論從何種角度來說都是必須予以了解的知識。了解中國經濟與社會如何從一個斯大林模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走到今天獨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歷程,對于認識當下中國的經濟制度,把握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方向,無疑是必要的。由是,筆者將吳敬璉教授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和張軍教授的《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視作為新近出版的關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歷程的兩部最為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筆者嘗試以書評的形式,評述吳敬璉教授和張軍教授的這兩部著作,同時也通過閱讀兩部著作給出的資料和理論,對當代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歷程予以系統回顧。二、在經濟改革的試錯過程中不斷轉變觀念和提高理論認識是改革的原動力在《通往奴役之路》這部20世紀的世界名著開篇,哈耶克就曾指出:“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vol. II) , ed. by Bruce Caldwell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2007).今天,我們也可以說,經過四十年的經濟改革所形成的中國當下的經濟體制,也是四十年來——尤其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來——政府領導人、經濟學家、社會各界人士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不斷轉變思想觀念、提高理論認識而進行資源配置方式的制度創新的結果。當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既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未來社會的設想,也非同于斯大林式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當然更非同于西方任何一國的市場經濟制度,而是一種獨特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今天稱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如每一位經濟學人在寫作的過程中實際上都會創生經濟學思想一樣,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參與者在不斷轉變觀念和提高理論認識的過程中試錯性地進行的。到今天,除了少數極其封閉的理論界人士之外,恐怕已經沒有人會懷疑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易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的經濟制度(相比于自然經濟——沒有多少勞動分工與市場交換的經濟形式,以及中央計劃經濟——以行政命令、資源調撥和配給制為主的經濟形式)。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很長一個時期,我們是把消滅市場交易、消滅貨幣、消滅私有制和達致一種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制度而作為長期發展目標的。正如1953年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制訂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中所指,“這條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經濟基礎”轉引自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43頁。。并且,毛澤東在1952年也提出了“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82頁。。20世紀50年代中國所進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1958年到1962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當時的領導人為力求實現上述整體社會發展目標所推動的現實經濟制度的變革。“文化大革命”期間,整個國家所實行的打擊投機倒把、消滅自留地乃至“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經濟政策,都是為了實現這種社會理想在社會經濟制度層面所作努力的一種延續。
在工商業基本消滅了私有企業和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制以后,中國特色的計劃經濟體制就形成了。計劃經濟體制之所以在短期內能夠迅速實現,吳敬璉教授總結了四條原因,其中兩條是:“(1)從意識形態看,仿效蘇聯的榜樣,廢除私有財產和市場制度,在國有的基礎上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協調為特征的計劃經濟,在很長時間中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天經地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蘇聯專家以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教育進行全面改造,成為唯一通行的經濟理論。按照這個理論,建立集中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4)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小農充斥的國家。‘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形成牢固的傳統。”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4546頁。吳敬璉教授認為這是中國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的政治基礎。
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1978年,按照《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55年)的教義所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帶給中國的是嚴重的經濟后果。且不說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大饑荒,奪去了上千萬人的性命,經歷了“四清運動”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發生的“四清運動”,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是介于“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之間的一場政治運動。這場運動的前期在農村主要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后期則是在城鄉“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運動的起因是,如何看待國內形勢,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特別是上層出現了意見分歧。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如何看待當時國內的困難形勢,二是如何看待農村的包產到戶。對于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困難和當時的經濟形勢,以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有了更加接近真實的看法,得出了“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毛澤東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當時的困難并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三面紅旗”(中國共產黨于1958年提出的一個施政口號,意指“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必須堅持。關于包產到戶問題,面對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安徽省委對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意見加以變通,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制,即“責任田”(這也為1978年后從小崗村到鳳陽縣和安徽省試行的土地承包經營的“大包干”改革提供了“前奏”),得到了毛澤東“可以實驗”的謹慎同意。同時,中央和地方許多黨政領導人都對包產到戶予以支持。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并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在“四清運動”中,毛澤東提出要“重新提起階級斗爭”和“反修防修”,并在后期明確提出在中國國內存在著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因此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四清運動實際上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曲。和“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8年,這種體制運行的結果是幾乎把中國經濟帶到了崩潰的邊緣。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到1978年,作為一個擁有9.6億人口(占當時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的大國,中國的GDP總量只有3678.7億元(按當時的匯率為2119億美元,還不到上海浦東新區GDP的一半),人均GDP只有381元(按當時的匯率為222美元)。在9.6億人口中,97.6%的中國人生活在聯合國規定的貧困線之下。實際上,正是在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吃不飽肚子且整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邊緣的情況下,殘酷的經濟現實才迫使我們開啟了經濟改革之路和對外開放的大門在2018年發表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2月號的一篇題為《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的文章中,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周雪光教授說:“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在面臨和應對危難的關頭,當權者才會被迫作出讓步;開明君主會審時度勢,啟動改革,以圖重振朝綱。但這些改革和變化多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變化。一旦渡過危機,得以休養喘息,上層則會收回讓步,重回窠臼。因此,歷史上改革起伏變動雖然時有出現,但制度性變革卻難以尋覓。”回顧中國四十年的改革歷程,可以發現,與過去的中國歷史不同,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朝著一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邁進的全面的制度變革。故時至今日,可能任何人也沒有能力把整個中國社會拉回到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去了。。
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這次全會不但開啟了“解放思想,事實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解放運動,而且明確宣布“把黨的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隨即終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對黨內黨外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等口號”,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執政路線的歷史性轉變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22頁。。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中國經濟學界和社會科學界探索未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的理論禁錮,隨即也開啟了經濟改革的歷程。但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極左”觀念體系下,中國經濟學的整體理論范式也還是沿襲著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框架,因而改革的初始思路之一是在保持計劃經濟體制整體不變的情況下,引進市場調節機制,并擴大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一大批老一輩經濟學家包括薛暮橋、孫冶方、馬洪、蔣一葦、董輔礽等,均在這一時期撰寫了大量文章和報告,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進行了論證。實際上,在1978年7月至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也曾明確提出要給予“各企業以必要的獨立地位,使它們能夠自動地而不是被動地執行經濟核算制度,提高綜合經濟效益”,從而,在理論界和當時的政府領導人大多數意見傾向一致的情況下,“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歷史起點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67頁;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294295頁。。但是,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上,囿于當時的思想禁錮,經濟學界還只能談論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到后來才逐漸提出要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經濟體制模式。比如,薛暮橋在1980年為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提出:“我國經濟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到1982年,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的國家領導人陳云,在與國家計委負責人座談時,還是把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體制模式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并主張在這種模式下,國有企業享有計劃允許范圍內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8年,第68、51頁。。
在黨政領導人與一些經濟學家關于改革方向的思想認識趨向一致的情況下,從1978年到1980年,首先從四川開始,進行了國有企業擴大經營自主權的試點,并在之后推向全國。到1980年6月,實行國有企業擴權的單位已經達到6600個,其“產值占全國預算內工業產值的60%,利潤占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的70%”,“1981年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工作,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要進一步,要在全國鋪開”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5355頁。。這說明,在那個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經濟學家乃至社會各界,并不完全清楚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最后會走向哪里,最后會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經濟運行體制。
但是,在經濟改革的初始階段,這種以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為主旨的改革被歷史實踐證明是失敗的:“在新體制下擁有某些自主權的企業不受市場競爭的約束,也不處在價格信息的引導之下,因此,企業增產增收‘積極性的發揮往往并不有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社會收益的增加,因而造成了總需求失控,財政赤字劇增和經濟秩序的混亂。”對此,張軍從經濟學理論高度分析道:“在國有企業的體制沒有變化的前提下,這個自下分權的改革必然造成國家與企業之間的‘激勵不兼容,這樣的放權讓利到最后可能葬送改革。類似的風險在蘇聯和東歐的局部改革時期(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西方經濟學家后來把這種單純地向地方政府和企業實行分權的改革做法叫做‘改革陷阱。”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7071頁;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03頁。
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失敗和暫停后,經濟領導部門和經濟學家之間隨即展開了一場關于改革大方向的新爭論。有一種意見主張中國經濟改革應當采取“計劃取向”而不是“市場取向”,進而主張轉變到完善計劃和嚴肅計劃紀律方向上去。并且,在1982年,主張“計劃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論家曾一度占據上風,以薛暮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遭到了批評和否定,隨即黨政機關發布的文件中均確認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方針。在這樣的氣氛下,中國的城市改革一時失去了方向,“實現企業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以及建立商品經濟體系的問題就很少有人提起了”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5760頁;《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6970頁。。這一時期的改革和理論爭論,充分證明了經濟學理論和思想觀念的沖突,也充分證明了哈耶克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Every social order rests on an ideology”(每一種社會制序都建立在一種觀念體系之上F.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I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54.)這一判斷。這一時期所進行的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改革的試行和失敗,充分說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一個迂回曲折且不斷試錯過程中進行的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七章。。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改革的不成功和保持計劃經濟取向的思想理論的回潮,并沒有阻止和中斷經濟改革的進程。已經啟動的市場化改革,并沒有按照這些主張回到計劃取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解放思想運動的背景下,經濟理論界和思想界繼續探討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隨之,各級和各地政府開始了新的市場化改革道路的實際探索和嘗試。在1981年初,山東省率先對國有企業實行了利潤(虧損)包干的經濟責任制。到1984年,國務院又批轉了財政部《關于在國營企業推行“利改稅”第二步改革的報告》,主張完全以稅代利,將企業上繳利潤全部改為上繳稅收。1987年,國家經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的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工作會議,要求全國所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在1988年年底之前全面實行廠長負責制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09頁。。國企改革并沒有完全止步于此,但從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到利改稅、承包經營負責制、廠長負責制的各種企業改革,并沒有改善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學界和實務部門開始探討現代企業制度,并隨即進行了大規模的國營企業“改制”——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民營化——這一今天看來不動聲色但實際上是驚天動地的改革舉措。與國企改革同時發生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是,在1993年11月14日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通過執政黨的綱領性文件,確定了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一決定一改之前“商品經濟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說法,而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14頁。。《決定》還明確指出:“就全國來說,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等方面。”“國家要為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216頁。《決定》的這一精神,實際上為民營經濟的成長和發展開了綠燈。
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所釋放的市場化改革的理論意見、指導方針和現實改革的政策導向,為民營經濟成長、發展和崛起創造了一個歷史性契機。1994年到1997年發生的國有企業(中小國有企業和虧損國有企業)的轉制,與民營經濟的迅速成長、發展和崛起,應該是同一個過程。1994年之后的這些改革舉措,實際上為中國經濟的迅速起飛,創造了制度條件。
《決定》對于中國經濟制度的這一新的解釋,以及民營經濟快速成長和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引起了一些支持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政治家、理論家的極大不滿。他們在19951997年間,先后寫了四份基本傾向一致、內容和側重點有所不同的長篇文章(俗稱‘萬言書),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強烈質疑。特別是在1997年初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為了進一步表達對改革開放方針的質疑,他們發表了‘第三份萬言書《關于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這份‘萬言書認為,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對‘公有制為主體的新闡釋‘相當普遍地被接受,‘是一個不幸的事實。同時,全面論證了自己的社會主義觀念,即‘社會主義把全民所有制(即國有制)作為公有制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這份“萬言書”還聲稱,“如果集政權與所有權于一身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保衛國有企業,就無異于在執行一種‘戈爾巴喬夫式的錯誤路線”轉引自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216217頁;《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186187頁。。
在蘇聯已經解體和東歐國家普遍轉制后,黨內外有些政治家和理論家仍然停留在“斯大林模式”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執政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認識水平和理論信念上。抵制經濟改革進程和反對市場經濟觀念的聲音,遭到了堅持市場化改革的經濟學家的反駁。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厲有為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班上的一次講話中就提出,要把全民所有制與國家所有制區別開來。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是一種理想化的、不切實際的占有形式。因為國有企業職工以外的人民群眾并沒有任何處置權和收益權;而國家所有制則是以統治階級的國家為代表的占有形態。國有制與其他形式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同時并存,互為條件、互相依存、公平競爭轉引自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187頁。。隨后,由吳敬璉、張軍擴、劉世錦等經濟學家組成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課題組也隨即撰文,對反對市場化改革的“萬言書”給予正面回應。他們指出,所謂“社會主義把國有制作為公有制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無非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征的舊調重彈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斯大林的親自指導下、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明確指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制在國民經濟的一切領域內都占絕對統治地位”。“公有制有兩種形式:(1)國家全民所有制;(2)合作社是集體農場所有制。”其中,“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占優勢的、起主導作用的所有制形式”。集體所有制是在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的情況下,作為一種權宜之計而保留下來的,當農業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集體所有制就應當逐步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國家所有制)過渡。受當時蘇聯的影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在1953年由毛澤東主持修訂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中就明確指出,“這條總路線的實質就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唯一的經濟基礎”。轉引自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183184頁。。這些觀點已成為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主要障礙”。他們主張,“十分有必要擺脫蘇聯模式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束縛,對社會主義作出更明確的定義,貫徹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不能把國家所有制看成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和社會主義必須追求的目標”引自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187189頁。。主張市場化改革的經濟學家的這些觀點和主張,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認可。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對這場爭論作出了明確的結論。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確定為經濟改革的基本目標。正是在這種理論互動中,全社會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不斷變革理論觀念,逐步確立起了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共同發展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之后,才有了21世紀以來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按照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截至2017年底,中國民營企業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目前民營經濟所創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60%。且65%的專利、75%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是由民營企業完成的。從吸納就業方面看,民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生力軍,是就業的主要承載主體。按照全國工商聯新近統計,在城鎮就業中,民營經濟占比超過了80%,而非公經濟(包括外資)企業對新增就業貢獻率超過了90%引自全國工商聯主席高云龍于2018年3月6日兩會期間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答記者問。詳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4177615597573760&wfr=spider&for=pc。。另外,在2018年GDP份額中,外資企業和私人農戶GDP占比應在16.9%左右,如果內資私營工商企業的比重在60%以上,那么私營部門的總比重應該在76.9%以上,剩余的23.1%才是國有部門創造的份額。這說明,民營經濟、私人農戶和外資企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而國有部門對GDP的貢獻,連四分之一都還不到(引自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2019年3月7日答記者問)據央視網2019年3月7日的一篇報道,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一次答記者會上曾透露,到目前為止,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城鎮勞動就業,還有90%的企業數量(也有資料表明現在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90%以上的新增就業),見http://news.cctv.com/2019/03/07/ARTIyYXtrtJ7SYQ6HapQbVsJ190307.shtml。。不僅如此,自1989年中國證券市場開始試行以來,大部分國有企業已經上市變成股份制企業,因此目前國有企業在性質上已經與原來的國有國營企業完全不同了,實際上變成了由國資委控股的上市公共企業(public corporation)。這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的實質。正是這種基本經濟制度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的逐步形成和發展,促成了過去四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市場化改革才是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年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盡管市場經濟才是被世界歷史尤其是當代世界各國經濟史所證明的、唯一能帶來經濟增長和人民福祉增加的資源配置方式;盡管2013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明確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區別于之前黨的文件中所說的“基礎性作用”),但實際上在今天的中國經濟學界以及理論界,對計劃體制抱有幻想者仍大有人在,或者說時至今日還有一些理論家實際上仍持有各種形式的中央計劃經濟優越的理論信念。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后,社會收入分配拉大,一些在市場化改革中收入沒有多少增加或相對增加比較少的人,仍然懷念計劃經濟時期大家都比較貧窮但收入相對平均的那種體制與格局。不僅在中國,在轉制后的俄羅斯也有一些人和階層仍持有這樣的信念。但是,就全社會而言,持計劃經濟優越這一觀念和信念的人已經很少了。社會觀念體系的這一轉變,正是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動因和動力。正如張軍所說:“中國的改革過程和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的形成無疑是中國在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遺產及政治條件的產物。不了解這個背景和初始條件,我們無法知道中國的改革為什么是漸進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為什么中國在改革中總是形成雙軌體制,并可以做到‘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正是這些制度遺產和政治條件使中國在改革方式和對改革方案的選擇上變得不那么激進。”“一旦我們把視野轉入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投入側而不是‘產出側,你就會發現中國改革的精彩之處在于改革如何從黨內的思想斗爭和政治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關鍵時候由政治領導人的智慧與眼光所推動;在于改革成為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過程;在于改革成為能讓更多人參與其中的社會過程;在于改革是一個基于局部經驗推廣和試錯法的社會實驗;更在于改革成為一個關于技術和制度的學習與擴散過程。”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12頁。張軍對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的這段評論和總結,不但精彩絕倫、全面深刻,而且道出了20世紀后半葉到21世紀之初,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史乃至當代世界歷史上這場偉大的經濟改革的實質。
三、中國經濟改革既是自發社會秩序的成長和擴展過程,也是整個社會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不斷轉變觀念的基礎上進行的制度創新按照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理論發現,人類有喜好交易與交換的天生稟賦,這種天賦稟性的發揮,會導致市場分工的自發演進和市場秩序的不斷擴展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76/1930)說:“盡管人類的智慧能預察到分工會產生富裕,并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但衍生出這么多益處的勞動分工,卻原本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它必定是不以這種廣大效用為目的的一種人類某種傾向(propensity)所非常緩慢和逐漸生成的結果,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以及相互交易。”“人類如果沒有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相互交易的性向(disposition),各個人都必須親自生產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必需物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務和工作全無分別,那么,工作不同所產生的才能的巨大差異,就不能存在了。”從充分利用人們在市場交易中的利己心這一認識出發,斯密就非常自然地從他的勞動分工理論推導出了他的“看不見的手”的著名原理:“由于人以此種方式經營產業的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像在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所引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人想要達到的目標。這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得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在任何文明社會中,市場交易總會自發產生其成長和不斷擴展的內在動力。事實上,早在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就提出了與斯密在18世紀、哈耶克在20世紀所提出的市場秩序自發運行和擴展的理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就明確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司馬遷幾乎表達了與斯密“看不見的手”的著名原理同樣的思想。更為可貴的是,司馬遷不僅闡明了市場自發運行和自發成長的基本原理,還明確告訴君主和政府,不要過多地干預市場運行,尤其是不要與民爭利。他說:人們出于本能在市場交易中自發追求自己的利益,要賺錢發財,“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司馬遷和亞當·斯密所講的這些道理,并不是中國古代社會遙遠的故事和18世紀英國的情形,而應該是人類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如果人們沒有追求財富的利己之心,沒有經過勞動和社會分工所導致的市場交易,沒有市場經濟的快速成長,哪里會有西方世界的興起?哪里會有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今天中國近百萬億元的GDP,工業化、城市化、高速公路、高鐵、現代化的機場、碼頭、地鐵、商業中心,以及平均每人幾十平方米的城市住房和人均超過1萬美元的GDP,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改革過程中市場經濟成長的結果。
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按照斯大林主義經濟模式的理論信念,我們一段時間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消滅私有制、消滅貨幣、消滅市場交易,轉而靠行政命令來組織人們生產和生活的理想社會。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進行的對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為逐步實現這一理想社會目標而推動的快速制度變革。單從農業生產制度來看,從1951年12月開始,中共中央頒布了一系列決議,規定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到1956年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三階段后基本完成,全國加入高級合作社的農戶已經達到96.3%。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接著,整個社會刮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共產風”1958年7月1日,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在北京大學慶祝建黨37周年大會的講演中,傳達了毛澤東的一段“最新指示”:“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商業)、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確認“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至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在這種快速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共產風”的勁吹下,到1958年9月,占全國98.2%的農戶被組織在26425個人民公社里,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里實現了以“公社制”為主的農業集體化變遷。1958年至1981年,“人民公社”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組織形式。20世紀5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還記得,在當時的2.6萬多個人民公社中,“每個公社有4500多農戶。公社下設生產大隊,作為管理生產、進行經濟核算的單位,盈虧由公社統一負責;在分配上,除實行固定工分制之外,還實行糧食供給制,不論每戶勞動力多少,都按照人口定量免費供給糧食,并以生產隊為單位,組織公共食堂,所有社員都必須在公共食堂領取飯食,嚴禁在家開火”。見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119頁。。當時所建立的人民公社,其特點是“一大二公”,即規模大(一般為兩千戶左右)、公有化程度高。權力過分集中,農戶和基層生產單位沒有自主權,生產中沒有責任制,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這種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了19591961年糧食供給嚴重困難的“三年大饑荒”,使整個國家和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吳敬璉先生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3章、《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3章和張軍教授的《改變中國》第1章,都詳細回顧了這一歷史過程。
從經濟學原理上來說,任何經濟制度和經濟組織均是要解決勞動及社會分工中的激勵與信息的應用問題。在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耕作的小農自然經濟中,以私人家庭農戶為主要生產單位顯然是最合宜的生產組織形式。這也就是吳敬璉先生所說:“農業是一個適合于家庭經營的生產部門。”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110頁。經濟學家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也認為:“農業因具有內部規模不顯著、勞動的監督和度量都極其困難的特點,而成為一個適宜家庭經營的產業。”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第123頁。即使到了機械化的現代社會,如果采取像斯大林時代那樣的集體農莊制,仍然不能解決農業生產的激勵(即所謂的“生產積極性”)問題,因而蘇聯的集體農莊和在中國運行近二十年的“人民公社”,均是一種無效率的農業生產制度形式。根據筆者1978年上大學前在魯西南的一個農村當生產隊長的現實觀察和思考,在1992年到1995年在悉尼大學所做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中,筆者就論證了在缺乏明確理想的沒有產權的社會聯合體中,無論采取“按勞分配”“按需分配”,還是采取二者的結合形式(如五五分成、三七開),這個生產者聯合體均沒有最優解。因為這種生產制度和組織形式必定是無效率和不可行的。筆者那篇文章的理論結論是:“在一個產權非個人化而又實行按勞分配的生產者聯合體中,每個成員向總勞動投入自己的個人勞動而占取自己的勞動報酬。個人的勞動投入量由兩個方面來決定:一是勞動時間;二是工作努力程度。然而,由于測度工作努力程度常常是很困難的,勞動時間往往成了度量每個成員的勞動投入量的唯一尺度。在此情況下,如果每個成員都沒有較高的社會覺悟(即不是自利的),他們會傾向于通過在工作時間內的偷懶來達到個人努力效用的最大化。這是生產者聯合體內部X負效率(Xinefficiencies)存在的主要原因。”“X負效率”這一概念為美國哈佛大學的萊賓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在20世紀70年代所提出。其基本涵義是,在給定資源和技術條件下,一個生產組織內部的實際生產效率和技術可行性最高效率之差(見Leibenstein,1976)。由此,筆者得出的結論是,依靠行政命令來組織生產和人們生活的經濟體制肯定是低效率和不可行的。并且,筆者還明確指出:“本文的抽象理論分析,既適用于行政控制國家改革前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包括前蘇聯的集體農莊Kolkhoz和中國農村改革前的生產隊),亦適用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以及以色列的基布茲(Kibbutz)生產者聯合體。”李維森:《產權非個人化條件下生產者聯合體成員的勞動投入行為》,《經濟科學》1999年第5期。應該說,筆者那篇文章的理論結論,與其說是出于純理論推理,毋寧說是基于筆者作為一個曾經的農村生產隊隊長的親身經歷和現實觀察而作出的理論反思。
事實上,在中國“大躍進”時期所建立的“人民公社制”是帶有很大空想成分且低效的一種制度實驗,是造成1959年之后中國三年大饑荒乃至改革開放之前經濟發展的災難性后果的根本原因。對此今天應該沒有人持懷疑態度了。但是,要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卻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盡管在1962年中共中央的決定對公社“一大二公”體制進行了調整,將生產小隊改為生產隊(同時將原來的生產隊改為生產大隊),并將其改為人民公社之下的基本核算單位,但20世紀60年代所實行的人民公社制的“三級核算、隊為基礎”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仍然是沒有效率的。按照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所提供的數據,張軍指出,“在19581965年間,中國農民的消費尚未達到1957年的水平,農民的收入在70年代幾乎陷入停滯狀態。整個70年代中國農民的糧食人均消費量只相當于20年前的水平,而食用油的消費量則一直低于50年代。農村的貧困十分嚴重。1977年,中國2100個縣當中有1/4的人均收入低于50元(人民幣)的貧困線水平”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435頁。。另外,按照吳敬璉先生的數據以及陳錫文的研究,在19571978年的21年間,農民年收入由73元增加到133.6元,平均每年只增加2.9元,扣除物價提高因素,實際純收入平均每年只增加1元;“到1978年還有約2.5億即全體農村居民的30.7%處于赤貧狀態”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121、123頁。。中國自1950年中期到1979年這二十多年間所推行的從“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制”的強制集體化經營的歷史,用鐵的事實證明,它們是違反經濟運行基本法則的、人為強制建構的、不可行的和低效率的經濟組織形式。因此,實際上從1957年起,在浙江溫州、安徽蕪湖和四川成都等地區,就有地方自發地實行了“包產到戶”的生產組織方式。1959年“大躍進”運動的高峰期,一些農村也出現了包產到戶的生產組織形式,但很快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壓制下去。19591961年,由于快速的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糧食減產和大饑荒,“一些地區的農民饑寒交迫,非正常死亡大量發生,農業集體經濟已經沒有力量維持社員的基本生存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安徽省曾經也是頭腦發熱的領導開始冷靜下來,采取了‘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辦法,希望通過這種辦法能恢復農業生產和維持農民的生計。到1961年3月,試行‘責任田的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已經占安徽農村生產隊總數的39.3%”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125頁。。但是,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中共安徽省委負責人支持農民搞責任田的做法。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和隨后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所謂的“復辟資本主義”的“單干風”和“翻案風”,提出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從而把基層政府組織和農民自發出現的第三次“包產到戶”硬生生地給扼殺了。
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粉碎“四人幫”、十年“文革”結束之后。從1977年開始,安徽各地(如肥西縣山南公社社員和鳳陽縣小崗村在整個社會或占支配地位的社會觀念體系沒有發生變革前,在任何社會中想要改變現存的制度安排的嘗試,都會冒一定的風險,甚至改革的當事人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正如吳敬璉先生和張軍教授的記述,盡管“包產到戶”是農民的一種“自發秩序”,但在當時的環境中,安徽小崗村的18戶農民是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參與者甚至都安排好了后事且簽字畫押才敢干的。幸好得到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并在后來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制才在全國推開。回過頭來看,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現在的這場中國經濟改革,是當代人類社會歷史尤其是中國社會歷史上最偉大的制度變遷,但每一步都是極其艱難和曲折的。參見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0年,第94頁;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943頁。)又開始自發地、偷偷地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生產組織形式了。但是,由于當時的領導人還是堅持“兩個凡是”,自然就不允許在全國范圍實行毛澤東生前所反對的“包產到戶”,以致到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仍然規定“不許分田單干”和“不許包產到戶”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7274頁;《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128129頁。。由于當時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想觀念仍然認為,只有人民公社的按勞分配制度才是社會主義的,分田單干則屬資本主義性質,因此,在安徽乃至全國所進行的分散經營方式,初時還是“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在當時還是私下里自發實行和擴展,只是借助于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支持,在安徽鳳陽縣和肥西縣才實行起來。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兩個凡是”的方針被否定,“但在各級黨政機關仍有不少人堅持反對‘包產到戶,認為這‘無異于背棄社會主義道路”這說明要在一段時期內轉變人們已經形成和信奉的思想觀念,是多么艱難,就連“文革”后期在魯西南農村做過短期的生產(小)隊長和大隊團支部副書記的筆者自己,當時也認為分田單干就是背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故自己大約在1981年在大學讀經濟學本科時,知道各地——包括自己家鄉的生產隊——都在進行“包產到戶”時,都感覺難以接受。另參見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129頁。。1980年,胡耀邦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支持包產到戶的萬里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到此時,主張農田承包制的意見在中央高層才占了上風。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中熱情贊揚在安徽肥西和鳳陽進行的“包產到戶”和“大包干”的實驗后,這一狀況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1980年9月5月《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下達后,各種形式的農業承包責任制在全國各地迅速擴展開來。直到1982年1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第一個“一號文件”出臺后,農業聯產承包的經營方式才獲得了最終的合法性。到1982年末,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已經占93%,其中大部分是“包干到戶”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129131頁;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7378頁;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4551頁。。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之后,原來的三級集體經濟組織已不存在上下級的行政隸屬關系,也不存在生產資料的占有由生產隊向生產大隊、再向公社逐級過渡的關系,在中國實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在198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之后又經歷四次修訂)和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后于2002年和2012年兩次修訂)后,形成了農村土地、農民的宅基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家庭承包經營這種獨特的農業經濟制度。這種由個人和農戶經營的家庭承包經營制,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的發展。中國的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30,477萬噸,增加到1984年的40,731萬噸(1990年達到44,624萬噸,2010年達到54,641萬噸),比1978年增長了33.6%,年平均增速為4.95%;棉花產量從1978年的217萬噸增加到1984年的625.8萬噸,年平均增長19.3%;油料總產量從522萬噸增加到1191萬噸,年平均增長14.7%;水產品從1978年的466萬噸增加到1985年的705萬噸,增長了1.51倍,到2010年,水產品產量已經達到5366萬噸,比1978年翻了11.51倍。按照張軍的計算,從1978年到1985年,中國農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為8.2%。農村居民家庭總收入從1978年的152元提高到1985年的547元,翻了3.6倍。到2010年則達到8120元,翻了53.4倍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131132頁、第133頁表32;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59頁表15。。按照林毅夫教授的測算,19781984年,由農村改革帶來的產出增長貢獻率總和為48.64%。其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貢獻率為46.89%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三海三聯書店,1994年,第95頁。。
由1978年開始的改制所帶來的農業生產巨大增長,基本上解決了國人的吃飯問題。這不但為之后城市和工商企業的改革提供了制度變遷的成功參照,也為后來的城市和工商業改革提供了空間和可能(改變了全國糧食短缺的局面)。農業經營制度從互助組、合作社到“一大二公”的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化,再到1978年之后從土地集體所有向農戶家庭“承包”(單干化)經營制的轉變,實際上為整個中國社會從建立一種空想的消滅私有制的計劃經濟的理想,逐步轉變為建立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市場經濟,提供了制度變遷的成功的實踐經驗。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民營工商業經濟自發性產生和成長,以至于到今天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無疑起到了先行和帶動作用。換句話說,1978年之后農業家庭承包經營制的普遍實行,實際上為中國民營經濟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并不為人們所意識的制度模板。用吳敬璉先生的話來說:“‘包產到戶改革的更加重要的意義,使中國找到了一種有別于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以國企改革為重點改革的戰略。這種改革戰略的特點,是不在國有經濟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驟,而是把改革的重點放到非國有即民營企業,因而被稱之為‘體制外先行戰略,或‘增量改革戰略。”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82頁;《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134頁。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吳敬璉先生也曾說:“‘包產到戶還有一個重大影響,就是促成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大大加快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用今天的話來說,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農村家庭經營承包制的制度變革,打開了民營經濟成長和發展的契機,加快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這才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偉大也是最為根本的制度變革。
“20世紀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開始以后,突破意識形態禁錮、引入市場機制成為改革的中心任務。為了繞開來自意識形態的巨大障礙,鄧小平等領導人采取了‘不爭論的策略,著重在經濟活動中逐步松動國有經濟的統治。在政府方面,一開始采取了一些變通的政策,使民間創業行為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在民間方面,利用這種新出現的機會,人們主動設法去開展創業活動。”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211頁。隨后,各種形式的民營經濟開始在中國大地“小心翼翼”地出現。但是,由于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仍在國家的法律和意識形態禁止之列,雇工超過7人就變成“私營企業”(雇工7人以下被定性為“個體企業”),私營企業的發展還受到很大限制在1982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在“文革”結束后修改的這部《憲法》還沒提到“私有經濟”或“私營經濟”,但是1982年的《憲法》已規定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實際上為今天我們所說的“民營經濟”即個人所有和經營的私營企業的產生、存在和發展開了綠燈。從此,中國的民營經濟才在“法律”和“政策”的一定程度的允許下自發地成長起來。。甚至在1983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中,對個體企業主雇工超過7人的,還實行“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的‘三不政策”。盡管有了些許松動,“但在中央領導機關中還有些人堅持要求開除那些雇工超過7人的小業主的共產黨黨籍”。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爭論”,“放兩年再看看”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8990頁。。在當時理論觀念的限制和政府政策約束的環境中,民營經濟發展首先采取的是鄉鎮企業的方式。因為鄉鎮企業從形式上講還是集體企業,是被允許的。因此,鄉鎮企業就在當時的理論框框和制度禁錮中發展起來,于是就有了當時的江蘇蘇南地區的鄉鎮企業的發展,這在后來被稱作“蘇南模式”。甚至浙江溫州和臺州這些私營企業迅速發展起來的地區,開始也是采取個體工商業或鄉鎮企業的形式:“浙江溫州、臺州鄉鎮企業也很發達,它們主要是由農民、手工業者等私人創立的個體商戶發展起來的,雖然這種‘溫州模式的鄉鎮企業往往由于要尋求保護而掛靠到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名義下(俗稱‘戴紅帽子),但實際上仍是私營企業。”另外,珠三角地區的“鄉鎮企業的特點是由港澳臺投資者(包括內地在港澳開設的企業,即所謂‘假洋鬼子)擁有,其業務也多為外向型的”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214頁。。
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了發展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方針。1988年4月,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11條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正式在憲法上承認了私營經濟的合法性。自此,中國的民營經濟才從無到有,迅速成長起來。“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民營經濟無論在工業生產還是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都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工業生產中,民營經濟產值已達1/3左右;在商業零售業,民營經濟成分增長得更快。與此同時,嚴格意義上的私營經濟(包括外資經濟)也開始嶄露頭角。”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9091頁。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一般小型國有企業,有的可以實行承包經營、租賃經營,有的可以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給集體或個人。”接著從山東的諸城和廣東的順德開始“放小”,即小型國有企業改制和民營化。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把非公有制經濟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后,“抓大放小”的中小型國有企業民營化(包括私有化)才在全國范圍內鋪開。
在私有民營企業從無到有的成長(“溫州模式”或“浙江模式”)和中小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同時,所謂的“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也在逐漸改制“蘇南模式”的概念1983年首次由費孝通先生提出。“蘇南模式”以發展集體經濟和鄉鎮企業為核心,追求村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因為非常符合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所以備受追捧。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為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為農機具廠,為集體制造一些農機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社隊企業發展明確予以支持,促使社隊企業步入了一個大發展階段。這些企業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改革開放初期,歷史的積累和來自上海的輻射為蘇南地區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當時的“短缺經濟”條件以及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信用擴張,對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已經占到60%。1998年,隨著中國進入買方市場以及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空隙的數量、形式和分布發生了本質變化,使在同一個空隙中生存的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競爭,蘇南鄉鎮企業經歷了第一次改制。當時的做法多是把鄉鎮企業改成集體控股的股份制企業或股份合作制,一部分鄉鎮企業隨之消亡或私營化了;另一部分則隨著股票市場的發展成長為企業集團,如中國最大的企業精毛紡企業陽光集團、軟塑包裝基地申達集團、磷化工生產企業澄星集團、模具塑料生產企業江陰模塑集團、金屬制品企業法爾勝集團,等等。這些由鄉鎮企業成長起來的企業集團變成了上市民營公司,已經不是原來意義的鄉鎮企業了。江陰的華西村則成了一個負債幾百億的上市公司,也不是原來意義的鄉鎮企業了。故在2005年就已有“蘇南模式”歷史終結的說法。參見新望:《蘇南模式的終結》,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在改革初期出現的“鄉鎮企業”,實際上是在當時黨的文件和憲法還不允許“私有企業”的情況下被逼出來的一種企業經營形式,它是“在鄉和鄉以上政府的直接領導下建立的,原來大部分由基層政府全資擁有。在改革初期,這種企業形式由于能夠得到基層政府的保護和有比較好的融資條件,曾經表現得很有生氣”。這一現象引起了國際上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但是當改革深化、企業日漸做大以后,它們和國有企業相似的缺點就日益顯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部分鄉鎮企業增長率下降,困難戶大幅增加,說明這一部分企業也迫切需要進行改制。”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211頁。到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黨的文件和政府政策允許私營企業的發展,蘇南地區和全國的鄉鎮企業摘下了“集體經濟”的帽子,紛紛改制成為私人企業或產權明晰的股份制企業。
回顧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中共“十八大”召開這一段時間經濟改革的過程,可以看出,這一歷史時期的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主要是通過黨的文件和決定,不斷放開國家對非公經濟的限制而整體推進。除了“十三大”報告、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50條)允許私有企業的發展,“十五大”報告也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外,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也明確規定,要“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重申“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正是因為在改革過程中,通過中共中央的報告和決定不斷放寬對私有經濟的禁止、管制及壓制,以及相關法律的允許、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才逐漸得到發展和成長,而90年代進行的中小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的改制和全國鄉鎮企業轉制和消亡,則是同一個過程。
四、中國經濟改革是在對外開放中向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學習,不斷進行制度創新的過程在《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的修訂版序言中,張軍教授指出:“作為后來者,即使在全球看,中國也毫無疑問是過去40年間向先行國家和地區學習技術和制度最快的國家。這一點讓我深信不疑。”張軍對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的這種判斷非常深刻,也符合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史實。這一點到今天卻往往被人們所忽視或者說遺忘了。中國在國內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同時,也對外開放。這種對外開放,并不僅僅只是增加對外出口和貿易以及引進外資,實際上是向“先行國家和地區”學習科學技術、現代企業組織形式、公司制度和管理方式、現代金融制度乃至宏觀經濟管理方式,并同時進行制度學習和創新的過程。正如周雪光所言:“開放所引起的全球化交流給中國社會造成了震動,帶來了壓力,激發了活力,也給中國社會內部的改革提供了持續的推動力。沒有‘開放這個前提,就無法想像和理解中國社會變化的深度和廣度。在這個意義上,對外開放是中國社會內部持續改革的動力源。”周雪光:《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總第170期)。
從1978年啟動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以來的歷程來看,中國之所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兩年后就開啟了經濟改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經過28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實驗和十年“文革”,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因而從中共黨內高層到社會各界,人人思變,人人求變;另一個方面,今天卻往往被人們所忽視,這就是當時世界上其他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并正在進行各種各樣的經濟改革,各自探尋著本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促使我們全面反思過去28年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建設,從而開始了經濟改革的進程。實際上,迄今為止,新中國一直進行著經濟制度的變革。只不過從1978年起,這一經濟制度變革進程改變了方向。
從現代世界歷史來看,1917年,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后,經過了“戰時共產主義”的短暫實驗和“新經濟政策”的調整俄共(布)在1917年“十月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后,在1919年3月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奪取政權后的第一個新黨綱,隨即在全國推行了后來所稱的“戰時共產主義”的實驗。包括剝奪大資本,把大中型企業收歸國有,把整個國民經濟轉變成一個“絕對統一的聯合托拉斯”;銀行全部收歸國有,使它成為生產的統計機構和財政分配機構,銀行的所有業務都由國家壟斷;逐步取消貨幣,取消一切商品貿易,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均由國家集中分配;強制勞動,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在先進地區的農村興辦國營農場,在落后的農村地區則要把眾多的“小經濟”聯合起來,組成公社和勞動組合,實行糧食征集制。戰時共產主義實行嚴格的軍事紀律和配給制度,這固然幫助布爾什維克黨保住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內戰結束以后,蘇聯農民尤其感到不堪忍受,普遍抗糧不繳,糧食的征收不得不動用軍隊才能完成。工人也開始罷工。接著出現了社會動蕩和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連列寧也承認,“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的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接著,在1921年3月,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1921年5月,蘇維埃政權通過關于交換的法令,恢復商品交換,國家通過合作社組織工業品直接交換農民手中的余糧,同時允許私人在地方范圍內進行市場交易。在工業領域,一切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中小企業則允許私人經營,并在一切工商企業中實行“商業化原則”和“商業核算”。在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的條件下蘇維埃政府恢復了市場制度(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1314頁)。1924年列寧逝世后,斯大林上臺,新經濟政策被慢慢廢除。1928年,斯大林公開宣布停止實施新經濟政策,并加速開展農業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逐步形成了后來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領導俄共(布)靠國家政權的強制力量,加速開展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形成了后來所說的“斯大林模式”。之后蘇聯經濟尤其是重工業經歷過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但是,盡管蘇聯的農業實現了機械化,集體農莊體制和政策的失誤使得蘇聯農業產值嚴重下降。“到20世紀50年代,戰后的恢復時期已經結束,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日益顯露,蘇聯、東歐國家增長率不斷降低,效率下降,各國先后提出改革原有經濟體制的問題。”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22頁。首先,在赫魯曉夫的領導下,蘇聯在1954年就開始農業改革,1957年開始了向地方政府放權的分權制改革,接著在1965年進行放松計劃控制、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但是這些改革均沒有成功,反而使蘇聯從20世紀70年代起進入近二十年的“停滯時期”。南斯拉夫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六七十年代實行了基于“自治企業制度”的市場經濟。匈牙利從1968年1月1日起開始了建立“新經濟機制”的改革,用政府對企業的間接控制代替了直接干預,并逐步放寬了對非國有小企業的限制,同時允許在有限的范圍內成立小型私有企業(但大的私營企業仍然不允許建立)。波蘭也在19571958年開始了向企業放權讓利的改革。而捷克斯洛伐克在1962年開始了較匈牙利更為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但引發了“布拉格之春”(在共產黨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領導下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發生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隨后在1968年8月20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干涉,使捷克斯洛伐克亞的經濟改革半途夭折。正是在那樣的一個國際環境中,“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和當時的黨政領導人還是開始了經濟改革,且也像蘇聯和東歐各國一樣,首先進行的是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改革。這實際上是在向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學習。在經濟理論界,也存在著到底向匈牙利模式學習,還是向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學習的理論討論。也因此,邀請了許多東歐經濟學家來華做報告和交流,包括捷克著名政治家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奧塔·錫克(Ota Sik,19192004),波蘭經濟學家、市場社會主義學派傳人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19212007),以及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anos Kornai, 1928),等等。
“隨著20世紀80年代初期對改革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對外部發展經驗的更多汲取,中國改革理論的研究逐漸超越了70年代末期著重討論調動積極性的具體措施的水平,進而研究應當用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來取代計劃經濟舊體制的問題。在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當時提出了三種可供借鑒的體制模式。”按照吳敬璉先生的回憶,當時理論界討論的這三種模式,一是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東歐模式”),即在計劃經濟框架下給予企業更大自主權;二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即日本、韓國、新加坡所采取的權威主義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體制(“像鄧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賞‘四小龍,特別是新加坡的許多做法”);三是自由市場模式(“歐美模式”),即“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在市場上提供私用物品”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5253頁。。
在改革開放初期,整個國家想從斯大林那種以國有經濟為主、集體經濟為輔和基本上消滅私有制與民營經濟的高度集權的經濟模式中走出來,開始學習匈牙利模式或南斯拉夫模式,但這些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后均被證明是不可行的。在此背景下,中國開啟了自己獨立的改革探索之路。隨著農業家庭經營制的普遍實行、城市大規模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民營經濟的崛起和外資的進入,中國實際上開始向西方國家學習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開啟了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改革進程。除了本文上述兩小節討論的農業改革、國企改革和民營經濟的崛起外,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逐步建立并不斷完善現代金融體系
(1)重建現代銀行體系。1978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從財政部分離出來。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作出決定,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到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至此,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以法律形式被確定下來。與此同步,在1984年把中國人民銀行的信貸業務和儲蓄業務分離出來,成立了中國工商銀行,并在全國范圍內設立了分支機構。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恢復成立。同年8月,中國建設銀行從財政部獨立出來。從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開始,大型商業銀行、各種地方銀行、政策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中小商業銀行恢復和建立,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于1986年恢復開辦,外資銀行也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和回到中國。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業集團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和貨幣經紀公司也在之后發展起來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194196頁;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233248頁。。
(2)保險業迅速恢復和發展。1979年國務院要求開展保險業務。1980年底,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逐步恢復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國省級分支機構。1988年成立了中國平安保險公司,1991年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成立。到1992年,全國已經有6家保險公司。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于1995年6月30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之后保險業迅速發展。到1999年,全國共有28家保險公司,其中國有獨資公司4家,股份制保險公司9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4家,外資保險公司分公司11家。到今天,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保險市場。近十年來,每年超過20%的年均增速,也使得保險業成為中國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
(3)貨幣市場開始建立和發展。“1980年至1984年期間,各種專業銀行開展商業票據貼現業務;從1982年開始,首先在上海試點開辦同城票據承兌貼現業務,1985年中國人民銀行允許銀行間辦理轉貼現業務;1981年財政部恢復發行國債,1987年至1988年,開發企業債券和國庫券交易市場,1987年先開放銀行間市場,銀行間債券回購市場和銀行票據貼現也逐步出現。截至2009年8月,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參與者包括銀行、證券公司、財務公司、農聯社、信用社、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2093家。同業拆借利率于2007年推出,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統一貨幣市場。”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196197頁。
(4)外匯市場的設立與發展。“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實行統收統支的外匯管理體制,一切外匯收入必須按照官定匯率出售給國家,一切外匯支出都要由國家計劃安排,因此中國外匯市場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197頁。1980年10月,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中國銀行在北京、上海等12個大中型城市辦理外匯調劑業務,1985年底在深圳設立了外匯調劑中心;1988年允許地方政府外匯留成。同年在北京設立了全國外匯調劑中心,形成全國統一的外匯調劑市場。1991年12月1日起,允許境內中國公民和定居在境內的外國居民進行外匯調劑。1994年4月在上海設立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提供銀行間外匯交易、人民幣同業拆借、債券交易系統并組織市場交易,辦理外匯交易的資金清算、交割,提供人民幣同業拆借及債券交易的清算提示服務,以及開展經人民銀行批準的其他業務。
(5)開設證券交易市場。這個過程值得專門回顧。1984年7月,北京天橋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股份制也由此開始進入了正式試點階段。1986年9月26日,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柜臺——靜安證券業務部——的開張,標志著新中國從此有了股票交易。1990年3月,政府允許上海、深圳兩地試點公開發行股票,兩地分別頒布了有關股票發行和交易的管理辦法。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正如小崗村的18戶農民冒著風險“包產到戶”一樣,中國證券市場和期貨市場也經歷了同樣艱難的創生過程,許多推動者后來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磨難,有的甚至坐牢、自殺。如“上海灘證券三猛人”的管金生(萬國證券的創立人,有“中國證券教父”之稱)后來就被控受賄和挪用公款而判入獄17年;闞治東(時任申銀萬國總裁)也曾入獄21天。曾參與“327國債事件”的魏東跳樓自殺,年僅42歲;同樣參與過“327國債事件”的金融大佬戴志康在2019年也因P2P互聯網金融公司資金鏈斷裂而投案自首(陸一:《無常的博弈:327國債期貨事件始末》,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這些證券行業的風云人物當然各有各的問題,但由此我們也會發現,過去40年中國所有領域的改革,都是在艱難曲折中慢慢演進的過程。,同年12月29日正式營業;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試營業,1991年7月3日正式開業。之后中國股市在跌宕起伏中不斷發展。在兩大證券交易所正式營業后,各種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信托公司也涌現出來。
(6)期貨市場開始發展起來。1990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中國鄭州糧食批發市場以現貨交易為基礎,引入期貨交易機制,作為我國第一個商品期貨市場正式啟動。19921993年,中國期貨市場出現了盲目發展的混亂局面。“1993年初,全國只有7家期貨交易所。到年底已經有33家鳴鑼開業。……1994年以后又有幾家交易所開業。當時全世界商品交易所才有四十多家,而我國期貨市場剛剛起步,不到兩年時間,就相繼成立了四十多家交易所,政府部門組建的期貨經紀公司達三百多家,以交易所會員身份從事期貨代理的現貨企業達一千多家。”按照陸一的研究,在19921994年,中國的期貨市場比較混亂,“期貨交易所一哄而起,交易品種重疊上市”,市場參與者“在交易過程中,不講規則,欺詐行為屢屢發生。市場參與者主要是國有大公司,贏了錢不吭聲,輸了錢就告對方,不僅上報國務院,還上告到黨中央”(陸一:《無常的博弈:327國債期貨事件始末》,第61頁)。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期貨市場不斷完善和發展,商品期貨、金屬期貨、能源期貨、金融期貨、黃金現貨和期貨如上海黃金交易所自2001年成立以來,不斷發展。到2019年,上金所黃金交易量達到6.86萬噸,連續12年成為全球最大的黃金現貨市場。2019年10月14日,上金所與芝加哥商品期貨交易所同步上線“滬紐金”和“上海金”期貨合約,已經與國際接軌,受到全球投資者的廣泛認可。截至2019年底,上金所“滬紐金”總成交量達到38.02噸,成交額128.47億元(特別感謝上金所王振營總經理為筆者提供了上金所最新數據。——筆者注)。乃至股指期貨都在21世紀后發展起來了。各種租賃公司、貸款擔保公司也涌現出來。
到目前為止,應該說中國金融市場體系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凡國際上已有的交易形式我們都已具備。但是,也許有人還沒有意識到,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改革過程中所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是向發達國家進行制度學習的結果。從當代世界史的變遷來看,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已經不動聲色地、大規模地乃至全面地向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市場制度的學習,且朝著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開始了自己的探索和制度建構進程隨之,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蘇聯和東歐改革經濟學家奧塔·錫克和布魯斯等人在中國經濟學界實際上也已經沒有市場。他們的理論觀點也在變化,并在國際上慢慢被人們所遺忘。。
(二)向西方國家學習政府對現代市場經濟進行宏觀管理的手段、機制和方法
在改革初期,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基本上還是一個變異了的斯大林計劃經濟模式。由于市場不發達,政府管理機構仍是管理計劃經濟的思維,連我們的經濟學家們,整體上也還缺乏現代宏觀經濟運行的知識。但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整體過渡中,中國政府也在摸索經濟運行的宏觀管理的機制和方法。吳敬璉先生和張軍教授都提到1984年在浙江召開的“莫干山會議”,以及會議所提出的“價格雙軌制”及其配套改革。從所提交的價格改革意見和建議中可以看出,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之于宏觀經濟的管理體系、方法和手段還沒有完全形成,主要還是用計劃經濟的、行政命令和控制的辦法來管理經濟。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的央行地位還沒有完全確立,金融系統還不發達,乃至國企利潤上繳及留成多少也還在摸索之中。民營企業還非常弱小,外資也沒有大舉進入。在那樣一種過渡性體制中,政府實際上還不懂得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調節宏觀經濟,政府官員和經濟學界主要關心和思考的是如何激勵企業增加生產,如何激勵農民多生產糧、棉、油,如何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以及如何管控通貨膨脹。到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情況開始有了一些改變,許多老中青經濟學家以及國際上的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和轉型經濟學家參加了這次會議。中方除了薛暮橋、安志文、馬洪、高尚全、劉國光等體制內官員和老一代經濟學家,還有戴元晨、陳吉元、周叔蓮、楊啟先、吳敬璉、趙人偉、張卓元等中年經濟學家,以及項懷誠、洪虎、樓繼偉、李克木、田源、郭樹清等青年經濟學家。參會的國外經濟學家包括美國宏觀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英國經濟學家艾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亞歷山大·凱恩克勞斯(Alexander Cairncross),日本經濟學家小林實,世界銀行駐華辦事處林重庚,以及東歐經濟學家布魯斯、錫克和科爾內等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106111頁。。1985年9月在游輪上召開的這一為期六天的國際會議的主題,就是“宏觀經濟管理和改革”。會議結束后,形成了七大專題報告:“目標模式和過渡步驟”“財政政策與宏觀管理”“貨幣政策和金融體制的改革”“收入政策與宏觀管理”“經濟增長與投資問題”“通貨膨脹和價格問題”,以及“實現宏觀經濟間接控制目標的一個重要前提”。這說明,到這個時期,中外經濟學家們已經開始考慮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管理機制和手段問題。實際上,從那時開始,隨著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包括央行的建立、國有企業利改稅、民營企業的崛起,以及稅收制度的改革和現代金融體系的生成與成長,中國已開始向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學習宏觀經濟管理機制、方法和手段。另一個往往被人們所忽視的事實是,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大轉變,是國民經濟總量的核算體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從1952年到1993年,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還是引自蘇聯、東歐計劃經濟體制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簡稱MPS,其核心指標是“社會總產值”,主要覆蓋農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飲食業五大類行業的產值。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繼續采用MPS進行國民經濟核算,已經不能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統計局遂著手研究西方成熟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的國民賬戶體系,簡稱SNA核算。到1985年,已經開始使用SNA體系的國內生產總值核算。“1992年1月,國務院組織有關方面專家進行論證,并通過了這一方案。同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實施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方案的通知》,要求在全國范圍內分步實施這一體系。”接著,從1993年起,國家統計局“以取消國民收入指標為標志,GDP成為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從而與國際上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接軌許憲春:《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革與發展》,《宏觀經濟研究》2006年第3期。。今天大家也許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均是中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向西方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制度學習的過程。
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上與國際接軌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按照吳敬璉先生的研究,從1956年到1979年,中國的財稅體制是政府公共財政與企業財務合一而組成國家財政系統。在這種體制下,政府運用自己的定價權和國有企業壟斷權,通過稅收以外的方式組織大部分政府預算收入。“屬于中央的固定收入有關稅、鹽稅、煙酒專賣收入,以及中央管理的企業、事業收入和其他收入;屬于地方的固定收入有印花稅等七種地方稅,以及地方國營企業、事業收入和其他收入。”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231232頁。按照楊之剛和馬駿的研究,從1958年至1978年之間,中國的稅制極為簡單,僅包含工商稅、農業稅和關稅等十種稅收,且稅收收入占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50年的78.8%降至1978年的45.9%。經濟改革啟動之后,19801993年,中國政府施行的是以財政承包制為中心的財稅改革。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則是以分稅制改革為主要特征。“稅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按照‘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的原則,規范稅制,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稅收制度。”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241242頁。后來幾經調整和改革,才形成了獨特的以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房產稅、車船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車輛購置稅、耕地占用稅、煙葉稅、關稅、船舶噸稅、環境保護稅等18個稅種,以及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和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等為主要財政收入的體系。這其中有向國外學習的地方,也有中國政府的創新。
從經濟改革的整個歷史過程來看,隨著央行的建立和1994年財政稅收制度的改革,中國政府機構也作了一些調整。到20世紀末,已經建立起基本與國際接軌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但是,由于自身獨特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中國的宏觀管理體系也有很多與國際上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國還有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央行缺乏獨立性,且政府財政預算收支實際上還沒有立法機構的約束和制衡。但整體而論,一個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管理體系和方式,在中國已經形成。
(三)向西方國家學習現代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
在《改變中國》第七章,張軍教授說:“1993年總是被國外經濟學界看成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分水嶺,標志性的事件是在這一年的11月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之前是商品經濟或者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說法,改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對國有企業而言,這更像是一個加速而激進的改革戰略的開端。”接著作者指出,“1994年8月2326日,由吳敬璉、周小川和榮敬本、樓繼偉分別牽頭的兩個課題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及‘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聯合國家經貿委,共同在北京的京倫飯店召開了一個國際會議,主題為‘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也就是后來所說的‘京倫會議”。張軍還認為,如果說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重點討論了宏觀經濟管理問題,“京倫會議”參加“京倫會議”的除了吳敬璉、榮敬本、周小川、樓繼偉、陳清泰、張卓元、李劍閣、劉遵義、錢穎一、許成鋼、吳曉靈、謝平、肖捷等中方經濟學家外,還有哈佛大學的哈特(Oliver Hart),斯坦福大學的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麥金農(Ronald I. Mckinnon)、青木昌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拉迪(Nicholas Lardy)等。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于8月25日下午會見了外方代表。見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15316頁。討論的顯然就屬于微觀范疇的問題了。張軍的這個細微觀察非常重要,也非常深刻。回顧中國經濟改革歷史上的三次重要會議,可以認為,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標志著當時經濟學界和政府領導人還在摸索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調控物價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合適手段;到“巴山輪會議”召開之際,已經開始面向現代市場經濟考慮宏觀經濟管理了;到了“京倫會議”時刻,隨著國有中小企業和虧損企業大規模的民營化及民營企業的崛起、央行的成立和證券市場的建立,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展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階段。正如張軍所言:“是的,在1994年,我們的理論界和企業界還不清楚什么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控制權(control rights)、信托責任(fiduciary)、持股人(shareholder)和利益相關人(stakeholder)以及股東代表大會,對董事會、監事會等這些治理制度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也還不甚了了。對CEO、CFO、MD(Marketing Director,即“營銷總監”——引者注)等這些在西方公司里流行的稱呼同樣比較陌生。京倫會議毫無疑問開拓了中國經濟學家的視野,讓我們看到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公司化或法人化,其核心是在企業內部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這些概念和討論無疑影響了1994年之后的企業改革的政策方向。”參見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14、318頁。就筆者所知,實際上,在整個經濟學界乃至整個社會對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還不甚了了的時候,吳敬璉和錢穎一1993年8月24日發表在《經濟日報》的“關于公司化”的一篇文章,對現代公司制度和如何建立現代公司制度進行了介紹。
中央政府在1994年11月出臺了《選取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的方案》和《深化企業改革,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規范意見》等文件,開啟了“抓大放小”改革戰略和大型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可是,就在中央政府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新方向的同時,大中型國有企業的基本面卻在進一步惡化。……1997年底,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的16,874家大中型工業企業中虧損者達6599家,虧損額為665.9億元。另外,國有企業改革導致下崗職工人數激增,19961997年,下崗職工總數已經達到1500萬人。”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21頁。正是在此背景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在1997年提出著名的“三年國企脫困”改革策略。“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對于國有資產管理的問題,應實行‘國家所有,中央政府和地方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的管理模式”,隨后在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成立了新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即“國資委”。到“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時,股份制成為國有企業改組改制的主要形式”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24325頁。。張軍這里沒有進一步往下講,根據《東方財富網》2017年提供的數據,到2016年年底,滬深兩市3118家上市公司中,國企上市公司共計1095家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3,20170223713991477.html。到目前為止,全國97家大型央企全部(或通過旗下公司)上市。現在看來,不管是央企、地方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合資企業,一旦上市,無疑都是按照現代公司制度來運作。即使還沒有上市的各種類型的大中型企業,盡管各有各的問題,但大部分企業也都是按照現代企業公司制度進行運作。到今天,也許我們并沒有認識到,在過去四十年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我們實際上已經向市場經濟國家進行全面的現代企業制度學習,并在學習過程中進行了獨特的制度創新。尤其是國企和國有控股企業,通過對于先進企業制度形式的借鑒,形成了中國獨有的“現代企業制度”。
(四)對外開放和自主制度創新
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一書第6章,吳敬璉先生指出:“1978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同時指出:為了實現現代化,必須‘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這一方針后來被概括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并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改革以后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也就是市場取向改革和對世界市場開放同時進行和相互促進。”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155頁。正如所言,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總體由兩翼構成:一是對內進行市場化改革;二是對外開放。如果說國內的市場化經濟改革,是市場秩序的自發成長和對外學習的過程,對外開放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中國的制度創新。
197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實際上包括三個方面:
1.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
盡管國內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被視作中國經濟改革的兩翼,但單從進出口貿易來看,中國的對外開放應該說比國內的市場化改革還要早。按照吳敬璉先生的研究,從1949年到1971年,實際上實行的是閉關自守的發展戰略。在1958年“大躍進”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后,中國領導人愈發強調“自力更生”,在對外關系上采取了閉關自守的國策。這不僅導致了整個國家的貧窮落后,而且使得對外貿易總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在1949年中國的人口為5.4億,進出口貿易占全球的1.5%。到1970年,對外貿易總量只占全球的0.7%了。到1977年,中國的人口已經達到9.4億人,占全世界42億人口的差不多1/4,外貿總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卻下降到0.6%。實際上,到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領導人已經開始意識到長期閉關鎖國的危險性,并且隨著與美國關系的松動和中日關系正常化”,開始與西方國家發展貿易關系,主要是進口了許多套大型工礦設備。粉碎“四人幫”之后,從1979到1994年,基本上是采取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但是到了1994年后,尤其是在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中國則采取了全面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366370頁。。單從外貿依存度(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來看,1978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為9.5%;到2012年,已經達到47%;到2016年,竟然高達65.17%(2018年下降到33.7%)。1978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只有97.5億美元,1994年達到1210.1億美元,2012年更是達到20,489.4億美元。201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達到14%。近兩年有所下降,但2018年仍高達11.75%,高于美國的10.87%。
2.外商直接投資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吳敬璉先生說:“中國營建對外開放基地的核心任務,在引進國外資金,引進先進技術,獲得國外企業在成長發展中積累的經營管理經驗及世界市場的營銷渠道。所有這些,都可以通過外商直接投資(FDI)較快地實現,因此,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385頁。自20世紀70年代起,中國各級和各地政府不斷采取一系列優惠政策,大力吸引外資,外資投資逐年增長。從1979年到1982年,進入中國的外資計17.69億美元;到1994年,就達到了337.67億美元。2001年年底加入WTO之后,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進一步打開。到2002年,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27.43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到2012年,則達到1117.2億美元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385386頁,表8.6。;到2018年,實際利用外資繼續增加,更是達到1349.7億美元,這個數字還未包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使用外資的數據。到21世紀初,全球5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絕大多數已經在中國擁有投資項目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387頁。。按照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2019年10月發布的《跨國公司投資中國40年》報告,截至2018年底,中國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96.1萬家,實際利用外資2.1萬億美元。外資的大規模進入,也直接貢獻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按照美國經濟學家恩斯特(Micheal J. Enright)根據中國統計數字的估計,“當我們把投資的直接影響以及外資的營運活動、供應鏈和員工的消費支出都包含在內,則19952013年期間,外資和外資企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約為16%34%,對中國就業的貢獻約為11%29%。而且,外資的影響力并沒有隨時間遞增而有明顯下降,因為在我們分析數據的截止年份(2013年),外資和外資企業占中國GDP的比重是33%,占中國就業總人口的比重則為27%”恩萊特:《助力中國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閆雪蓮、張朝輝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7年,第30頁。。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外資的大量進入,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國際市場網絡、國際定價體系及其貿易規則,實際上也整體性地提升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促使中國融入了經濟的全球化。除此之外,吳敬璉先生還發現,20世紀80年代之后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的發展,對中國市場體系的形成和市場制度的完善,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外資企業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經營,對于良好經營環境有較強的訴求。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各級政府主要靠對外企實行優惠政策來回應這種訴求。但是,只對外商實行優惠政策,一方面意味著把本土企業視為二等公民,在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上對本土企業產生‘擠出效應;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外商企業建立透明的競爭規則和法治的經營環境的要求,內外企業的這種要求,也成為促進中國進行經濟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吳敬璉先生也發現,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力的加強,并通過強化市場競爭力提高了經濟效率:“本土企業競爭力的提升主要來自于:(1)完善企業管理體制和激勵機制,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2)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便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技術和管理的‘溢出效應;(3)提高戰略管理能力,逐步形成全球競爭視野,等等。”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171頁,第390394頁。今天看來,市場化改革中的國企改制、民營企業的成長與外商直接投資的互動,共同推動了國內市場的形成和與國際市場的接軌,才有了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3.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園、高科技園區和自貿區的建設與發展
在《改變中國》第四章,張軍教授說:“40年來中國經濟的改革應該解讀為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實驗和制度變遷過程。這話聽起來是很震撼人心的。但是,對于40年前的中國領導人而言,制度變革并不是一個可以事先設計得當的試驗,沒有人對此有足夠的知識準備。”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133頁。這一觀察和判斷十分深刻。我這里要補充的是,從改革開放過程來看,如果說1987年對外開放的兩翼(1)外資的進入以及(2)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一種制度學習過程的話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到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都這么做過。,那么,開辦經濟特區,以及后來在許多城市建立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園區、高新科技園區,以及“保稅區”“自由貿易區”等等,卻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自己的制度創新和實驗。就連鄧小平本人在1985年8月1日會見日本客人時也曾說:“前不久我對一位外國客人說,深圳是個試驗,外面就有人議論,說什么中國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變,是不是我否定了原來關于經濟特區的判斷。所以,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不矛盾。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轉引自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133頁。
對于深圳,國內已經有許多專著進行研究。在《改變中國》一書中,張軍專門用了一章“特區實驗場”來回顧深圳的輝煌發展歷程,并在2019年出版的一本專著《深圳奇跡》中,全面回顧和探討了深圳初建的坎坷經歷及其之后的崛起過程,故這里我們就不再復述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深圳確實如同被施了法術一般,在短短四十年的時間里,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邊陲小鎮,到擁有2000萬人口、GDP總量超過2.7萬億元(2019年數字)的現代化都市。到目前為止,深圳位居世界城市經濟競爭力排行榜前列。1979年,深圳GDP僅1.97億元(人民幣,下同),人均GDP僅606元;2017年,深圳GDP2.24萬億元,人均GDP18.31萬元,GDP年均增速達23%,創造了世界罕見的“深圳速度”。今天,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深圳從1979年撤寶安縣建市及1980年設經濟特區,其在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作用是什么。
首先,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深圳和其他經濟特區(包括珠海、汕頭、廈門)的開辦,無疑是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李先念、習仲勛、吳南生、葉劍英、谷牧等一致同意下的一項重大制度實驗和創新另據有關人士研究,1979年4月,廣東省委提出,希望中央能根據廣東緊靠港澳,華僑眾多的特點,給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頭建立出口加工區。這一設想得到了鄧小平的大力支持。鄧小平說:“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就叫做特區。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筆者感謝周瑞金先生在一條微信中提供了這一信息。另據張軍的研究,在“經濟特區”概念提出時,曾在中共內部就特區的性質進行過激烈的爭論。“長期領導中國經濟建設并且在黨內擁有很高威望的領導人陳云對經濟特區的運作方式一直持謹慎的態度。根據時任新華社副社長曾建輝1984年在《瞭望》周刊的文章所述,1982年陳云曾經批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陳云的這個意見對特區在早期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參見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論述》,第151頁。。這說明,在“文革”剛結束不久,老一輩革命家的思想還是相當開放的正如張軍所說:“當時,以蘇聯經濟學教科書為教條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處于經濟理論界的權威統治時期,社會和經濟制度的‘性質(或者‘主義)還仍然是中國經濟學家考慮問題的核心概念框架。因此,今天我們對40年前深圳和珠海等為什么能被中央考慮并批準為‘特區充滿好奇。”參見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140141頁。。其次,我們回顧深圳從20世紀80年代初誕生并迅速崛起,所關注的并不在于其經濟總量已經位列中國城市的第三位并成為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中國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輝煌成長史,而在于其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制度創新與擴大開放的實驗和示范作用。正如張軍所見:“40年來盡管風雨坎坷,深圳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也確實是名副其實的試驗場。它有1979年第一個引進香港‘外資興辦的來料加工企業;它有1981年在蛇口第一個采用的建筑工程招標制度;它有1983年向社會公開發行(IPO)的全國第一張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的股票;它有1985年成立的第一個外匯交易中心;它有1987年第一個土地使用權的拍賣會;它有全國第一個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制度的改革;它還有1990年探索出的國有資產三級授權經營的模式;它是建立勞動服務公司和實行勞動就業合同制的第一個嘗試者,是最早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區域,也是實行政企分離、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和引進招聘上崗制度的先鋒。”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133134頁。回頭來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深圳實行的一些制度創新與改革的成功經驗,到后來基本上都在全國鋪開實行了。20世紀80年代深圳經濟特區(以及珠海、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這些特區顯然沒有深圳那樣成功)開發的成功,堅定了中央決策層更進一步開放的信心。“1984年5月,\[中央\]決定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給予外資企業與經濟特區相類似的待遇。”“1985年2月,又把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閩南的廈、漳、泉三角洲地區,以及膠東半島,遼東半島列為經濟開發區。”“1988年4月,決定興辦海南經濟特區。”對各種各樣的經濟特區而言,開始只是改革的試驗區,主要是吸引外資和內部制度創新。當它們的改革實驗成功了,其經驗和做法再推向全國。因此,從整個國家來看,建立經濟特區本身就是中國式改革的一種制度創新。正如張軍在新近出版的另一本書《深圳奇跡》一書所言:“在我看來,‘特區這兩個字給深圳做了一道防火墻,確保了深圳在20世紀80年代不受計劃體制的干擾。”“從幾十年的歷史來看,今天就是因為在一開頭特區被給予了屏障,擋住了無數的有形之手,這使得深圳能夠營造出讓企業說了算、讓市場說了算的制度,這種環境在國內的其他地方是非常少見的。”張軍:《深圳奇跡》,北京:東方出版社,2019年,第393、394頁。張軍的這一判斷,確實道出了深圳奇跡的最深層原因。今天,我們又可以說,深圳從80年代開始崛起到21世紀初迅速成長,在深圳實行的市場制度,逐漸透過了特區的“防火墻”,擴展到整個中國大陸,才有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
除了設立深圳等經濟特區這種改革開放的試驗區外,在中國改革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章就是浦東開發。張軍在《改變中國》一書中專門講述了這一歷程。由于深圳的經濟改革如火如荼,鄧小平1990年來上海過春節期間,就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镕基談到了浦東開發,即在上海搞深圳式的特區。回到北京,鄧小平就同政治局的同志商討浦東開發事宜。“就這樣,在鄧小平的敦促之下,199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終于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決定。4月18日李鵬總理親自到上海宣布這一決定,中央同意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特區的政策。4月18日就成了浦東開發的紀念日。”“1990年5月3日下午,在浦東的浦東大道141號,上海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和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正式掛牌,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的朱镕基出席掛牌儀式。”張軍接著還記述道:“1991年2月18日,農歷大年初四,鄧小平一家登上了上海的新錦江大酒店41層的旋轉餐廳眺望上海市區的面貌,鄧小平回頭跟身旁的朱镕基說:‘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鄧小平講了浦東‘金融先行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鄧小平回應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現在就要做起。也就是在這個場合,鄧小平說了那個著名的‘三個一點的話: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59、363頁。現在讀到這些話,是多么激動人心!這些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實際發生的故事,現在又有多少人知道?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世界上摩天大樓最密集的浦東新區的成長和崛起背后,有這么多真實而感人的故事?今天,在鄧小平逝世二十三年之后當筆者寫到這里的時候,時值鄧小平逝世整整二十三周年。——2020年2月19日晚謹記于上海寓所。,有多少人會想到,GDP已過萬億元的浦東新區的崛起,原來竟萌生于鄧小平的一念之間。這難道不應該記入中國乃至世界歷史?在比較詳細地回顧了中央給予浦東開發十項優惠措施及浦東發展的輝煌歷史后,張軍教授最后說:“浦東宣布開發已經28年了。這28年也是上海這個昔日的遠東大都會和計劃經濟時期的制造業重鎮華麗轉身的28年。今天,上海不僅產出了將近3萬億人民幣GDP的經濟總量,而且毫無疑問已經成為中國最為國際化的超級大都市。也正是由于浦東的開發和上海經濟的轉型,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地區才得以成為中國與全球生產鏈緊密銜接的制造業中心,與南方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相得益彰。據統計顯示,19792016年,接近3/4的外資集中于中國的沿海地區,尤其以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主。”張軍:《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第383頁。
確如張軍所言,浦東和上海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快速增長,帶動了長三角地區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的迅速崛起。臨近上海的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1994年2月經國務院批準設立,同年5月啟動。蘇州工業園區行政區劃面積278平方公里,是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間的重要合作項目,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和“國際合作的成功范例”。蘇州工業園區率先開展“開放創新”的綜合試驗,成為全國首個開放創新綜合試驗區。到2018年,蘇州工業園區共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570億元,公共財政預算收入350億元,進出口總額1035.7億美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93.7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1萬元。2006年,經江蘇省政府批準,江蘇昆山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正式成立;2010年9月,昆山經國務院批準成為設在縣級市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到2018年,昆山市的GDP已經達到3832.06億元。接著,各種各樣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高科技園區、工業園區在全國各地發展起來。據統計,至2012年底,國家級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已經達到171個,其中東部84家,中部49家,西部38家,遍及全國各個省市區(實際上,各省許多經濟技術開發區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設,甚至比浦東開發還要早),成為所在地區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增長極。正是這樣由點到面,遍地開花,從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的經濟特區開始,再到浦東和其他各省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設立和發展,構成了過去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的主旋律。
概言之,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經濟改革,先從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試水,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變革的突破,再到國企改制(“抓大放小”和大規模國有企業民營化)與民營經濟崛起,伴隨著對外開放、經濟特區設立和金融體系的重建與發展,宛如一部宏大的歷史交響曲,如此波瀾壯闊,聲震寰宇。中國經濟社會在過去四十年就是這樣一路走來,實際上經歷了一場偉大的漸進性乃至革命性的制度變遷,從而造就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
五、觀念的變遷與深化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將會走向何方?
在1974年出版的《組織的極限》一書中,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說過:“我以為,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導致了歷史上的諸多大災難。這種對過去某一個目標的追求(commitment to a past purpose),在經驗表明應該被廢棄(reversed)的時候,反而強化了原初一致認同的目標。”接著,這位當代社會選擇理論大師又告誡我們:“理性和前瞻真的能夠帶來延遲和懷疑;同樣,人們的良知、對他人的尊重,以及我們應當擔心的對遙遠和不可預見結果的模糊意識也會如此。真實信仰者在社會行動中往往更有效率。至于這種行動對與錯,那是另外的問題。……這里并沒有簡單的結論,我也不想給出任何結論。在歷史上有許多時刻,我們只是簡單地必須行動。我們完全知道我們對諸多可能結果的無知,但是為了保持我們完全的理性,我們必須承擔并不一定確定如此的行動的后果。我們須得總是在認識過去的錯誤和變化過程的可能性上保持開放的心態。”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29.經歷了四十年改革開放,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關節點上,重讀當代經濟學泰斗的這句話,意味深長。回顧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歷程,我們會發現以下兩點:第一,經過四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運行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型,已經從斯大林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或言基本上排斥市場交換的行政命令經濟),轉向了具有現代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在此過程之中,社會各界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甚至一些目前仍然持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理論范式和知識框架的經濟學人,也對市場經濟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轉變。在市場化改革的輝煌成就面前,在經濟學界乃至社會各界,恐怕幾乎無人會否認通過市場交易來組織社會分工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合理性了。在過去四十年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觀念都在變,每個人都在不斷“提高理論認識”。每個經濟學家若回頭看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也許都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的理論認識在過去幾十年間竟然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甚至也有許多經濟學家完全從一個“計劃派”走向了“市場派”。就連中共“十三大”之后的歷屆全會報告,尤其是“十四大”之后的歷屆大會報告,乃至中共中央關于經濟改革的幾次重大決定,無論是理論觀點、現實政策主張和理論表述,都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強調市場經濟的作用。譬如,在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大會報告中的提法還是“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在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大會報告則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則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在2019年10月31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進一步明確指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由此可以認為,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輝煌歷程,以及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全社會對市場經濟的思想觀念和理論認識的轉變是同步發生的。這即是說,自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出“解放思想”號召以來,在中國的農業、工業、商業、金融和外貿體制的改革過程中,通過不斷的試錯,不斷轉變觀念和認識,慢慢認識到人類社會經濟運行的法則,并在經濟改革的實踐中不斷修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觀念;反過來也在觀念轉變過程中不斷地進行制度創新,最后在世紀之交,才慢慢形成了目前正在運行、同時也在不斷改變著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系。
第二,經過四十年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的經濟體制實際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到目前為止,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形成。中國獨特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包括政府購買,政府基建投資的招投標和建設以及水、電、煤氣的供給)已經市場化,且民營經濟已經成為GDP創造的主體;但政府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份額,相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已經很高,乃至政府調控和駕馭經濟的能力比任何國家及經濟體都強大按照周天勇教授的計算,2017年,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36.2%,總量29.94萬億(其中稅收14.43萬億元,土地出讓金5.21萬億元,社保基金5.84萬億元,國企上繳利潤2579億元,彩票收入4267億元,預算外非稅收收入2.83萬億元,各種罰沒計入預算的其他收入9403億元)。盡管北歐國家的政府宏觀稅負比中國還高,但這些國家實行的是高稅收和高社會福利政策,故可以認為世界上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和駕馭能力有中國這般大。。另一個被人忽視的現實是,盡管經過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抓大放小”的國企改制,但國企部門的資產不是在萎縮,而是還在急劇擴張和增長。按照2019年10月23日財政部部長劉昆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提交的《國務院關于2018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210.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負債總額135.0萬億元,國有資本權益總額58.7萬億元。其中,中央國有企業資產(非金融)總額80.8萬億元,負債總額54.7萬億元,國有資本權益總額16.7萬億元;地方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29.6萬億元、負債總額80.3萬億元、國有資本權益總額42.0萬億元。在金融企業國有資產方面,2018年,全國國有金融企業資產總額264.3萬億元,負債總額237.8萬億元,形成國有資產17.2萬億元。在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方面,匯總中央和地方情況,2018年,全國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總額33.5萬億元,負債總額9.9萬億元,凈資產23.6萬億元。其中,行政單位資產總額10.1萬億元,事業單位資產總額23.4萬億元http://www.chinanews.com/cj/2019/1023/8987609.shtml。這樣,按照財政部長所提供的官方數據,目前的國有資產總額為508.2萬億元。如果去掉政府行政性資產33.5萬億元不計,全國國企的總資產高達474.7萬億元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10/9b41e133a8cb45abaebbb44893a2eb55.shtml。目前,我們還無法估計民營企業的總資產是多少(有估計為165萬億元),以及中國境內外資的資產總額是多少,但是顯然二者無法與國有資本相比。經過四十年的經濟改革,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國有資本一直是、且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主體這符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尤其是從金融體系來看,商業銀行主要是國有銀行,而地方股份制銀行、民營股份制商業銀行所占比例很小。另外,盡管中國目前開設了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外匯交易市場、貨幣市場和保險市場等,但120家證券公司幾乎全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各省市大都有屬于自己的證券公司,且每個國家部委和省市政府都有自己的金融投資公司。在實體部門中,舉凡鐵路、高速公路、航空、電力、航運、礦山、石油、鋼鐵、煤炭、汽車制造,乃至大型房地產企業,大部分是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經過40年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完全形成了一種非同于英美、歐洲大陸、日本、東亞“四小龍”乃至“金磚國家”的獨特市場經濟體制。盡管從形式上來看,我們有現代公司制度,有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外匯市場、保險公司和信托公司這些現代金融機構和制度,但是因為市場的玩者(players)和莊家主要是一些國有獨資、國有控股集團與公司,這就與西方國家基本上以私有制為主的市場經濟制度完全不同股票市場從它在人類歷史上誕生那天起,本質上是私有資金在投資和買賣。。然而,一個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是,在過去四十年,這種獨特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過程,卻孕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當然,目前已經形成的以國有資本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也帶來一些經濟與社會問題:(1)國有資本的整體效率不高。按照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的說法,2018年中國經濟所創造的GDP,60%以上來自民營企業,16%以上來自外資Michael J. Enright, Developing China: The Remarkabl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ndon:Routledge, 2016).。這樣倒推下來,目前中國所有國有部門所創造的GDP大致不會超過中國GDP總量的24%。一個有著近475萬億元資產的國有部門所創造的GDP占比不超過24%,這一現象和格局本身就說明我們的國有部門還是低效率,因而應該進一步改革的。(2)以國有資本為主體的銀行和金融系統成了目前中國最盈利的行業和部門,政府和國有機構的壟斷定價(包括利率)導致銀行與金融部門的高利率;而實體制造業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融資成本過高,利潤率很低,甚至出現大面積虧損。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與其說是以國有資本為主體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在為實體部門的發展進行融資,倒不如把這個龐大的、以國有資本為主體的金融體系看成是實體制造業的食利者。另外,盡管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了GDP創造的主體,但由于主流思想觀念的滯后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部最新修訂的《憲法》實際上還沒有關于私有制的規定,只是在第十一條有以下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在這里,《憲法》還是用“非公有制經濟”指代“私有經濟”。故爾,這些年來出現的“民營經濟”這個說法,也就是《憲法》中所說的“私營經濟”和“其他非公有制經濟”。回頭看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在主要有下列各種;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的規定;第八條,“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第九條,“國家依照法律保護手工業者和其他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第十條有“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的規定。由此看來,今天在體量上占據主體地位的“民營經濟”還是一種“非公有經濟”,這便牽涉到民營經濟的合法性問題。,近幾年來民營企業家信心不足,民營企業的投資在下降,從而民營經濟成長趨緩。(3)目前以國有資本為主的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為掌握權力和資源的政府官員與國有企業高管的腐敗尋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可能,這就導致某些政府官員和國企高管尋租式腐敗的大面積發生,而這又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由于存在上述種種問題,在這樣一個歷經四十年改革而形成的現行經濟制度格局中,一個以國有資本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秩序,目前看來仍然是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的一場試驗。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經濟改革仍然是現在進行時。(2020年2月26日初識于滬上,3月15日改定。在此感謝林毅夫、張軍、陳詩一、盛松成、王振營諸位教授的評論。特別感謝林毅夫教授,他不但詳細閱讀了此稿,還提出了許多深層次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思考。我的學生張志華教授、李秀輝副教授,席天揚、孫梁博士以及陶麗君、蘇映雪等都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和建議。也特別感謝上海三聯書店匡志宏女士,她是吳敬璉老師諸多著作的編輯者,不但對本文的文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也對這篇文章的內容和歷史記述方面的紕漏提出了許多有益的修改意見。最后,特別感謝復旦大學出版社谷雨女士。作為我的諸多著作和譯著的編輯者,谷雨非常熟悉我的思想和語言風格,多次修改了這篇文章的文字和表達方式,幾乎每段都有改動,她的修改意見也全都被接收到定稿之中。當然,文中所有觀點均由作者負責。)
[責任編輯 劉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