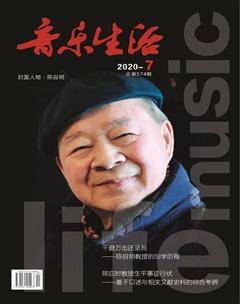千磨萬擊還堅勁
張大軍
陳自明教授以其堅韌不拔的毅力,最終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成為國內在世界民族音樂研究領域的佼佼者。作為學者,陳自明教授著述文獻多達百篇見于各大期刊,另有四本學術著作。作為教師,他培養了許多來自國內外的求學者,其中包含本科、碩士與博士研究生等。作為推廣者,他走遍全國30余省,講授世界民族音樂課程。作為田野工作者,為獲取第一手資料,他前往世界36個國家與地區調研。作為一個領導者,他曾擔任中國民族器樂學會會長、世界民族音樂學會會長,為中國的音樂事業奉獻自我。陳自明教授具有什么樣的觀念認知?何以取得如此成就?他為什么以世界民族音樂為研究對象?對這些問題的解讀,利于我們對陳自明教授學術思想的認知。筆者試從陳自明教授學術思想形成脈絡、研究視角等方面進行闡釋,以期解答以上問題。
一、時代背景下的觀念蛻變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得出的觀點也就千差萬別。作為世界民族音樂的研究者與推動者,陳自明教授的音樂價值觀不是一開始就自然形成的,在經歷思想的不斷洗禮之后,最終形成多元文化觀的過程。

著作《印度音樂文化》揭幕式現場
1932年,陳自明出生在蘇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父為清朝舉人,主管當地教育事務。父親陳章畢業于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上海交通大學前身),1924年留學美國普渡大學,歸國后在浙江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等多所學校任教,是中國電機電子高教事業的開拓者,一代電壇宗師,在電力、通信廣播和無線電工程等領域頗有建樹。母親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曾擔任過中學、大學教師,陳自明最初的音樂記憶是母親教唱的學堂樂歌。1937年中日戰爭打響,南京、蘇州相繼淪陷,民眾無家可歸,只能逃往他鄉,陳自明隨父母來到武漢、長沙等地,最終在重慶落腳。在重慶南開中學期間,他在課堂上跟隨阮北英學習音樂,第一次接觸了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肖邦的作品,學會了《嘉陵江上》《太行山上》《松花江上》《黃水謠》等抗戰歌曲,這些都成為他一生中無法磨滅的音樂記憶。在重慶南開中學高中部的兩位哥哥經常在家中演唱各種外國名歌(多選自美國出版的《101首名歌集》),對他形成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底,陳自明隨家人回到蘇州,就讀省立蘇州中學,接觸口琴。1947年在中央大學附中(高中部)學習,這時陳自明開始學習小提琴,正式走上學習西方專業音樂的道路。1949年11月他考取南京國立音樂院,在這里開始接受專業的音樂教育,隨陳洪學習小提琴。1950年6月,南京國立音樂院與另外幾所院校合并,在天津成立了中央音樂學院,陳自明隨同音樂院師生一同前往在天津的新校址,繼續自己的專業學習。
當時中國的兩所音樂學院,教學采用西方的音樂體系,接觸到的多是西方音樂或是在其影響下創作的音樂作品。在這種音樂教育體系影響下的陳自明,衡量音樂美的標準自然存在著偏向性,歐洲中心論的思想已進入到他的靈魂深處。此時的陳自明對中國傳統音樂的認知較淺,認為它是一種粗俗的、缺少和聲的單調音樂。這種思想在不斷地與傳統音樂接觸過程中悄然發生變化。1951年文藝界開展整風學習運動,次年,運動蔓延至學校,中央音樂學院全校停課,教師和學生奔赴鄉下進行勞動鍛煉,吳祖強、陳自明、金湘、郭淑珍、王治隆、陳比剛等30人到河南禹縣參加修建白沙水庫,時間長達8個月。期間,來自附近七個縣的地方劇團每天都為13萬民工進行慰問演出,表演河南的傳統戲曲。在耳濡目染的過程中,陳自明喜愛上了河南曲子和河南梆子,傳統音樂在他的思想認知中占據了一席之地,逐漸改變原先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片面看法。
20世紀60年代,過了而立之年的陳自明,思想上逐漸成熟,對問題的理解有了更加全面的考量,有了個人的創見意識。當時,中央音樂學院放映了一部安第斯高原音樂影片,陳自明為之心動,暗下決心要涉足拉丁美洲音樂研究領域。1965年是其學術思想轉向世界的重要節點,他參與了為西非幾內亞改良民族樂器的工作,對世界民族音樂的親身體驗,使陳自明的價值觀產生重要影響,觸動了他研究世界民族音樂的興趣。通過不斷與世界各民族音樂的接觸,以及民族音樂學在國內的影響,拓寬了陳自明的學術視野,逐漸形成了多元文化價值觀。1977年陳自明參加了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亞非拉音樂小組,開始研究加勒比海的鋼鼓音樂,寫有《加勒比海的音樂明珠——鋼鼓》[1]《加勒比海地區的音樂》[2]等文。1979年涉足南美音樂,論文有《秘魯、玻利維亞的民間音樂和樂器》[3]《秘魯的音樂文化》[4]等。1983年9月出訪緬甸,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緬甸是他第一次走出國門,對緬甸音樂作了詳細的調查研究。相關著述有《“萬塔之城”話音樂——記緬甸音樂》[6]《緬甸的音樂文化》[7]等;1985年前往菲律賓考察調研,《菲律賓的音樂世界》[8]《菲律賓民族音樂》[9]等文記述了菲律賓的音樂特征。1988年,率文化部非洲教育考察團,領略了埃塞俄比亞、加納、利比里亞、尼日利亞等國的音樂文化風采,在陳自明的學術研究中,印度音樂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1983年對陳自明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印度音樂大師拉維·香卡來華作表演的學術性講座,他全程陪同香卡,受到大師的啟發后開始研究印度音樂。1989年,去印度學習,歷時8個月。關于印度的研究文獻有《印度“拉格”初探》[10]《印度的西塔爾琴與音樂大師拉維·香卡》[11]等。陳自明《印度音樂文化》一書,是第一部由中國學者撰寫的印度音樂專著,填補了中國關于印度音樂研究的空白。該書的發布儀式于2019年8月在印度駐華大使館舉行,印度駐華公使魏圣賢認為該書在增進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特別的意義。每個民族的音樂不盡相同,都有其合理性與存在價值,文化的差異性與多樣性是世界音樂文化發展的基礎與內在動力。陳自明游走在世界各國中,將所見、所思、所想了然于紙面,增加了國內在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術厚重感,使國人可以窺視世界民族音樂與文化信息。
?二、國家使命下的兩次契機
作為一個博學多聞的學者,時代的呼喚與個人的品質筑成了陳自明今天的成就。他緊跟時代的步伐,抓住歷史機遇,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最終開花結果,成為該領域的集大成者。
1.幾內亞樂器改良

在秘魯學習排簫
1961年,陳自明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參于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樂器制造專業。1964年他到民族音樂研究所進行中國民族樂器改良工作。次年,民族音樂研究所(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前身)受國家文化部與輕工業部委托,與北京樂器研究所、北京民族樂器廠一起對非洲的幾內亞樂器進行改良。在所長李元慶的安排下,由王湘、陳自明、宋文杰、張祥云、朱虎雄組成的“幾內亞樂器改良小組”開始著手相關工作,大家各司其職,王湘任組長,陳自明與宋文杰負責調研工作,張祥云與朱虎雄承擔設計、制作任務。為了做好Balafon(木琴)、Konni(非洲吉它)、Bolon(琴)TomTom(鼓)、笛子五件樂器的改造,陳自明通過種種途徑去查閱資料,力求全方位解讀幾內亞的文化與歷史,這些工作為后來的成功改造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小組成員克服種種困難,改良后的樂器得到了幾內亞國家歌舞團的認可,增進了中國與幾內亞的友誼,為國家間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這次幾內亞樂器改良的經歷,雖然時間短暫,但對陳自明的影響卻是深遠的。一方面打開了陳自明的音樂視野,近距離接觸到異域的音樂文化,另一方面正是這次偶然的邂逅,促使他下定決心在世界民族音樂領域做出一番貢獻。陳自明曾專文對這次幾內亞樂器改良工作的來龍去脈進行梳理,“我有責任把這一段重要的史實記錄下來,留給后人。同時,這一段經歷對我也至關重要,正是從這時起,在民研所,我開始了對亞非拉音樂的探索和研究,對此,我永遠銘記在心……在這里,我對中國民族音樂有了真正的認識;在這里,我開始擺脫‘歐洲音樂中心論。”[12]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知識沉淀之后,陳自明開始踏上音樂的尋密之旅。從1983年前往緬甸開始,在長達四十多年的研究之路中,已經前往36個國家與地區進行調研,領略了風格各異的世界民族音樂魅力。
2.亞非拉音樂小組
1977年,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成立了“亞非拉音樂小組”。金文達任組長,陳自明為副組長,成員有林凌風、嚴安思。之后金文達與嚴安思相繼退出,俞人豪、王雪進入小組,后因林凌風調入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小組最終僅剩下三人,陳自明擔任組長。陳自明主攻秘魯音樂、鋼鼓音樂和印度音樂,同時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亞非拉音樂分支主編。美籍華人劉邦瑞教授曾在美國教授世界音樂的課程,1980年在中央音樂學院為音樂學系師生作民族音樂學和世界音樂的系列講座,當時日本音樂家岸邊成雄、小泉文夫等人也相繼來華講學,這些專家給了亞非拉音樂小組很多啟迪與幫助。為了使廣大師生接受世界民族音樂教育,音樂小組開始籌劃相關的課程。經過多年的準備與努力,《外國民族音樂》這門課程終于在1982年成功開課,陳自明主講印度、秘魯和鋼鼓音樂,俞人豪負責印度尼西亞、伊朗與土耳其音樂,王雪負責墨西哥音樂。在音樂小組成員共同努力下,該領域的研究不斷深入,這門課程在三人的努力下成功開課,奠定了世界民族音樂這一新學科在國內的基礎,不斷產生影響,遍布全國。陳自明認為:“在歐洲、美國、日本的著名大學和研究院中,都已開設了介紹世界民族音樂的課程,有些學校還開設了演奏世界民族樂器的課程。而在我國目前只有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開始設立這類課程。世界民族音樂在我國是一個急需開發、建設的新學科,全國從事這一學科工作的不過十幾人,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看來取得人們的共識和支持已成為燃眉之急。我們呼吁音樂界和有關方面的領導大力支持,創造條件,使這一學科得到較快的發展,以適應21世紀的需要。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13]陳自明覺得自己有責任挑起這份重擔,幫助中國人突破二元思想的束縛,樹立音樂的多元化認知。由此,拉開了陳自明在全國推廣世界民族音樂課程的序幕,為了擴大世界民族音樂在中國的影響力,陳自明不畏艱難,推廣世界民族音樂課程,堅持全國各地講學,奔走于國內近60所院校,在昆明、桂林、福州、三亞、成都、武漢、蕪湖、洛陽等50多個城市都留下陳自明的足跡。如2007年12月,海南大學組織“陳自明教授世界民族音樂專題報告會”,陳自明以《學習世界民族音樂的目的和方法》《印度、拉美、歐洲民間音樂賞析》為題,向廣大師生講解了世界音樂的發展史,分析了世界其他民族的音樂特點,展示了一位學者的學術思維與執著追求。2017年3月,陳自明走進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為該院師生作了兩場別開生面的世界音樂巡禮,主題為“走進世界民族音樂的百花園,欣賞絢麗多姿的音樂瑰寶”“神奇浪漫的拉美音樂,神秘奇妙的印度音樂”,專題講座在充滿魅力的世界民族音樂中圓滿結束。
三、堅守初心的不懈追求
四十多年以來,陳自明始終堅守“世界民族音樂”的初心,行走在世界民族音樂之路上,雖有磕絆,希望之花仍然盛開,不改初心。
陳自明選定世界民族音樂為研究對象,他的初心是什么?他雖沒有專門進行說明,但從他對世界民族音樂研究目的與意義的闡釋中可以知曉。“世界上不同的人種、民族對人類的音樂文化做出了不同的貢獻……對世界上不同的音樂文化有了初步的理解之后,我們才有可能客觀、公正、平等地對待世界上的各種民族音樂了……剔除了傲慢和偏見后,我們就可以按照各種音樂文化的特征來認識世界各地的民族音樂,就能發現無數晶瑩奪目、閃閃發光的音樂瑰寶,就能聆聽絢麗多姿、幾乎是無窮無盡的音響世界。”[14]世界民族音樂可以使我們開闊視野,消解片面性認知,具有學術研究價值與文化意義。
西方國家對其他民族音樂探索是伴隨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侵略成長與發展起來的,“世界音樂版圖”在西方國家已經形成。縱觀亞洲,日本在該領域的探索與經驗也是值得我們思考。近代以來,中國與日本都曾向西方學習,我們講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用主義,日本注重“開發民智”的現實主義。前者看到西方現有的思想與成果,而后者思考的是西方為什么出現這些成果,采用什么方法?[15]日本人照搬美國教育制度,開設世界音樂課程,目光投向域外。日本既有像“東洋音樂學會”、“日本流行音樂學會”等組織以研究世界音樂為主,諸多院校也將其納入研究范圍,在中小學課堂中教授世界音樂的內容,為更深層次的人才培養奠定了基礎。與其同時,JVC錄制的《世界音樂大系》在世界范圍內影響廣泛,為世界音樂的研究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鑒于以上國家在世界音樂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與貢獻,作為國內世界音樂的探索者與領先者,陳自明認為在該研究領域中應該有中國人的一席之地。

為了研究世界民族音樂,陳自明篤學不倦,四十六歲開始學習西班牙語,此時的他因心中有了追求的目標而充滿喜悅,在未名湖畔高聲朗讀,他要將荒廢的時光用自身的努力彌補回來,為的就是實現對未知領域的探索。陳自明認為:“每一位從事這一學科的人必須看到目前暫時的困難,要有克服困難、堅持到底的勇氣,以極大的熱情從事這一21世紀中國新的音樂啟蒙運動。在我看來,20世紀的音樂啟蒙是了解、學習西方音樂,21世紀的音樂啟蒙是了解、學習全球的音樂文化。它必將極大地開闊人們的音樂視野,為中國音樂的繼承、發展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16]在中國音樂學院紀念安波教授誕辰一百周年研討會上,陳自明建議該院要秉承初衷,以中國民族音樂和世界民族音樂為辦學主線,形成自己的特色。[17]在這樣一個各民族交流頻繁,溝通順暢的世界環境下,我們應該擁有一種責任感與使命感,加強對世界民族音樂的研究,發出我們的聲音。

在西雅圖演奏鋼鼓
若從現代學術意義的角度來看,我們對世界音樂的關注還是較為滯后的。最早介入該領域的當屬王光祈,起始時間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范圍主要限定在包含中國在內的東方諸民族音樂與西方音樂領域。與其不同的是,陳自明認為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在國內都有一批學者在關注,因此,他暫將中國音樂與西方專業音樂放置一邊,將目光投向亞洲、非洲、美洲等地區。鑒于中國的實際情況,既要加大對世界民族音樂的研究力度,也亟需從教學的層面推廣世界民族音樂,從而培養我們的多元認知。因此,陳自明立足于本土視角窺探世界民族音樂,從學術研究、教學推廣兩個實踐層面展開,并且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當下世界音樂的中國實踐基本表現為兩種類型,即‘中國國情下的世界音樂教學與‘中國視野下的世界音樂研究。如何在當下以西方音樂教育體系為主的各類專業音樂教育中實現世界音樂課程的意義,以及如何通過世界音樂的各類研究來完善中國音樂學學科發展及進行學科反思,這些顯然已經成為國內相關學者越來越關注的問題。”
陳自明教授雖近鮐背之年,但其身體依然矍鑠硬朗,思路清晰,聲音堅定有力。在與陳自明教授接觸的過程中,給后輩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對世界民族音樂的執著與追求,正是這種孜孜不倦的探知欲望感染了一批批年輕后輩。
注釋:
[1]陳自明:《加勒比海的音樂明珠——鋼鼓》,《國際音樂交流》,1997年第6期。
[2]陳自明:《加勒比海地區的音樂》,《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
[3]陳自明:《秘魯、玻利維亞的民間音樂和樂器》,《樂器科技》,1978年第4期。
[4]陳自明、景深:《秘魯的音樂文化》,《國際音樂交流》,1996年第4期。
[5]陳自明、張雷:《“萬塔之城”話音樂——記緬甸音樂》,《中國音樂教育》,1997年第6期。
[6]陳自明:《緬甸的音樂文化》,《國際音樂交流》, 1996年第2期。
[7]陳自明:《菲律賓的音樂世界》,《中外文化交流》,1994年第1期。
[8]陳自明:《菲律賓民族音樂》,《國際音樂交流》,1996年第3期。
[9]陳自明:《印度“拉格”初探》,《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3年第3期。
[10]陳自明:《印度的西塔爾琴與音樂大師拉維·香卡》,《樂器》,2003年第6期。
[11]陳自明:《一段不應遺忘的重要歷史——記幾內亞民族樂器的改良工作》,《中國音樂學》,2014年第2期,第55頁。
[12]陳自明:《世界音樂文化的多元性》,《民族藝術》,1997年第4期,第10-11頁。
[13]陳自明:《研究世界民族音樂 共享全球音樂資源——在第二屆世界民族音樂研討會上的講話》,《人民音樂》,2006年第2期,第17頁。
[14]楚漁:《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頁。
[15]陳自明:《我學習和講授世界民族音樂課程的經驗加體會》,《人民音樂》,2017年第4期,第22頁。
[16]陳自明:《我的希望和建議》,《中國音樂》,2016年第3期,第5-6頁。
[17]胡斌:《“世界音樂”需要中國敘事》,《音樂研究》,2014年第1期,第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