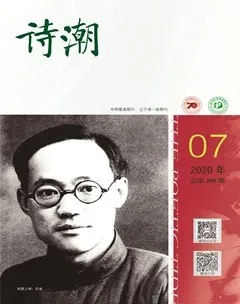日子被時間布置成一種形狀 [組章]
梁永周
教堂與河
天津路一直延伸到無名河才轉了彎,它總是在夜色之中對我的思想動手,帶著生活的回聲,以及我分泌出來的羞澀,進行一次討伐。
伴著晚風的雜音拖動腳步,一切都清涼了。
我主觀認為教堂處在河水中央,我不靠近,亦靠近不得。你得想象主祭臺和合唱席之間的紅地毯,不,我們的禮俗應該說有金燦燦的配飾加入,或者是滿足一切貪婪、欲望的道具,比如隨從、救贖、保佑、懺悔之后的豁免等,從小玻璃投進的光,居高臨下。
那塔尖一定朝向虔誠者的心臟,若換上彈藥,即刻斃命。不對,這塔尖的威力要大于這假設的一切。
夜色之下,你看得清河水的靜謐,正如此,我們被自我的信仰脅迫得小心翼翼。
教堂的鐘聲,馴化過的河水,應該足夠抵抗風波。
春風說
一直不斷有人死去,我是知道的。他們的名字被集中收錄在大地上。
一個早春的正午,是沒有人選擇跟陽光對峙的,因為那時它已足夠熱烈,那時我已足夠欣然,感念春風吹走一切,感念陽光所照過的每一種生活,至少是坦然而過的。
突然之間,蒲公英奔向我,我像極了一個假扮童年的傻子,一直追著風奔跑。
春天告訴我,一定要離耕地近一些,就像那株草一樣,潛伏進命運。
青山依舊
在眾多等我們的角色中,只有青山依舊。
從離開夜空中的星星與月光中,我們成就了一種逃離的夢想。又在陽光與路燈之下的背影里學會懺悔。我們每天的早餐都可以加一顆雞蛋,可是四點鐘混亂的雞啼沒有了,為此我們興奮,可以與知己分享的那種興奮。你一定要等到朋友從笑聲中變得沉默,只有這樣的甄別,才能判定友誼。于是笑著笑著,就產生了一種怪異的想法,從夜里的失眠開始,編織救命的稻草。
你可曾患過時光的炎癥,反復,久治不愈。那些無關痛癢的、發炎的往事,是不是糾正我們的得意。我們身中光陰的毒,如是才有了生活的嘆息,以及人陪同懺悔生長出來的善良。
在等我們的眾多角色中,大部分在往后退,最后都不見了。只有青山依舊,蒼郁得讓人有了想哭的歡喜。
日子被時間布置成一種形狀
日子被時間布置成一種形狀,所以我們不可以有一種情緒。
這個春天死亡如此密集,像是模仿雪花降落一樣。所以,我想跟孩子們交談耕種的愿望更加強烈。春耕,我們從翻地開始,所有的種子已經在深冬做好反省,我們需要把自己的忠誠一并埋進土地,深淺一定要適宜,所有的肥料一定要保持距離。
是啊,我的孩子們!我僅有的耕種經驗一直都未喪失,所以你們長得很好,你們如此地受到他人的褒獎。可是,我總覺自己的言辭羸弱,不足以讓你們舉一反三。只有真實地擁抱過土地,才算得上歷經,才能夠根深蒂固。
日子被時間布置成一種形狀,所以我們都必須遵守道義。
這個春天顯得過于遲鈍,雨水過后,所有的植物都還沒有茂盛的打算。我們要分配好自己的體力,分別完成每個時辰的走步。人生迢迢,如何保持仰望藍天的習慣呢?
一次起夜,偶然與天空的繁星對視,一定不要淚流滿面,不要給自己如此機會。你要受得住初如來世的凈,便不會有多余的流水沖垮你的眼眶。
日子被時間布置成一種形狀,所以我們要始終如一地熱愛。
不要在一個雨天想念陽光,同樣不可在陽光明媚之時懷念雨水,若是修得怡然自得,我們便可以始終如一地愛下去。不管這個形狀如何包容,我們都要用心地去裝飾。正如土地中的每一粒塵土,都應該讓我們足夠重視。
乘風而去
坐進春天的陽光里,乘風而去。
你一定能夠聽到童年里的流水聲,那隨風搖擺的草綠,以及陪伴過你的每一件被遺棄的東西。我們曾經假設過一塊石頭的角色,曾經把很小的自己交給婚姻,可是等你長大的時候,總是把那些欣喜的事情想得很難,難到寸步難行。
十幾棵樹就可以成為我的森林,黃昏的時候,飛鳥一下子多起來,那樹梢上的一切拴住了我所有想象,包括高飛。
把很長的時間放在凝望藍天這一件事情上,浮云變幻,所有的猜測都讓如今的我心生艷羨。
坐在春天的陽光里,乘風而去。
空空山谷
站在我家的屋頂就可以看見四周群山,它們沉默、寂靜。
黎明和黃昏的時候它們美得讓我想了又想,我總是很早起床,又很晚吃晚餐。我把最容易消失的那種短暫給予此種美好。
夜深之時,我會多疑到替一座山谷感到寂寞,輾轉反側。
一切都睡下的時候,山谷啊!你可想念過那些因風走散的泥土?
空空山谷,我登高再也不敢喊,是怕那回聲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