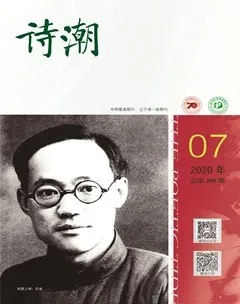草木令 [組章]
鮑偉亮
黃昏的故鄉(xiāng)
村莊像只被掏空的獸。
犬吠三聲之后,便只剩下風聲——肆意切割老邁的骨頭。
雀鳥飛去了更遠的地方。
童年的白楊林,被新開鑿成寬廣的河流。
此刻,晚霞映照著南河,故鄉(xiāng),又刮來一陣北風,那些童年的故事,風干成獨屬于一輩人的童年。
屋后的幾株老槐,咳出多余的炊煙,突兀地想起:久別村莊的那些身影。
生命本是一間藏有光亮的屋子,屋子有燈火,失去便成了常客。
在故鄉(xiāng),冬天著實是一場偌大的煎熬。總有人熬不過去,總有人在三百多個日子里埋葬于東山,總有人無法收到除夕夜的祝福,總有人意欲抓住那些瑣碎的時光……想來,唯有歲月能教懂未歸之人,如何不言不聞地永別。
唯有那一望無際的天,還有參差的皚皚白雪,愿意陪同日出日落長久守望著那個炊煙不斷瘦去的村莊。
所謂一眼萬年,就是金玉質地的銀杏葉,一夜落盡。再回首,徒留下光禿禿的枝干,如同鐵面無私的守衛(wèi)般,固執(zhí)地與時光對峙。
明日,牧羊人的長鞭依舊會響起在晚霞映照的南河旁,村莊,還會是一個北風吹刮的障礙物——燈火,不知疲倦地燃燒……
東山小記
紅瓦房遙望著東山。
東山上的土饅頭早已荒草雜生,除了碑文履行著自己的職責,他們,恍若不曾路過山下任何一個生命。
即使,生命總會以一種特有的方式延續(xù)下去,記憶卻是抵不過遺忘。
冬日里,太陽的每一次升起都是一次宣判,沉默才是最穩(wěn)妥的守望。
桃枝皈依大地,流淌著土地一般粗糲的血液。它們會感知歲月的印記。一里、兩里,散落滿山的墳墓下,粗糲的血液,逐漸氧化變質或是分崩離析,他們的曾經便已不再重要。他們也會是村莊的未來時。
時光是一條無法回頭的路,走出去的人多了,村莊終是老邁失守,東山,逐漸將其吞沒。荒涼,是蒼老的歸宿,日光、星光、月光,一切都會在目光中老去。
唯有一場大雪,會給予柴扉短暫的新生。因為茫茫的白,一切便都忘了。
如果不是一望無際的雪白,便將是樹皮的灰、墻皮的灰、土地的灰、麻雀翅膀的灰,整個村莊如同空氣凝固般的灰蒙蒙的灰。
當日光打破這灰蒙蒙的沉寂——
一束光,照耀生靈。對有的人來說,這是一天的開始,對于另一些人來說,則是一生的結束;一束光,照耀靈魂,有的逝者走在不曾來過的路上,有的逝者則喚作了無名。
東山越發(fā)龐大;村莊越發(fā)沉重。
別夢寒
月光照亮幽徑,路上,我們想著各自的事。
年輪教會樹木生長,年齡教會命運釋然。一條路,沿著既定的路線,便可以一直走下去。順行、逆行,乃至交織、停頓,唯有碾壓成膠片才具備形體,否則,便是一陣從未誕生過的風。黑是盡頭和源頭,路燈已冬眠,黑暗中掩藏著隨時揭露降世的江湖。
落葉滿地,很多錯過都是這般,悄無聲息。
夜,一下子便寂寥了。仿佛是打開一冊書,再閉合,所有的人與情都已泛黃,甚至是卷起一角。
路,越走越窄;人,越走越少。越來越適應孤獨之心,越來越懷念一把生銹的鐮刀、一只年邁的犬,又或者是墳墓中的某個人。
所有的相遇都將在相忘中結束。終于,西風吹散了一只,意欲歸隱的燈。
一片落葉棲于發(fā)絲,我想起了泛紅的木槿,想起遠方車輪軋過道路的低沉,原來,對與錯、失與得,都是上帝的安排,并在遙遠處暗暗回響。
所以,酒館永遠不會缺少朋友。
酒是一味藥,麻木隔閡已深的靈魂。一杯酒,清澈到可以對話,可以與淡去的淚交心,可以偶爾荒唐,忘記車水馬龍的大路上不認識一個人,亮起的路燈如同造物的瑕疵。
懷念起一排梧桐,一山春雨,一群漫無目的游走的身影。
月光,還在照耀漂泊的城市,還有,那一萬家同樣寂寥的燈火。
草木令
凌晨的汽車,奔向一盞預留的燈火。
今夜,我在濟南,守著賓館的玻璃窗心無所依。凝望車輪碾軋而過的水洼,月光破碎,溢了出去。
孤獨的路燈,正與梧桐對視。
昨夜,在生命的冬季,梧桐迎來了一場雨。生與死的間隔,便成了一場遲到多日的雨。
草木一秋,跌跌撞撞,兜兜轉轉,正如這人間所有的相愛都會在相忘中結束,此生,便只剩下自己,與自己和解。
此時,它,與它們,生命原本傲立的頭顱,被凜冽的寒風踩在腳下。如果此夜死于枝頭,路燈便是最后送別的那一把大火。
我看到:蜷縮的黃葉,爬上了更多的銹跡,嶙峋的骨架,已然喪失鋼鐵的魂魄,它們垂老枝頭,狀若狂風撕扯后的棉絮。
失去是生命的最后一課。但,故去的生命不會感知到失去,也不會帶走一瓣杏花。
明日,殘葉或將歸根,斷去最后一分聯系。也或許余下稀缺而又尖銳的信仰,執(zhí)著于等待一場大雪,一如看慣的往來行人霜發(fā)滿頭,經歷過生命輪回的儀式,再落地,勾兌遺忘。
時光的齒輪還在有條不紊地滾動著,不偏不倚。
沒有亙古不動的星,也不會有恒定的前行軌跡。結束的無法擺脫結束,即將開始的正在醞釀開始。
之后。燈,換了一個城市閃爍;路,落滿了陌生的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