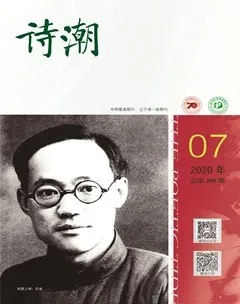那些從你嘴里說出來的雨 [組章]
紅線女
聽坂本龍一的《圣誕快樂,勞倫斯先生》
起初是喧囂的,夾雜著悲鳴,像一只巨鳥,在夜空里狂奔。
慢下來了。是的,像窗外的雷雨聲,不知不覺地慢下來了。
天好像亮開了,壓頂的烏云好像在移動,從我,移到了另一個無聲的角落。
風鈴,好像也響起來了,在屋檐邊,在山坡上,在沒有你的梧桐樹下邊。
傾訴開始了。
吉他嘶啞,像在訴說著生命永遠無法選擇的宿命和悲傷。
成為陌路,就是我們的宿命。以謊言開始的愛,能堅持到什么時候呢?
人性的純粹和復雜,就在其中。
真善美的追求,自尊,自愛,與矜持,也在其中。
愛的迷戀,情欲的糾纏,欺騙與否認,對我們必然的歸途的回避,對漂亮外表下某顆心變得虛假后的碎裂和痛感,都在音樂里,清醒地疼著,糾纏著,漸漸變得激烈,激越,像爭吵,像戰爭,充滿濃濃的火藥味兒。
雷雨聲漸遠。
暴熱變成了狂躁,變成了傾訴,變成了傾聽,變成了硝煙彌漫,不信任感,充斥了整個夜晚,空氣似乎沉重得無以承受,一切都變得虛無,變得遙不可及,即使伸出手去,也什么都抓不住。
灰燼。是的,音樂的殘渣,空氣的碎片,你往日的容顏,都在這個吉他聲里,不斷重疊,不斷閃現,讓人應接不暇,心力交瘁。
就像面對死去的人,留下或深或淺的記憶,所有愛的美麗和痛苦,化成了一句“圣誕快樂”,然后漫天飛舞起潔白的雪花,沒有大雨,沒有狂風,只有密密麻麻的雪花,不斷飄落于這個世間,每個干凈或者不干凈的角落。
我無法祭奠這個夜晚。
就像要經歷很多的大雨之后,才能抵達圣誕;或許,很多的大雨之后,我們也不會有圣誕快樂。
就像你走了之后,我的生命只剩下了九分之一。
而我,只有訴說,也只能訴說。
對著自己。對著黑夜。
那夜的雨
我又對你說決絕的話了。就像烏云壓低了六月的天空,不到黃昏,你就下起了雨。雨點密集,敲打著車窗,敲打著長長的電話線,然后跑出來,落滿了大地。
我們是焦躁的。即使那么多的雨落下來,也沒辦法把我們變得滋潤一點。我們被一些看不見的陰影籠罩著,被一些看不見的手卡住了脖子,想對著對方呼救卻沒有力氣。
其實,我喊了,你也喊了,我們都喊了。天空被壓得很低,它蓋住了我們的聲音,蓋住了我們的絕望,也蓋住了彼此的信賴。
我是聽見你了的。一直以來都聽見了。
就像我看見百合花謝了,紫薇花接著開,然后是蘋果花,槐花,它們一個一個次第開放在你面前。不一樣的花香,不一樣的色彩,還有不一樣的身姿,回應你,輝映你,想讓你從陰影里走出來,快快好起來。
而雨,總在你身前,身后,不經意間,下起來了。而且越下越大,淹沒了我的花,淹沒了我,和我們。
該怎么結束呢?
傘似乎沒有用了。
那些被雨水淋濕的花,有的枯萎,有的落淚,有的蜷縮著,有的隨風而逝,嬌艷和風華遠去,就像我們的傘,如今已經遮不了我們了。
現在,雨似乎更大了。透過十八樓的窗戶,我仿佛看見你的影子,就在馬路對面的路燈下一晃一晃的,那微微抬起的左手,好像正在抹眼淚。
百合花
凌晨兩點的時候,大風淹沒了整個夜晚,窗簾飄起來,灌滿了呼啦啦的心事,在屋子里飛起來,像沒有靈魂的人,又像長著翅膀的幽靈,一會兒上下移動,一會兒左右沖突,擠滿了整個房間。
玻璃窗是什么時候破碎的,我沒有注意,風聲密集的時候,我一個人躲在黑里,一動不動,一動不敢動,連碎玻璃片落在地上,也沒看見。
雨進屋來了。
他大搖大擺,帶著說不清楚的表情。他先淋濕了陽臺上的布娃娃,接著沖向那盆百合花。早已在大風中破碎不堪的百合花,她竭力捂住自己的臉,那雙哭得紅腫的雙眼,你永遠也看不見。
雨真的進去了,他毫不客氣地打濕了她的臉,她的葉子,并把深深的水,留在了她的身上。關于一場大雨和百合花的故事,似乎由此謝幕了。
而我的百合花還是很白。即使破碎了的花瓣依然很干凈。那些留在她身上的雨水,變成了很多很多的痂。
那些從你嘴里說出來的雨
世界都在哭泣,大地成了游泳池,很多人成了不會游泳的魚兒,被無數浪頭,被無數倒塌的房屋和謊言,打翻在水中,奄奄一息。
你一直在描述雨。
描述那些被風吹來的透明的雨,生病住院的黑色的雨,不能描繪形狀的紫色的雨,黃色有點像陌路的雨,紅色有點像愛情的雨……
這些從你口里說出來的雨,都有高高的個頭,俊秀的臉龐,明亮的眼睛,和能說會道的嘴巴,這些聽起來漂亮的雨,真的有一大段時間迷惑了我,讓我只想站在雨里,和你一起。
你一直給我描述的那些雨啊,很呼嘯,很虛無,把整個夏天弄得也很虛無。
我踉蹌了,我摔倒了,我嘔吐了,我流血了,我甚至想到了死,真的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死。
可你還在跟我說雨,一次又一次跟我強調,那些雨都是紅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