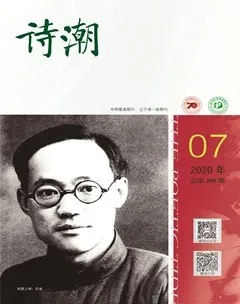偏信流水式的勝利 [外一章]
牧雨
1
風(fēng)還沒到來,木槿在努力開花。
時間流淌的聲音,隱于石,隱于灌木,被吹回的云,用葦?shù)颜f話。
之前,我不相信山中藏有如此遼闊的憂傷。柿子離開枝頭,從這只手轉(zhuǎn)到那只手,被反復(fù)捏,直到無人問津,沒有一本書描述過這一細節(jié),或源于秋光,使嘴和胡須大白天下,還有一種可能是宿命,評頭論足的風(fēng),成就了這一斷章。
知道真相的人,提著竹籃,駝背往回走,經(jīng)過一大片黃菊,進到虛掩的門。
這時,葡萄枝在繼續(xù)尋找水和泥土,柚子為了一點糖分在枝頭苦修,對于它們的苦衷,我做不到守口如瓶;魚在淺水行道,波紋被誤認為花,刻在懸崖;牛在河灘,不諳時勢,啃著老草,沒人度化它們的孤獨和憂郁。
而我,難以釋懷的是在三月的一首詩,美化過它們的眼淚。
2
風(fēng)從窗口傳來,帶來飛鳥穿過夜的聲音。

李偉《關(guān)羽和張飛》
有葉在落,有水在流,有人在行走,這些被時間驅(qū)趕的靈魂,不悲不慍,一步步隕落自設(shè)的圈套。
我想告訴你,三月二十一日,已被我譯成墓志銘。那時,水豐,鱗錦,石梯沒有猛漲,陳列著理性、感性的空氣,還有色彩斑斕的笑聲,自上而下。
那時,鳥在我們周圍游來游去,叫聲落在桃樹的夾縫,第一只蝴蝶從你眼里飛出,第二只嗅著你身上的花香,當(dāng)你側(cè)過臉看我,第三只蝴蝶棲在你肩頭。
無法簡化的東西,像風(fēng),像陽光,成為嗅覺的回憶和財富。
帶著遠方散步的人,從緩慢、柔軟的道路,到慵懶、平和的河岸,為了上乘的山水、植物以及鏡外人,養(yǎng)活指頭、嘴唇。路過我們時,牽著的手依舊沒有松開。
有時,得信流水式的勝利。
3
鳥散之后,銀杏葉就黃了。
樹下空曠,被一堆婦人占據(jù),有人說,這個季節(jié)葉黃是土質(zhì)不好,又有人說,是雨水過多,盤踞公共場所,淹沒了新舊不一的輿論。
不過,我倒從被污染的思念,學(xué)會用話語取暖,學(xué)會跟隨那款狂草,處置余下的時間。
青棗可忘記花朵,紅心柚可忽略枝頭,這是時間的側(cè)面。雪中送炭的人在路上,旅途雖有些擁堵,臘月初八應(yīng)該能到。不必為營養(yǎng)不良的石頭,消化不好的柳樹,偏信中二、潮南、腹黑、二次元之類的詞匯,偏信一本沉靜的書,可以祛權(quán)利之毒,度物質(zhì)之劫。
而我可安然在屋頂,種植冰霜,在樓上聽雪:有幾根光線逃走,余下折斷和跌落的雨聲,這是冬的插曲,不會攪碎那雪的象征性。
夜聽壁上鐘,想懲戒自己,可以從多層黑夜,遷斜月,或追究月光的籍貫,包括前科。
有時,謊言也很有張力。
有一種誘惑,是幻聽秋意
1
時節(jié)的開始和結(jié)束,植物先知。
山竹依舊共舞,不接受任何詰問,苦楝樹停在不知名的空中,守著風(fēng),也守著自己的果實。
鐵匠鋪里,還有人在打制鐮刀、鋤頭,退下來的老村長,蹲在反復(fù)抵達過的村口,聽著這單調(diào)的敲打聲。
當(dāng)想著扁擔(dān)卸下水桶,水牛失去耕地,忍不住咳嗽,一只失蹤已久的鷺,從芭茅叢飛出,落在視線之外的稻田,之后的四野像十月的鳥巢,裝滿逐漸變黃的寂靜,某些曲折的歡叫,尚存余溫,被編織山的深處。
——幻聽秋意,本就是致命的錯。
2
四川鄉(xiāng)下的九月,天空倒也清曠,有風(fēng),無帆,無所謂把疼痛,轉(zhuǎn)讓給遙遠的光陰。
晚歸的人們拖著霞光味的影子,在河水中淘洗腳板,對話里會涉及“我們這里還有魚”之類的話題,心境與空氣間,會穿插一些綠蕪與光影。
不用從指縫里看時間的肥瘦,每一杯水不再那么淘氣,從上谷到灘涂,經(jīng)歷了古風(fēng)、磐石,然后是木瓢、竹籃,最后抵達歡喜的桌面。
視力好的人,能從此見到歲月的漣漪,偏離命運的預(yù)言。
——這種低海拔的樂趣,只有圖片,沒有文字說明。
四川鄉(xiāng)下的九月,河水只負責(zé)流動。
分走山村一部分雞鳴犬吠,無所謂激蕩、回旋和交匯。
不計得失的魚群,經(jīng)過清淺的九月,有的被趕進竹篩或舊報紙,與過期的新聞一起,死于斜陽。這是視覺的敗筆。
搗衣的女人,笑聲是粗野了一些,倒也清澈,沉默已久的小山跟著笑出聲音。
這時,水聲、倒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超越了反復(fù)講述的關(guān)于狐貍的故事,以及玩偶般的神。
——碰上不忍心著筆的結(jié)局,是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