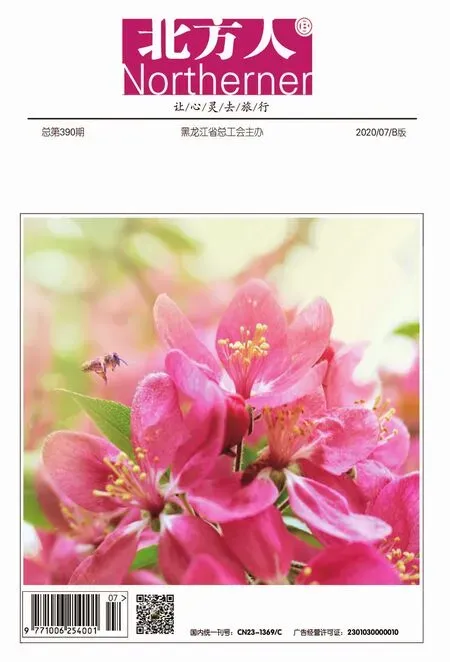仰望群星筑夢未來
演講者/吳 季

大家知道在兩千年前,希臘的科學家也好,古埃及的科學家也好,中國的科學探索和科學觀測者也好,對宇宙是有很多認識的。但宇宙是非常非常復雜的,我們到現在還有很多東西不了解。
我有幸在1985年的時候,被送到了歐洲空間局去學習。大家知道哈雷彗星每76年回歸一次,就是每76年會飛到離太陽最近的地方。為了1986年回歸,歐洲空間局就研制了一個衛星計劃去探測哈雷彗星,叫“喬托”。
“喬托計劃”傳回來的圖像最開始是個小亮點,然后慢慢越來越大,越來越大。探測器離彗星最近的時候,大概只有幾百千米。在這之前,沒有人知道彗星是個什么東西,它為什么會拖個彗尾,這次探測就把這些問題全部揭開了,大家心情都很激動。
你想,作為一個年輕人,當時我才二十幾歲,你就感覺人類在探索自然的過程當中,這樣一種不斷在發現的感覺真是非常好。但當時我們中國沒有科學衛星,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講,我就覺得空間科學太吸引人了。我們仰望星空,必須要有技術手段。所以探測器這些探測結果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觸動。
我還是想跟大家講一講,為什么中國一定要搞科學衛星呢?有很多人都說,這個科學它也不能用啊,你發現了那么多東西,你們是挺感興趣的,但是對國家有什么好處啊?
恰好我們現在在希臘,我們回想一下,兩千多年前,三千多年前,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阿基米德,這些科學家思考天空的時候,思考宇宙的時候,也沒有想到要用什么,對吧?我們中國歷史上也有過很多早期的發現,中國是最早記錄太陽黑子的國家,哈雷彗星的回歸中國連續記錄了28次,一直到1910年。中國還發明了指南針。在明代初期,我們是最早派船出海的。鄭和帶著一個非常大的團隊,當時中國的航海技術是全世界最高的,可以一直走到非洲的東海岸。那為什么當時的中國人也做一些基礎的探索呢?也看天呢?就是因為當時中國還是世界上比較富的國家,國家有錢,就有可能資助一些這樣的基礎研究。你說它沒用,是沒用,但是如果我們只局限于有用沒用的話,就不能代表人類來做事情。
中國現在已經很富了,是全世界GDP第二大的國家。這樣一個國家,你能不為人類做些探索嗎?
中國現在的高鐵是全世界最長的,高速公路是全世界最長的,鋼產量是全世界最多的,互聯網的用戶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看看我們現在的科學知識,我們中學的課本,大學的課本,里面出現的這些理論的名字,從阿基米德、歐幾里得開始,全部都是歐洲人和美國人的名字,沒有中國人的名字。難道我們不應該做些貢獻嗎?如果我們做些貢獻的話,在基礎科學做出突破的話,一定要有重要的工具,那么放衛星就是其中一個。空間科學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做基礎科學的突破。
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在做基礎研究,都在發現,所以基礎科學的問題、空間科學的問題一定是全世界的合作。
單對歐洲來講,我們和歐洲空間局建立一個對話機制,每年對話一次,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咱們能不能共同做些什么。我們從“雙星計劃”以后討論了10年,一直到最近我們才確定再跟歐洲空間局聯合做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有個很好聽的名字,叫“SMILE”,這個“SMILE計劃”是想把一個X射線的照相機放到太空中去,對地球的磁層進行成像。
這個計劃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一個最緊密的合作,我們緊密到什么程度呢?這個衛星有兩部分,科學儀器的部分由歐洲來負責,服務的部分由中國來負責,然后衛星做好了以后再拿到歐洲來做實驗。做完實驗以后放到一個歐洲的火箭上去,在南美的庫魯發射場發射,所以就變成了一個緊密合作的空間計劃。
這樣的計劃,我們希望在未來進一步地推動。希望到2030年,我們國家的科學衛星能夠產生最好的結果。那個時候,我們的年輕人再讀教科書,可能有一些基礎理論的最新發現是以中國人的名字來命名的,這就是我們現在工作的目標。
我帶了幾本書,《尋找暗物質》,執筆的這個人是新華社的一個記者,她不是搞科學的。這個記者到了我們發射場的實驗隊里面,跟每一個做儀器的人去討論,直到把她說懂了,她理解了,才寫了這本書,所以這本書非常好。
第二本書叫《Calling Taikong》。這個Taikong就是中國的太空,就是space,這個字就被所有的英語國家接受了。那么calling Taikong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去給太空打個電話也好,去呼喚一下也好。我們現在剛剛起步,要想理解太空到底是什么,必須做一個長遠的規劃,這個規劃的主要目的,就是讓中國人也參與進科學探索當中。我想在座的年輕人肯定也會非常感興趣,如果你們感興趣的話,歡迎你們加入到空間科學研究的隊伍中來。
我今天的講演就到這兒,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