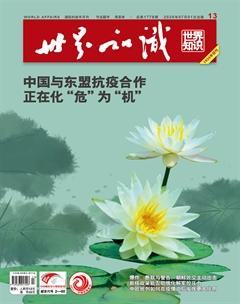新核政策能否助俄化解軍控壓力
代勛勛

俄羅斯“鎮國神器”“白楊”-M移動式洲際戰略導彈系統。此照片攝于2009年5月9日俄慶祝衛國戰爭勝利64周年閱兵式上。
6月2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總統行政令,頒布《俄聯邦核遏制領域國家基本政策》(以下簡稱《基本政策》),取代了十年前制定的同類文件(內容從未公開),首次以公開形式宣示俄方核政策,體現了俄對當前危險威脅的新判斷,是對美方核政策改變的回擊。
新核遏制政策的變與不變
總的看,從國家實力和安全環境出發,新核遏制政策與以往相比具有連貫性和一致性,其防御性質沒變,將核力量維持在足夠保障核威懾的水平即可;遏制形式沒變,以擁有和動用核武器作為威懾手段;根本目的沒變,遏制對俄及其盟友的入侵,維護國家安全。
但新核遏制政策并非了無新意,其發布的時機、新增的內容及展示的姿態耐人尋味。
首先,面臨形勢變了。近年來,國際軍控體系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美俄在軍控領域沖突不斷。長久以來,美國對現有軍控體系持懷疑態度,認為該體系對美國的限制程度遠超他國,先后退出軍控條約,抬高談判門檻,并持續對俄戰略施壓,使俄感受到國家安全層面的強烈威脅。此時俄頒布《基本政策》,針對美國的用意十分明顯。
其次,用核門檻變了。《基本政策》增加了兩種俄方使用核武器的情形,即“影響俄重要目標使其核反擊能力遭到破壞”和“使用常規武器使俄國家生存面臨威脅”,俄不僅在遭受核打擊時可使用核武器,甚至當俄重要目標如交通、能源或通訊系統遭到大規模常規武器打擊或網絡攻擊時,也會觸發俄方核反擊。也就是說,俄方對常規武器打擊實施核反擊有了法理依據,同時可依據主觀意愿自行決策使用核武器的時機,核門檻大幅降低。
第三,威懾姿態變了。通常而言,戰略核威懾的有效性取決于實力、決心以及讓對手知曉的程度。《基本政策》清晰展示了俄在核武器領域的威懾意圖和用核想定,俄方在具備強大核實力的前提下,公然強調己方實施核報復的必然性,威懾意味更濃。
軍控危局中的大國角力
美蘇在冷戰期間簽署的《反導條約》《中導條約》和《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是國際軍控體系的三大支柱,基于此建立的軍控機制也是美俄戰略穩定的重要保障。然而,隨著美俄間現實利益的日益沖突和戰略互信的逐步喪失,雙方在軍控領域的角力愈演愈烈。
第一,競相改變用核理念。近年來,美逐步改變核政策,提出全球快速打擊理念,允許使用洲際彈道導彈作為常規武器對他國實施打擊,不將使用低當量核彈頭視為核戰爭;出臺《核作戰》文件,認為必須改變核武器運用范圍;發布《非戰略核武器》,模糊戰略核武器與非戰略核武器的界線,甚至揚言重啟核試驗。
冷戰后,俄整體軍事實力雖有所下降,但在“三位一體”核力量和高超聲速導彈上的投入從不松懈,戰略武器現代化比重逐年提升。1997年起,俄著手研究老舊核裝備的更新問題,加緊研制高超聲速武器和新一代反導系統,大力發展其他高技術武器,力爭在常規戰力弱于美國的形勢下,以核武器實施“終極對抗”。
第二,推進核武器小型化戰術化。退出《中導條約》后,美立即宣布試射陸基巡航導彈和中程彈道導彈。對此,俄羅斯當即回應,如果美國進行中短程導彈系統的研制,俄方也將“被迫”全面研發類似的武器。除了在反導和中短程導彈問題上的較量,雙方還不斷推進核武器小型化、戰術化和隱身化。小型核彈頭體積更小、重量更輕、運送難度更低,可以無聲無息地執行外科手術刀式的“拔點斬首”行動,打擊精度大大提高。俄羅斯不斷推進小型核武器試驗,美國則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部署搭載小型核彈頭的潛射彈道導彈加以對抗。
第三,爭奪法理和輿論高點。針對軍控違約問題,美俄間“口水仗”不斷。美國將其退約歸咎于俄羅斯未依約履責,俄方則予以針鋒相對的反擊。如,針對《開放天空條約》問題,美認為俄多年來一直違反條約規定,限制美國飛越俄鄰國格魯吉亞和俄在波羅的海沿岸的飛地加里寧格勒;指責俄利用飛越美國和歐洲領空的機會偵察可在戰時襲擊的美重要基礎設施。而俄方則不滿美限制低空飛行(尤其是在華盛頓地區),削減俄在夏威夷島上空的偵察飛行范圍等。針對此次退約,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明確表態,美國經常指責別國破壞條約,以此為自己退約尋找借口。
激進態度背后的克制考量
今年,俄外有美西方戰略擠壓,內有權力格局調整,加之新冠疫情形勢日趨嚴峻,可謂內外交困。此時頒布新核遏制政策,貌似態度激進,卻也暗含謹慎克制的戰略考量。
近年,美對俄遏制態勢愈發明顯,極大地擠壓了俄戰略空間。不斷在俄周邊地區增加軍力部署,先后進駐波羅的海地區和波蘭,借口烏克蘭局勢惡化實現在烏駐軍常態化,在羅馬尼亞修建陸基宙斯盾系統,甚至意圖將部署在德國的B61核彈轉移至波蘭,大大加強了對俄的預警和打擊能力;實施有針對性的軍事行動,出動B-1B戰略轟炸機闖入鄂霍次克海內海領空,頻繁出動艦機對俄偵察,使美俄軍事力量發生正面沖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綜合國力差距甚大的情況下,俄方不得不繼續秉持非對稱制衡理念,為美方劃出紅線,捍衛國家安全和盟友利益。
軍控機制雖不能消除戰爭根源,卻發揮著遏制戰爭的重要作用。如今,美方意圖“砸爛”現有軍控機制,而俄方對軍控問題一直持開放積極態度。一方面,軍控是目前為數不多俄可與美平等談判的領域,雙邊軍控機制意味著兩國對世界命運享有特殊的“大國責任”,俄不會放棄這一彰顯大國地位的平臺。另一方面,軍控機制下,可通過自行裁減和相互監督避免世界走向核武的深淵。因此,俄將軍控談判列入年度外交工作重點,拉夫羅夫外長強調,“現有條約作為全球安全的基石,非常有必要加以保留”,甚至表示“愿將高超聲速武器等新興核武器納入談判內容”,盡最大努力將美拉回談判桌。
俄頒布新核政策也是出于國內政治的需要。2020年是俄國內權力格局調整和普京布局連任的關鍵之年。3月國家杜馬通過了俄現任總統任期“清零”的議案,后續全民公投將于7月1日實施。然而,上半年以來,俄本就不景氣的國內經濟因疫情愈呈頹勢,加之養老、延遲退休、修憲等政策“非民主”推行,使民眾不滿愈發積累,普京的國內支持率持續走低。此時頒布新核遏制政策,為民眾敲響國際形勢惡化的警鐘,也有增強國內凝聚力、降低全民公投不確定性的考量。
軍控機制是缺乏戰略互信的產物,大國爭奪未來制勝權的較量從不會停歇,根據新的安全形勢制定平衡雙方利益的軍控規則需要新的智慧,這注定要經歷漫長的磨合調整。俄新核遏制政策看似升級了緊張局面,深層意義卻是迫使美方能更加謹慎地審視對俄政策,收斂危險行為,降低美俄爆發戰爭的風險。同時要看到,現有軍控體制難以約束網絡空間、外太空、反導系統、人工智能、高超聲速武器等新技術領域的武器發展,單純依靠核遏制手段難以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這也就注定了新核政策的“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