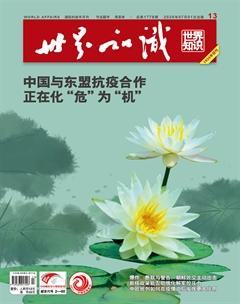美國做得到尖端武器絕對“美國造”嗎
蘭順正
5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現在可能是時候在美國制造F-35戰斗機的所有零部件了。當被問及如何激勵美國公司在美國國內開展更多工作,而不是過度依賴已被轉移到國外的供應鏈時,特朗普回答說,“我們從全球多個地方獲得零部件,問題是,如果與我們合作的一個國家出現問題,我們就無法制造飛機。這多么可怕!我們應該在美國生產所有產品”。特朗普的此番表態再度激發對美國軍火自造問題的觀察和思考。
新冠疫情影響F-35生產
特朗普之所以公開宣揚應把F-35戰機零部件生產全部遷回美國本土,直接原因是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對該先進戰機的全球供應鏈造成了影響。
F-35戰機是美軍一款性能先進、造價高昂的單座單發戰斗機/聯合攻擊機,屬于第五代戰機。國際參與是該項目一大特點,美國是主要的設計方、采購方和資金提供者,英國、意大利、荷蘭、加拿大、挪威、丹麥、澳大利亞、土耳其等國為其開發提供了總計43.75億美元的經費,九個主要參與國擬在2035年前獲取超過3100架F-35整機,以色列、新加坡也在就采購F-35與美國進行談判。有美國軍工機構估計,F-35型戰機未來的總銷售量將會突破6000架,成為全球部署規模最為龐大的戰機之一。在F-35聯合開發計劃中,合作伙伴將被給予優先購買權,并有資格參與分工,這意味著他們對F-35的開發決策和未來改進擁有發言權,并能為F-35生產零部件。目前F-35在海外有兩個總裝生產線,一個是意大利的卡梅里組裝中心,主要負責生產意大利和荷蘭使用的120架F-35A和F-35B戰機,第二個是位于日本三菱重工的小牧南工廠。
此次疫情期間,日本和意大利的組裝廠先后被迫關停,影響到生產交付進度。雖然疫情未導致美國國內的F-35戰機生產工廠關門,但在3月下旬,位于加利福尼亞州的愛德華茲空軍基地報告了四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正在該基地進行的F-35戰機“初始作戰能力測試與評估”被迫暫停。美國政府問責局5月12日發布的最新報告承認F-35戰機零部件供應不足問題愈發突出,指出延期交付的F-35戰機零部件數量從2017年8月的不到2000件增加到了2019年6月的10000件,這些缺失的零部件有60%以上由總計20個海外供應商生產。另外,作為北約盟國的土耳其訂購了俄羅斯研制的S-400防空導彈系統后,美國禁止土耳其購買F-35戰機,并開始逐步淘汰土耳其負責生產的F-35戰機零部件(土為這款戰機提供大約1000個不同的部件,美國尋找新的供應商可能需花費數億美元)。
美國軍工跨國合作的隱憂
深層次看,特朗普的言論也反映出美國國內對于整個國防工業跨國合作問題的擔憂。
一直以來,美國非常重視國防工業的跨國合作,但也有研究認為相關國際合作是把“雙刃劍”,會讓美國越來越依賴外國生產武器裝備,尤其是某些關鍵部件,從而弱化美國國防工業的基礎。美國國會國防聯合監督對外依賴委員會對海軍“麻雀”III空空導彈進行了調查,發現制導系統內裝的是從日本進口的集成電路和晶體管,鐵氧體移相器用的是德國產品,存儲器芯片在泰國組裝,制造球形軸承的原材料則來自四面八方,整個導彈經查證有16種部件是在外國生產的。這項調查的結論是:一旦依賴進口的部件貨運中斷,導彈生產就不可能繼續下去;如美國想用自己的產品來代替這些外國部件,約需18個月時間才能恢復生產。
有美方文獻指出,目前美國的國防工業在計算機存儲器芯片、高功率電子開關用硅元件、高速數據處理用砷化鎵基半導體、先進的纖維光學器材,以及偵察衛星和其他軍事裝備的精密玻璃、液晶和發光顯示器等方面,都嚴重依賴外國供應鏈。今年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咨詢座談會上,美軍高層討論了如何把高超音速武器從設計圖變成實際型號的有關問題,陸軍部部長麥克卡西表達了對供應鏈穩定性的擔憂。所以說,美國國內一直存在將關鍵武器零部件生產對外脫鉤的說法,疫情導致的F-35生產受阻顯然強化了這一觀點。

美軍F-35A戰斗機。
美國的軍工制造很難完全排外
但客觀而論,美國想要切斷軍工跨國合作,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美國雖擁有全球最強大的國防工業,但一國資源終究有限,很難在國防的各個領域保持領先地位。而且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現代武器裝備的研發生產成本越來越高,不確定性因素也越來越多,任何一國都無力獨自承擔所有武器裝備的研制與生產任務。通過國際合作,美國既能將超出國內需求部分的武器裝備出售給其他國家,以賺取利潤并維持國內軍工企業正常運轉,也可以通過與其他國家聯合研發、生產降低成本,加快武器裝備的推陳出新并提高美國的軍工生產能力和軍事技術水平。
美國雖然把中國作為競爭對手,但在軍工領域對中國的需求依然很大。2018年5月“美國國家利益”網站發文指出,盡管美中在政治、軍事、貿易等領域紛爭不休,但美國國防部一份最新報告顯示,中國企業在美國國防產業中依然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美軍高層認為已到“危險地步”,但要改變這一點卻非常困難。如美國武器對先進電子設備依賴性很大,而它們多數都在國外制造,其中90%的印刷電路板都在亞洲制造,其中又有過半是在中國生產的。這些關鍵零部件離開了中國基本無法找到替代供應方,更不用說全球稀土需求的80%由中國供應了(制造一架F-35戰機需要大約400公斤稀土)。
其次,跨國軍工合作不但可以給本國的軍火商們帶來巨大經濟利益,與盟國合作生產武器裝備也能把他們更緊密地綁上美國的“戰車”。由于軍事裝備的敏感性,國家間不論是買賣還是聯合研制都有濃烈的政治和戰略意味,在國際關系中相當于“歃血為盟”或納“投名狀”。而且,相比單純的錢貨交易,聯合研制可以讓相關國家獲得更多技術紅利,雖然美國在國防工業國際合作中對高技術武器裝備的核心技術控制極為嚴格,但跨國合作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果在所難免,相關國家為了拾到“技術牙慧”以加強本國國防工業,往往寧愿經濟虧本、政治承壓、外交受損也依然積極參與。這種心態的普遍存在也迫使美國在推動脫鉤時不得不有所顧忌。此次特朗普發出有關“收攤”言論后,就有澳大利亞媒體發文指責特朗普“不在乎盟友感受”“隨心所欲地忽視、羞辱乃至傷害盟友”。
另外,跨國軍工合作可以直接提升盟友戰斗力。美國國內有觀點認為,不管美國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大,如果聯盟其他成員的軍事基礎和防務能力薄弱,在聯合作戰中必會拖美國后腿。比如在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美國與歐洲盟國的武器裝備技術水平就存在實質差距,影響到雙方協同作戰能力。而美國通過向盟國出售先進武器裝備,甚至與盟國聯合開發、研制生產武器,可以明顯提高聯盟的整體防務水平,一旦需要集體作戰時,可為美國省去后顧之憂。
綜上所述,美國固然有心實現尖端武器“美國造”,采取更多措施削弱對軍工國際合作的過度依賴,但要徹底脫鉤卻有很多主客觀方面的阻力。極為敏感的軍工技術尚且如此,那些涉及民生的產品如電信就更難擺脫全球供應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