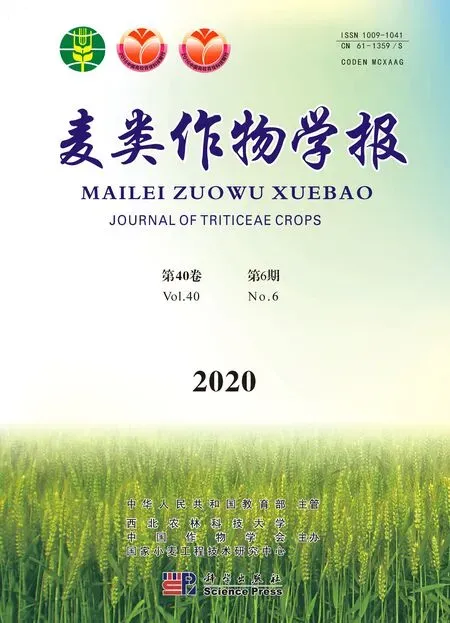旱地小麥根際土壤酶活性及微生物生物量對覆蓋方式的響應
宿兵兵, 程宏波, 柴守璽 , 常 磊, 李 瑞,楊佳佳, 柴雨葳, 李亞偉
(1.甘肅農業大學農學院, 甘肅蘭州 730070; 2.甘肅省干旱生境作物學重點實驗室, 甘肅蘭州 730070; 3.甘肅農業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 甘肅蘭州 730070)
農業覆蓋技術是我國西北黃土高原半干旱區重要的栽培措施之一。覆蓋具有明顯的蓄水保墑[1-4]、調節地溫[2-5]、增加土壤微生物數量[4]及活性[6]、增產增效[1-2,4]等作用。農田小氣候特征的變化必將引起土壤微生物特性的改變。李旺霞等[7]發現,覆膜可提高土壤酶活性, 但不同的覆膜方式對不同酶活性的影響則存在較大差異[8]。杜社妮等[9]在玉米田中研究發現, 地膜覆蓋提高了收獲后土壤蔗糖酶和堿性磷酸酶活性, 卻降低了脲酶和過氧化氫酶活性。徐華勤[10]研究發現,稻草覆蓋下茶園土壤的過氧化氫酶、蔗糖酶、脲酶和磷酸酶較CK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在CK、稻草覆蓋條件下不同施肥處理對土壤酶活性影響并不大。
地膜覆蓋改變土壤的微生態環境, 但對微生物量碳、氮含量影響的結論不一。劉小娥[11]、王 靜[12]、張 帆等[13]、Li等[6]研究發現,地膜覆蓋能夠顯著提高表層土壤養分、微生物量碳、氮含量和物質間的轉化速率, 促進有機質的分解,為土壤微生物生長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于 樹等[14]的研究結果表明, 地膜覆蓋對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的影響不顯著, 但有機與無機肥配施時, 地膜覆蓋下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有所升高。而張成娥等[15]在覆膜對玉米不同生育時期微生物量碳、氮含量的研究中發現,覆膜降低了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 在苗期尤為突出, 原因可能是在覆膜的條件下, 土壤有機物的礦化速率較快,而對其微生物量有一定的掩蓋作用。任江波等[16]研究發現,覆蓋地膜降低了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揭膜后可逐漸恢復到裸地栽培水平; 覆蓋秸稈的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較高, 其中,覆蓋小麥秸稈的效果好于覆蓋玉米秸稈。
有關土壤微生物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長期施肥(有機+無機)、灌溉、秸稈還田和地膜覆蓋等方面, 而在秸稈覆蓋方面的研究鮮有報道。本研究團隊針對西北寒、旱地區生產生態特點提出了“玉米秸稈帶狀覆蓋種植”新技術, 且多年多點試驗及示范結果表明, 秸稈帶狀覆蓋技術對小麥具有突出的增產增效潛力, 且對不同生育時期和土層具有增墑與降墑[1-2]、增溫與降溫[2,19-21]的雙重效應。根際土壤微生物可調節植物生長發育、促進作物養分吸收、提高作物抗逆性[22]等生態功能。本研究擬從土壤微生物生態學的角度出發, 探討小麥根際土壤微生物特性對覆蓋引起的土壤水溫變化的響應, 旨在進一步明確秸稈帶狀覆蓋技術對土壤的生態效應,為深入剖析該技術的產量形成機理及推廣應用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區概況
該試驗于2018年在甘肅省通渭縣平襄鎮甘肅農業大學旱作循環農業試驗示范基地進行。試驗地海拔1 750 m, 年均氣溫7.2 ℃,年日照時數 2 096 h, 無霜期120~170 d, 屬中溫帶半干旱氣候。作物一年一熟, 為典型旱作雨養農業區。平均年降水量390.7 mm, 且60%以上集中在7~9月。試區土壤為黃綿土,0~20 cm土層容重1.25 g·cm-3; 土壤有機碳含量5.52 g·kg-1,全氮 0.65 g·kg-1, 有效磷10.63 mg·kg-1,速效鉀107.1 mg·kg-1,pH為8.5。
1.2 試驗設計
以冬小麥康莊974為供試材料, 分別進行玉米秸稈帶狀覆蓋種植(SM)、地膜覆蓋種植(PM)、無覆蓋露地種植(CK)共3個處理,各處理的小區面積均為180 m2(30 m×6 m), 每個處理3次重復, 采用隨機區組排列。具體試驗處理如下:
玉米秸稈帶狀覆蓋種植(SM):設計種植帶70 cm, 秸稈覆蓋帶50 cm。秋季機械條播5行小麥于70 cm種植帶上, 行距17 cm, 越冬前小麥三葉期后50 cm覆蓋帶上進行玉米整稈覆蓋, 秸稈擺放方向與小麥播種行平行, 為防止秸稈壓苗, 小麥邊行與秸稈間距離為5 cm, 玉米秸稈覆蓋量為風干重9 000 kg·hm-2。
全膜覆蓋種植(PM):旋耕整地, 耱平后全地面覆膜, 膜面覆土1cm。穴播小麥, 行距17 cm。
露地對照種植(CK):旋耕整地, 耱平后平作, 條播行距17 cm。
各處理播種量均為225 kg·hm-2,施純氮120 kg·hm-2、P2O590 kg·hm-2,均作為基肥在旋耕整地時一次性施入, 生育時期內不再追肥。在開花期進行1~2次“一噴三防”作業。
1.3 土壤樣品采集
分別在小麥拔節期、孕穗期、開花期、灌漿期、蠟熟期采用抖土法取0~20 cm根際土壤樣品, 每個處理3次重復,每個重復采用3點法取樣, 去除根系等動植物殘體,混勻并過1 mm篩后分兩部分裝入8號自封袋,低溫帶回實驗室,一部分置于通風處自然風干,另一部分保存至4 ℃冰箱, 用于含水量、pH、土壤微生物量碳、氮測定。
1.4 測定方法
1.4.1 土壤含水量、溫度及pH測定:
(1)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測定[1-2];
計算公式:SWC=(W鮮-W干)/(W干-W鋁)×100%式中, SWC為土壤含水量,W鮮為土壤樣品鮮重,W干為土壤鮮樣烘干后重量,W鋁為鋁盒重量。
(2)土壤溫度:在土壤樣品采集的同時, 利用電子溫度計測定[2];
(3)土壤pH:采用土水質量體積比為1∶2.5浸提, 用pH計測定[27]。
1.4.2 土壤酶活性測定
(1)過氧化氫酶活性測定采用KMnO4滴定法[23];
(2)蔗糖酶活性測定采用3,5-二硝基水楊酸比色法[24];
(3)脲酶活性測定采用靛酚藍比色法[23];
(4)堿性磷酸酶活性測定采用磷酸苯二鈉比色法[23]。
1.4.3 微生物量碳(MBC)、氮(MBN)含量采用氯仿熏蒸-K2SO4浸提法[23,25]
用0.5 mol·L-1的硫酸鉀溶液浸提(土液比為1∶4), 采用碳氮聯合分析儀測定其含量, 微生物量碳、氮的換算系數分別為0.38、0.45。
1.5 數據處理
采用Excel 2016和SPSS 19.0進行數據分析, 通過Duncan法進行顯著性差異檢驗。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壤水分、溫度及pH對覆蓋方式的響應
由表1可知, 從拔節期-蠟熟期, 各時期土壤含水量均以秸稈覆蓋帶(SMd)最高, 其次為地膜覆蓋(PM), 秸稈帶狀覆蓋(SM)處理的種植帶(SMu)與露地(CK)相近;SMd和PM在拔節期-蠟熟期平均土壤含水量分別較CK高 29.49%、14.55%。處理間差異以開花期最大,變異系數(CV)為26.54%, 蠟熟期最小, CV值為 2.25%。說明覆蓋平抑了土壤水分在不同時期間的劇烈變化, SMd和PM土壤含水量不同時期間的CV值分別為26.19%、 30.42%, 均低于CK (47.16%), 且平抑效果SMd更為突出。

表1 不同生育時期土壤水分、溫度及pH對覆蓋方式的響應Table 1 Response of soil moisture, temperature and pH to mulching method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從拔節期-灌漿期, 各時期0~20 cm土層土壤溫度均以CK最高, SMu次之且與PM相近, SMd最低。SMd只有在蠟熟期略高于地膜覆蓋。SMd和PM在拔節期-蠟熟期平均溫度分別較CK低12.60%、5.15%。處理間差異以拔節期最大, CV值為7.83%,蠟熟期最小, CV值為3.07%。SMd的0~20 cm土層土壤溫度時期間CV值為12.62%, 較CK明顯增加,而PM與CK相近。
從拔節期-孕穗期, 0~20 cm土層土壤pH以PM最大,各處理間差異不顯著。開花期-蠟熟期以SMd最大, PM次之, CK最小。SMd和PM在拔節期-蠟熟期pH平均分別較CK高 1.64%、1.24%。處理間差異以蠟熟期最大, CV值為1.43%, 孕穗期最小, CV值為0.51%。SMd和PM的pH在時期間變異系數分別為 0.86%、1.31%, 均低于CK(1.76%),說明覆蓋較露地平抑了時期間pH的波動。
2.2 土壤酶活性對覆蓋方式的響應
從拔節期-蠟熟期,SM處理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分別較CK降低了21.91%、 2.82%, 堿性磷酸酶活性提高12.14%,過氧化氫酶活性變化較小。覆蓋帶(SMd)和種植帶(SMu)間的酶活性差異較大, 覆蓋帶的土壤酶(除堿性磷酸酶)活性均較CK有所降低, 種植帶土壤酶活性(除脲酶)均高于CK。
SMd從拔節期-蠟熟期的土壤過氧化酶、脲酶、蔗糖酶平均活性分別較CK降低10.5%、 30.56%、21.22%; 而堿性磷酸酶則在拔節期、蠟熟期高于CK,分別提高 8.33%、 35.14%, 在孕穗期、灌漿期則低于CK 5.88%、3.57%, 使其拔節-蠟熟階段的平均活性高于CK 9.40%。
SMu處理的土壤過氧化氫酶、堿性磷酸酶、蔗糖酶活性在不同時期表現為高于或低于CK,因增高幅度大于降低幅度,使3種酶在拔節-蠟熟階段平均酶活性分別較CK高7.58%、 14.09%、 10.32%; 而脲酶在孕穗期顯著高于CK (16.67%), 其他時期則顯著低于CK (12.00%~ 54.55%), 使其拔節-蠟熟階段的平均活性低于CK 15.74%。
PM處理在不同時期對土壤過氧化氫酶活性、脲酶、堿性磷酸酶及蔗糖酶的活性表現為或促進或抑制作用, 其中對過氧化氫酶、堿性磷酸酶活性的促進作用大于抑制作用,二者拔節-蠟熟階段平均酶活性分別高于CK 3.50%、6.71%。PM對脲酶和蔗糖酶活性的抑制作用大于促進作用,拔節-蠟熟階段兩種酶的平均酶活性分別低于CK 3.70%、6.49%。

相同時期圖柱上不同字母表示處理間差異在0.05水平顯著。圖2同。
2.3 土壤MBC、MBN含量及MBC/MBN對覆蓋方式的響應
覆蓋總體較CK提高了土壤MBC、MBN含量及MBC/MBN, SM分別較CK提高24.40%、 12.53%、3.42%, PM分別提高了47.37%、 2.76%、52.19%。SMd與SMu之間的MBC、MBN含量以及MBC/MBN的差異也較大。
SMd處理在拔節-開花階段的各時期均較CK顯著提高了土壤MBC含量及MBC/MBN。對于MBC,SMd處理在拔節-開花期的增幅(46.96%~63.18%)大于灌漿-蠟熟期(15.37%~ 35.32%), 拔節-蠟熟階段平均較CK提高MBC含量37.19%。SMd處理的MBN含量在拔節期-開花期較CK提高26.56%~55.21%, 在灌漿-蠟熟期則較CK低17.83%~19.89%, 拔節-蠟熟階段平均含量則與CK相近。SMd處理的MBC/MBN在各時期均較CK提高 (3.16%~75.77%),以灌漿期增幅最小,蠟熟期最大, 拔節-蠟熟期平均較CK高27.33%。
SMu處理較CK降低拔節期-孕穗期MBC含量9.11%~30.02%, 開花期-蠟熟期則提高MBC含量16.56%~31.14%; 對于MBN,SMu僅在孕穗期較CK顯著降低(28.65%),拔節期和開花期顯著提高。在拔節-蠟熟階段,SMu的MBC、MBN含量顯著高于CK(15.26%、 21.66%)。由于MBN含量增幅較大, SMu的MBC/MBN除在蠟熟期較CK提高27.30%外, 其他各時期均較CK降低, 拔節-蠟熟階段平均較CK低13.67%。
PM處理在拔節-蠟熟階段的各時期均較CK提高了土壤MBC含量(32.52%~ 101.89%); 其MBN含量在開花期和蠟熟期低于CK(5.47%、15.55%),其他各時期則顯著高于CK14.58%~43.91%; 由于在各時期MBC的含量增幅均大于MBN, 因此,PM處理的土壤MBC/MBN在各時期均高于CK(10.08%~ 82.05%)。
3 討 論
已有研究表明, 施肥可降低土壤pH值[26]。本研究發現, 覆蓋提高了土壤pH值, 可能原因是覆蓋促進深層水向表層富集, 帶來了可溶性鹽基離子, 而覆蓋又降低了淋溶, 使鹽基離子在表層土壤積累, 造成土壤pH升高[27]。土壤酶是一類具有催化能力的生物活性物質, 是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重要參與者[28-29], 可作為反映土壤肥力和生態系統功能的敏感指標[30]。本研究發現,小麥根際土壤過氧化氫酶活性隨生育時期推進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在開花期達到最大值, 與張 亮等[31]研究一致。脲酶活性先降低后升高, 開花期最低, 堿性磷酸酶呈“波浪”型,灌漿期為最低點, 這與張 亮等[31]在百合根際土壤中的研究有所差異, 其原因可能是植物類型、土壤類型、施肥制度、種植方式及環境因子不同的原故。秸稈覆蓋帶平均較露地降低了土壤過氧化氫酶、脲酶、蔗糖酶活性, 可能原因是秸稈覆蓋帶的降溫作用抑制了酶活性。

圖2 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及碳氮比對覆蓋方式的響應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既是土壤有機質和土壤養分轉化與循環的動力, 又可作為土壤中植物有效養分的儲備庫, 對土壤環境因子的變化極為敏感[26]。一般而言,土壤中微生物量和微生物群落活躍程度呈正相關關系, 即微生物量越大, 其群落活躍度就越高。本研究中,MBC含量在小麥拔節-蠟熟期隨生育時期推移而波動,在小麥蠟熟期最高, 這與李云玲[32]在玉米上的研究結論一致。MBN開花期最低, 可能原因是開花期是植物的旺盛生長期, 小麥對氮素需求增多, 植物與土壤微生物之間的養分競爭加劇, 而植物在與微生物養分競爭中得到了更多的營養物質, 從而導致MBN 下降[33]。土壤MBC/MBN可反映微生物群落結構信息, 其顯著的變化預示著微生物群落結構變化, 可能是微生物量較高的首要原因[34]。覆蓋不同程度的提高了土壤MBC、MBN和MBC/MBN,以開花期MBC/MBN較高,推測開花期可能土壤真菌占優勢。
本研究表明, 除過氧化氫酶外,土壤含水量與酶活性存在明顯的正相關, 這主要是因為, 土壤水分的增加能夠為各種酶促反應提供反應條件與場所, 促進酶和底物的擴散, 酶和底物濃度相應提高, 從而使酶活性有所增強[35-37]。土壤溫度與多數微生物特性指標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其原因可能是溫度升高會促進微生物活性, 土壤微生物的生長與代謝速度加快, 產酶速度也會增快, 酶庫得到擴充, 酶活性升高[33]。MBC和MBN均與脲酶、堿性磷酸酶呈極顯著正相關,而MBN與過氧化氫酶呈顯著的負相關,可能原因是土壤生物學特性對覆蓋方式的響應存在既相互協同又相互制約的復雜關系。
4 結 論
地膜覆蓋對土壤具有調溫保墑、提高pH的作用, 促進土壤過氧化氫酶、堿性磷酸酶的活化, 但抑制了脲酶和蔗糖酶活性。秸稈帶狀覆蓋在提高土壤SCW和pH的同時, 對0~20 cm土層土壤起到明顯的降溫作用, 且SMd的對土壤的保墑、降溫、pH的影響大于SMu。SMu和SMd土壤水溫及pH的差異也導致兩帶間酶活性的差異, 覆蓋帶的土壤酶(除堿性磷酸酶)活性均較CK降低, 種植帶土壤酶活性(除脲酶)均高于CK。覆蓋的增墑效應可能有利于提高微生物群落活躍程度,從而增加土壤MBC、MBN含量和MBC/M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