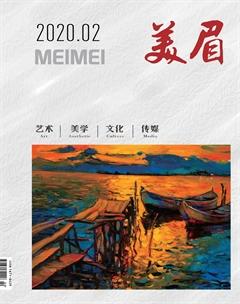音樂地理學視域下的四川民歌
葉靜
關鍵詞:音樂 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 民歌 四川
不同地理環境中音樂風格的特征和規律差異巨大,因而音樂地理學的出現適用于辨析特定地理文化區域中音樂的特征、背景及技術語匯系統。其中地理中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帶來的音樂影響是不可輕易小視的,自然地理帶來了各民族之間的氣候條件差異和自然物資差異,人文地理帶來了社會群體的不同生活習慣和地域性語言。
在音樂教育中,不能僅局限于學校教育中音樂課程教育和校本音樂課程教育,而應該深層次地理解到社會和家庭各種形式的潛移默化影響。加強各個層次的音樂文化教育、創作、推廣,看到基于滿足于音樂文化基本需求后的延續和更新需求。
一、自然地理對音樂教育的影響
音樂地理性的重要性影響,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春秋時期,先輩們在編纂《詩經》時便立下了,十五“國風”一律標明原傳地的原則,就連“頌”,也要指出是“商頌”“周頌”還是“魯頌”。也正因如此,后世對“詩”的研究中音樂地理性劃分做出了不俗的貢獻。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1223-1296年)便是輯錄《地治》《水經注》《詩譜》等材料,將凡是涉及《詩經》中的地理名稱皆匯編于《詩地理考》這本專著之中,為后世音樂、地理的交融起到了有益的推廣作用,也是《詩地理考》流芳千古,名揚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紀80年代后期音樂地理學在我國被正式提出,并作為音樂學和地理學互相交叉而形成的新型學科而誕生。它主要以“音(樂)——地(理)”為理論基礎,探討各種特定時空下的區域音樂現象。以四川為例:
(1)四川地理環境特殊,四面環山,聚集了眾多少數民族,例如彝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因而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與山地民歌十分豐富多彩。其中,山地民歌內容大多以反映山地勞動人民的勞作場景、田園生活、青年男女愛情為主的創作,其中代表地域性的代表作品《康定情歌》《神奇的九寨》等。
(2)四川四面環山除了山地民歌以外,川中平原地區便是人口密集的市區,城鎮,因而受地理因素影響,另一種節奏簡潔明快,朗朗上口,演唱時常使用竹片、竹筒敲打伴奏的“四川清音”便孕育而生。只是受到人口密集的城鎮化社會群體需求而存在的,最早是明清時代流行于川渝地區的民間音樂形式,由“湖廣填四川”的移民結合音樂地理性中地理環境和語言環境的眾多因素雜糅而成。四川清音作品《布谷鳥兒咕咕叫》便是運用四川方言演唱,流行于成都為首的中心城區、農村、江河沿岸。四川清音受到地理位置、地方語言、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地域文化的影響,形成了有別于其他地域的唱腔風格,在天府之國豐衣足食后的“茶館文化”熏陶下,逐漸形成了唱腔清麗,細膩婉轉的演唱風格。
因而,在學習音樂中有條理、有邏輯地為學生科普音樂自然地理知識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讓學生擁有及時的代入感和環境想象空間,對后期音樂作品的歌詞、背景、曲調有更深層次的理解。
二、人文地理對音樂教育的影響
人文地理中地域性的語言在音樂教育中有著十分突出的作用,為后來的音樂教育少數民族傳承有著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在研究民間戲曲和少數民族時,由于民間音樂家運用了大量的地方方言形式,所以研究地域性的語言、語音、語調與唱詞內容的關系,是人文地理為音樂教育的豐富和傳承,因而有“語言作為一種音樂,音樂作為一種語言”一說。
20世紀80年代,全國范圍進行柯達伊教學法推廣,過去的幾十年中,人們對它的理解還大多停留在科爾文手勢、首調唱名以及不同節奏的讀法等教育手段中,對其核心的“母語音樂教育”了解甚微,其中“母語音樂教育”中的“母語”在漢語中是一個英譯詞匯,其英語譯為“mother tongue”或是“parentlanguage”,又稱“第一語言”。“母語”系指一個人在嬰幼兒時期自然習得的語言,一般是一個人的本民族語言(地域性語言)。兒童的思維能力都是在一定的語言基礎之上的,運用語言的能力對下一步的學習至關重要,所以一個人在嬰幼兒時期自由習得的語言,一般是一個人的民族語言。以四川話為例:

四川話作為官話的一個分支,同普通話相比較,在語調、詞匯、語法方面也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在四川地區川中、川東、川西、川南方言更是十里不同天,這里以成都話為例,四川方言主要表現在:
(1)聲母無卷舌音zh、ch、sh、r 不卷舌。
(2)韻母中無后鼻音韻母eng、ing。
(3)聲調調值無高升調。 其中,更是喜歡。詞語使用中:
(1)名詞的重疊,非重疊詞匯有單字單用、加“子”尾、加“兒”尾或兒化等幾種方式。例如: 花—花花兒、蟲- 蟲蟲兒、洞—洞洞兒。
(2)四川成都方言話動詞一般不重疊,動詞加“一下”或“哈兒”表示嘗試一下回事非常短暫的動作。例如:看一下、看下兒、看一哈哈兒;說一下、說下兒、說一哈哈兒。
(3)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話中形容詞的生動形式相當豐富。這從川劇、方言作品中都可明顯感覺到。
其中,四川阿壩州,從藏族歌手容中爾甲譜曲和參與填詞的四川音樂作品《神奇的九寨》(譜例1)中可以看到,作者將九寨擬人化描寫,運用文字將人間天堂九寨溝賦予了感情色彩,歌詞中“溫情”是如燦爛的陽光一般“灑滿”了高高的山崗,美麗的“童話”世界也是如草地般“鋪滿”了高原。因而,四川話中靈活運用形容詞將九寨溝描寫得活靈活現。另一方面,四川方言聲調調值無高升調,在方言語句中話語結尾聲調多向下,在《神奇的九寨》這首音樂作品中也會發現長音“哦”(653)。長音結尾經過la-sol-mi 是一個音調向下的形式,和四川人說話方式相似,在全文每一個歌詞中也基本保持著聲調調值無高升調(與漢語的陽平相似),停頓向下的過程。這基本符合了四川方言的音調特色,為后來《神奇的九寨》在音樂教育傳唱中起到了很好的推廣作用。
四川民歌《康定情歌》(譜例2)便是1946年,吳文季先生在西康甘孜(現四川甘孜)任文化音樂教員的時候,偶然聽到的一首《溜溜調》整理,加工,而成了現在耳熟能詳的《康定情歌》(又叫《跑馬溜溜的山上》)。其中“溜溜調”中的“溜溜”在歌詞中為漂亮,美麗的意思。再次體現了四川話中形容詞的生動形式相當豐富。用“溜溜”的云、山、城、男子、女子表現了美好、安寧的康定城美景、美人、美色。

音樂中的地理因素使得四川山地民歌曲調一般都是高亢洪亮、熱情奔放、富有節奏的,簡單明了的歌詞使得歌曲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為后來的音樂文化創作與音樂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藝術素材和創作源泉。地域性語言特色在音樂中的積極表現也是讓四川民歌不同于他地民歌的區別之一。
此外,音樂地理學研究中紛雜繁蕪,因為音樂一方面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有著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它又是相對獨立,具有個性的存在。因此,有時候音樂家可以為一個國家的音樂文化區進行整體劃分,也可以以一個民族為單位作音樂地理劃分,可以作一種音樂類別的音樂地理劃分,更可以作一首樂曲、歌曲,一種音樂風格的地理劃分。
是將自然因素與音樂因素分別作為相互對立而又相互交融的兩個整體,“音(樂)——地(理)”的區域音樂現象。因此,它所涉及的社會歷史內容便十分廣泛,其研究對音樂、地理、教育、文化的整體進步影響重大。因而在音樂教育教學中,應合理規范地使用音樂地理素材,正確引導學生學習音樂知識和開闊音樂風格眼界。
結論:
通過收集整理材料以及結合本學期音樂教育原理的學習,本文認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對音樂教育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當然,音樂課堂不是地理課與歌唱課的簡單相加,而是教育中音(樂)——地(理)區域音樂現象的雜糅歸一、升華淬煉、傳遞賦予意味的音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