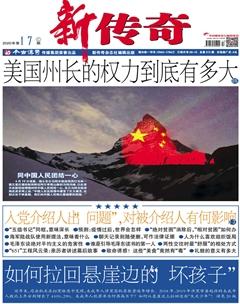“絕對貧困”消除后,“相對貧困”如何辦
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實現后,并不意味著中國反貧困事業的終結。中國農村的貧困將會進入到一個以轉型性的“次生貧困”和“相對貧困”為特點的新階段,需要進一步完善貧困治理體系,提升貧困治理效能。
2020年4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調研時說:“對于今年全面完成現行指標的扶貧,我是有信心的。我更關心的,就是今年以后是不是能夠穩定下來,是不是有一個長效的機制,就看這些基本的措施是不是穩定的、持續的。”的確,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實現后,中國會進入“后扶貧時代”,克服貧困治理的“短期效應”,保證扶貧政策和措施穩定持續,提升貧困治理效能,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大議題。
一個判斷、三大趨勢
2020年我國將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但是,“絕對貧困”在統計意義上的消失并不意味著中國反貧困事業的終結。2020年后,中國農村的貧困將會進入到一個以轉型性的“次生貧困”和“相對貧困”為特點的新階段,需要進一步完善貧困治理體系,提升貧困治理效能。具體表現為三大趨勢:
后扶貧時代,“相對貧困”將成為貧困治理的重點。2020年,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打贏脫貧攻堅戰目標的實現,我國農村的貧困將主要表現為“相對貧困”。“絕對貧困”率的下降只是測度標準固化下的一種表象,“相對貧困”現象則將長期存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物質和精神財富均沒有得到極大滿足的情況下,總有一部分人占有相對多的資源,另一部分占有相對少資源的群體和個人則為“相對貧困”者。同時也要注意到,貧困并不僅僅體現為物質上的缺乏,思想文化、精神意志、人際關系等各類有形與無形資源的短缺都是貧困。
反貧困將在城鄉統籌進行。隨著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農村人口逐漸向城市遷移,城鎮化在不斷吸納農村人口的同時,也將貧困問題空間性地轉移至了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我國將進入城市貧困和農村貧困并重的階段,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發展為城鄉統籌扶貧創造了有利條件。因此,從城鄉統籌的角度審視貧富差距以及“相對貧困”問題將越來越重要,反貧困也將面臨建立完整的城鄉反貧困體系、將農民工貧困治理納入我國反貧困體系等難點。
鄉村貧困治理與鄉村振興同步推進。緩解鄉村貧困是鄉村振興的前提,貧困治理在實踐中解決了貧困居民的基本生存與發展需求,為鄉村振興提供了重要時序前提和空間基礎。鄉村振興則通過助力產業脫貧和精神脫貧,為精準脫貧提供長效內生動力。
后扶貧時代貧困治理面臨的挑戰
目前,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主導下,貧困現象大規模減少,其根本原因在于舉全國之力、投入大量的扶貧資源,但這也使得某些地區和群體的脫貧穩定性并不牢固。
如,鄉村基礎設施雖有了較大的改善,在住房條件、飲水安全、獨用廁所、有線電視、衛生室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有突出表現,但在上學便利性、寬帶建設、管道供水、公共交通等方面還存在一定不足,能源供應、自來水凈化、垃圾集中處理等方面亟待改善,部分特困地區仍然面臨難以突破的發展困境。貧困群體,特別是農村的“三留守”(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問題日益突出。農村留守兒童的營養、生活、安全和教育難以得到有效保障;留守婦女面臨勞動強度高、精神生活貧乏、子女教育乏力等問題;留守老人則缺乏良好的醫療照顧和養老保障。
另外,部分地區和群體存在返貧風險。首先是因為農民可行能力不足。扶貧開發過程中,大部分地區是基于政策導向,強調水利、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職業教育培訓、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一旦脫貧,有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就會缺少維護和可持續性。同時,由于農村社區的市場發育不足,脫貧人口的市場能力、知識技能與信息化社會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容易被社會邊緣化,致使部分脫貧人口在遭遇突如其來的天災人禍時,可能會因難以有效應對而再度陷入貧困。
此外,長期以來,農村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合理、服務可及性差,農民健康衛生知識匱乏、自我保護意識差、預防能力不足,一旦患病就會使家庭陷入貧病交加的境地。
還有就是,自然災害與農村貧困發生率呈正向關系。重大自然災害,一方面為區域受災群眾帶來生命與財產的損失;另一方面還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公共服務設施、經濟基礎設施,影響區域發展環境,毀損發展根基,進而影響貧困治理成效。
后扶貧時代貧困治理的可行思路
后扶貧時代貧困治理要將扶貧與扶志、扶智結合的傳統長期堅持下去,進一步補齊貧困群眾的精神短板和能力短板。可加強脫貧致富典型的宣傳推介,組織開展脫貧致富模范評選獎勵表彰活動,樹立“自主脫貧光榮”的鮮明導向;通過輿論宣傳引導、貧困戶脫貧培訓、科技文化“三下鄉”等形式,提升貧困農民素質能力,實現職業技能培訓全覆蓋。要根據致貧原因,對符合條件的已脫貧對象,明確“脫貧不脫政策”的執行期限、終止標準、終止流程。要分類、分級、分批改進現有配套制度,完善特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配套要求。要深入推進實施教育、醫療和住房保障政策,提高保障標準,加強農村低保制度和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確保兜底保障對象的保障性收入不低于同期國家貧困標準,加大對社會救助兜底保障對象的幫扶力度。
還可以推動“互聯網+貧困治理”,健全返貧風險防范機制。一是要不斷利用扶貧大數據和信息化技術,構建返貧風險預測預警機制,加強動態監測。全面建設脫貧人口動態信息管理系統、脫貧人口常態化跟蹤監測機制、返貧風險分級分類治理機制、返貧風險雙向溝通機制。二是要進一步擴大醫療救助人群范圍,擴大重大疾病保障病種范圍,提高醫療服務水平,鼓勵分級診療、縣域內看病與開展遠程醫療相結合,加快實施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充分發揮醫療救助作用,積極拓寬多元化的救助渠道等。三是要構建災害預警機制,通過保護與修復自然環境、生態移民等措施來避災;通過加強防災減災基礎設施建設來抗災;通過完善農業保險救助體系來救災。推進救災工作從應急性向常規性轉變,從災后救助體系向綜合救助體系轉變,加快普及災害相關知識,強化防災理念,提升防災能力。
(《國家治理》 許源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