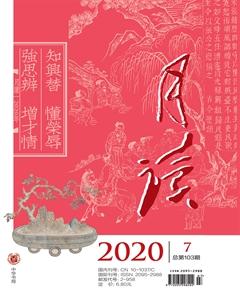《史記》論“天下一統”“海內一統”
王子今
《史記》沒有出現過“統一”一語,但是使用了“一統”的概念。《史記》記錄了秦實現“一統”的歷史。《史記》有關秦政的論述,對許多方面有所否定,但似乎對“一統”的歷史趨勢是肯定的。這一文化態度,應當與“《春秋》大一統”的政治導向有關。《史記》關于“一統”的內容,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秦漢歷史的真實走向。太史公肯定“一統”,卻對《秦始皇本紀》和《李斯列傳》中出現的“別黑白而定一尊”或“別白黑而定一尊”的行政方式有所批評,這顯然體現了他清醒的政治觀點,透露出開明的歷史理念,值得我們在讀《史記》時予以重視。
一、《史記》言“天下一統”
對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 21)實現統一的歷史進程,《史記》沒有采用“統一”的詞匯予以記述,而習慣用“一統”一語。《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按:(周)王赧卒后,天下無主三十五年,七雄并爭。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統,十五年,海內咸歸于漢矣。”這是在關于周史的回顧中說到秦始皇時代“天下一統”。張守節作為唐代學者,這一說法,自然偏晚。《史記》本身出現“天下一統”之說,見于《李斯列傳》中呂不韋的舍人李斯“任以為郎”時“說秦王”的言論:“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李斯敦促秦王政“急就”而不失時機,積極進取,“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
而對于后來實現統一的政治成功,李斯的說法是“并有天下”,“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
“天下一統”的說法,也見于《漢書》中對于漢帝國政治局勢的記述,如《異姓諸侯王表》和《師丹傳》。《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中可見曹植的奏疏,也寫道:“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又如《三國志·吳書·宗室傳·孫鄰》所見孫鄰語,也說“天下一統”。或許可以說,在《史記》之后,“天下一統”已經成為政論熟語。
《漢書·武帝紀》說“中國一統”,《后漢書·朱儁傳》可見“海內一統”,《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可見“萬里一統”,又《三國志·魏書·徐宣傳》“遠近一統”,《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九有一統”;而《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載孫權詔,《三國志·吳書·胡綜傳》載胡綜為吳質作降文,均言“普天一統”,也語義相近。
這些政治判斷和政治取向的表達,很可能是受《史記》“天下一統”說法的影響。
二、《史記》言“海內一統”
《史記》對于秦國實現統一,多見“海內一統”的表述。《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廷尉李斯”建議行郡縣制的政論,說道:“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
《史記·太史公自序》關于上文“十五年,海內咸歸于漢矣”的歷史變化,使用了“海內一統”之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所謂“海內一統”,《漢書·司馬遷傳》寫作“海內壹統”。
《史記》中所見“天下”和“海內”的習慣性對應,起初即用以評價秦統一天下的事業:“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史記·魏世家》)“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史記·刺客列傳》)“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天下”和“海內”都是說當時最宏大的政治空間。
在《秦始皇本紀》中又可以看到“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的說法。這是“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也就是王綰、馮劫、李斯等重臣奉命上書“議帝號”時說的話。正式的官方政治宣言中的這種說法,又如瑯琊刻石:“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秦二世回應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的進諫,說道:“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也說“天下”“海內”。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道:“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意思是“海內為一”的政治格局為“周流天下”的繁榮的經濟生活提供了條件。
“天下”“海內”的對應,在漢代政論文字中多有繼承。賈誼《過秦論》寫道:“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正是例證之一。《史記·孝文本紀》中還有:“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有時“天下”“海內”的使用,形成了嚴謹的對仗語式。如《史記》的《淮陰侯列傳》:“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淮南衡山列傳》:“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漢書》也多見這樣的語例,如《律歷志》:“貞天下于一,同海內之歸。”《伍被傳》:“臨制天下,壹齊海內。”《賈誼傳》:“威震海內,德從天下。”《韓安國傳》:“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吾丘壽王傳》:“天下少雙,海內寡二。”《東方朔傳》:“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鮑宣傳》:“承天地,安海內。”學者或許可以將這種政治語言學的特殊現象作為關注與研究的對象。
《史記》所見以對“海內”即“天下”的全面控制來稱頌秦始皇政治功績的話語,有周青臣說:“賴陛下神靈明圣,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淳于越說:“今陛下有海內,……”秦二世說:“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又有“制御海內”之說(《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中類似的說法,又有《平準書》“并海內”,《三王世家》《劉敬叔孫通列傳》“定海內”,《平津侯主父列傳》“危海內”,《高祖本紀》“威加海內”,《秦楚之際月表》“平定海內”,《禮書》“總一海內”,《律書》“恩澤加海內”,《范雎蔡澤列傳》“威蓋震海內”,《齊悼惠王世家》“海內初定”,《三王世家》“海內未洽”,《春申君列傳》“盈滿海內”,《酈生陸賈列傳》“海內搖蕩”“海內平定”,《萬石張叔列傳》“巡狩海內”,《平津侯主父列傳》“匡正海內”“化于海內”“海內乂安”,《滑稽列傳》“海內無雙”。
上文說到,“海內一統”又見于東漢人朱儁的政論(《后漢書·朱儁傳》)。意思大體相近的,還有“萬里一統”的說法。蜀漢將領孟達投降“歸魏”,曹丕“甚相嘉樂”,表達了“歡心”。《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載錄了曹丕寫給孟達的信,其中自然有對曹魏政治形勢的自我宣傳:“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質任。”其中所謂“海內清定,萬里一統”,其實是可以理解為“海內一統”的。
后世“海內一統”的語言習慣,很可能來自《史記》的行文。
三、秦實現“一統”的歷史觀察
上文引李斯所謂“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是李斯被趙高陷構,收捕治罪,在獄中上書秦二世所說的話。《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李斯自陳功績,說到七個方面對秦王朝的貢獻,其中第一條和第二條陳述秦統一之促成:“臣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
通常對秦實現“一統”的理解,往往限定于兼并六國。如后人所謂“六王畢,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宮賦》)。其實,“北逐胡、貉,南定百越”,北河與南海兩個方向的進取,超越了戰國七雄控制的地域。這兩個方向的軍事征伐,其實也在秦統一的戰略主題之內。
《史記》提示我們注意這一歷史現象,除了《李斯列傳》詳盡記錄了李斯的言辭之外,還有《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前221)記事內容中已言“南至北向戶”,二十八年(前219)瑯琊刻石有“皇帝之土,……南盡北戶”語,可知向嶺南的拓進應當在兼并六國之后開始。秦軍遠征南越的軍事行動開始得較早,可以引為佐證的有《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的記載:“……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文中指出,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軍在滅楚之后,已經開始“南征百越之君”的軍事行動。《史記·南越列傳》說秦遠征軍“與越雜處十三歲”,從年代上看,與《白起王翦列傳》的說法相合。而《漢書·嚴安傳》:“秦禍北構于胡,南掛于越,宿兵于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也說秦的勢力進入嶺南,在秦統一的時間表之內。
《史記》的記錄,為我們真實、準確、完整地認識秦“一統”的歷史過程,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四、關于“《春秋》大一統”
對于“一統”的追求,在先秦政治思想表述中已經有比較鮮明的體現。儒學經典中較早可以看到大致明朗的思想傾向。《詩·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樣的話,可以理解為四海之內,山野都是“王”的土地,民眾都是“王”的臣仆。這一詩句,后來被頻繁引用,形成較大的影響,成為一種政治信條。
“大一統”一語的明確提出,最早見于《公羊傳·隱公元年》。對于《春秋》一書中為什么以“王正月”開始這一問題,作者回答道:“大一統也。”這里,“大”是指尊崇、推重。“大一統”是儒學學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方向,也是他們推崇的政治體制。《史記·太史公自序》有一段太史公和“上大夫壺遂”的對話:“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這段文字近七百字,回答壺遂“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的提問,肯定了《春秋》的意義:“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指出儒學經典中,“《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董生”,據裴骃《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裴骃《集解》:“骃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史記·儒林列傳》說:“(董仲舒)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閑,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許多學者認為司馬遷曾經從董仲舒研習《公羊春秋》,《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中吳樹平先生撰寫的辭條“司馬遷”就寫道:“司馬遷十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期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961頁)也有學者說,司馬遷“自十歲起到二十歲壯游前”的“從學經歷”,包括“從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的大義”(袁傳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頁)。而“司馬遷所稱《春秋》亦指《公羊傳》”,金德建先生早有考論(《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12—115頁)。而當時社會文化的大趨勢,如《漢書·儒林傳》所說,“(漢武帝)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公羊》學地位上升,“武帝對《公羊》學日益明顯的偏愛”,“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當時,“投入《公羊》家名下的儒生大為增加”,主流意識形態“有濃重的《公羊》學色彩”(陳蘇鎮:《〈春秋〉與“漢道”—— 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第226—229頁)。可以推知,《公羊傳》“大一統”思想經過董仲舒而影響到司馬遷,是很自然的事。
《史記》沒有出現“大一統”的文字,而《漢書》中屢見這一政治理念的表達。《漢書·路溫舒傳》:“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董仲舒說“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強調“《春秋》大一統”是超越空間、時間限制的絕對真理。這樣的觀點,司馬遷是熟悉的,也應當是基本接受的。
五、“一統”的路徑
戰國時期,社會希求統一的意愿已經在不同學派發表的文化論說中有所表現。儒學學者最早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主張;其他不同學派的學者,也分別就“大一統”有論說發表。“大一統”理想的提出,是以華夏文明的突出進步和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初步形成作為歷史基礎的。大一統政治體制,是儒學學者的政治理想,但是,在當時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卻不僅僅是這一派政治學說的主張。和一切政治概念一樣,同一政治命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進行解釋,可以為不同立場的人所利用。對于“大一統”來說,儒學思想家們往往期望恢復周王朝的“大一統”。其他學派則傾向于建立在新的政治基礎上的新的“大一統”。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論即以君主權力的一元化為思想基點。《慎子·佚文》載錄慎到的言論:“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強調政治權力一定要集中,以避免二元和多元的傾向,認為這種傾向將導致動亂,如《慎子·德立》所說“兩則爭,雜則相傷”。《墨子·尚同中》也提出過“一同天下”的說法。莊子甚至曾發表類似的涉及“天下”這一政治命題的意見,如《莊子·天道》所謂“一心定而王天下”,《莊子·讓王》所謂“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等。
對于“大一統”實現的方式,《孟子·梁惠王上》記錄了孟子的觀點。對于天下怎樣才能安定這一問題,孟子回答說:“定于一。”當對方問到誰能夠實現統一時,孟子回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就是說,不好殺人的國君能夠統一天下。另外,孟子還強調:“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孟子·離婁上》)“仁人無敵于天下。”(《孟子·盡心下》)王道的核心,就是以“德”統一天下。然而歷史事實上的統一,是秦人在法家思想指導下通過暴力的形式,采用戰爭的手段,經歷流血的過程而實現的。歷史進程表現出與“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相反的路徑。
秦人自稱這種通過軍事途徑解決統一問題為“義兵”。《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史記》中五次出現“義兵”的說法,其他四處,一處沒有明確指代對象,三處都是指反秦武裝。對于秦王政說韓、趙、魏、荊、齊等國“倍約”“倍盟”“畔約”“為賊”“為亂”,于是“興兵誅之”,“舉兵擊滅之”,“興兵誅暴亂”,即所謂“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史記》均予以客觀記錄,而《秦始皇本紀》的篇末說:“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賈誼《過秦論》對秦的軍事成功,即使不是高度稱頌,也是給予了充分肯定:“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秦始皇時代“續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自詡“義兵”的勝利者似乎擺脫了儒家對“嗜殺人者”的批判,而司馬遷在客觀記述秦人宣傳語言的同時,也在筆下保留了對“秦暴”(《史記·趙世家》)的指斥。
六、“法令由一統”與“別黑白而定一尊”
《左傳·昭公七年》記載,對于臣下分君權的企圖,有“一國兩君,其誰堪之”的嚴厲指責。提出這一見解的人,還引用了上文說到的《詩·小雅·北山》的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溥天之下”作“普天之下”。《孟子·萬章上》也寫道:“《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說:“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過,孟子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解釋,與一般的理解似乎略有不同。孔子所說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見于《禮記·曾子問》和《禮記·坊記》,然而都寫作“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很顯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或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體現了“大一統”政體和專制行政的關系。
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論即以君主權力的一元化為思想基點。《太平御覽》卷三九○引《申子》也說,這種高度集中的君權,是以統治天下為政治責任的,“明君治國”,“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和廷尉李斯等奉命“議帝號”時,有頌揚秦王政的話:“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然而后來政治形勢的演變,形成了另外的局面,即《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李斯建議焚書時所謂“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史記·李斯列傳》對同一史事的記述,作“今陛下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對于“白黑”,司馬貞《索隱》:“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就是說,國家政治、社會禮俗、民間輿論,其黑白真偽,都由“一尊”做出決定性的裁斷。
后來秦二世、趙高執政時所有政治決策都“定”于“一尊”的情形,《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按照趙高的語言,即“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其中“主重”二字,值得細細品讀。賈誼《過秦論》對于導致秦亡的政治氣候,做了如下分析:“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賈誼還有一段言辭淋漓的政治史評論:“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秦始皇“足己不問”,“行自奮之治”,對于“自”“己”資質能力的盲目自信,不能聽取正確的意見和建議,“遂過而不變”。而“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最終導致了秦王朝的短促而亡。司馬遷贊嘆道:“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他對賈誼關于秦政的分析,是高度贊同的。也就是說,無論是“別黑白而定一尊”還是“別白黑而定一尊”,這種由“一尊”專制專斷的政治方式,司馬遷完全同意賈誼的批判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