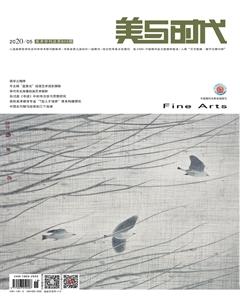7-8世紀庫木吐喇石窟的漢風壁畫研究
洪寶


摘 要:龜茲地區的石窟壁畫繪制于4世紀至8世紀,壁畫的樣式基本是統一的龜茲風格。然而龜茲地區的庫木吐喇石窟卻是特例,它有大量的漢風壁畫的遺跡,呈現出中原的繪畫風格。由此,文章對7-8世紀的庫木吐喇石窟漢風壁畫進行研究。
關鍵詞:庫木吐喇;壁畫;漢風
庫木吐喇石窟位于新疆庫車縣西南約30公里的渭干河出山口及東岸的崖壁。地處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北端的庫車縣,在古代是龜茲國的所在地,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3世紀經絲綢之路傳到新疆境內,通過開鑿石窟、繪制壁畫、塑造佛像等方式,向所到之處的居民傳播教義。佛教經過龜茲、高昌等地一路傳到敦煌,約5世紀再由敦煌傳到中原,在中原生根發展,而后又對周圍地區產生影響。
一、新疆境內的佛教石窟壁畫
從今天的佛教石窟壁畫遺跡來看,新疆及甘肅境內有多個石窟群。3世紀初到9世紀,龜茲地區修建了大量佛寺,規模較大的有克孜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在今天吐魯番附近的高昌地區,也存在著不少石窟群,較大規模的有柏孜克里克、吐峪溝石窟。同樣位于交通要道的敦煌地區,從4世紀到14世紀,開鑿了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其中保存著大量的壁畫、雕塑。
克孜爾石窟擁有236個洞窟,而庫木吐喇石窟現發現有112個洞窟。從克孜爾石窟沿渭干河東行若干公里,便可到達庫木吐喇石窟。克孜爾石窟開鑿的時間大約在4世紀,約到8世紀逐漸被廢棄,持續了三四百年,庫木吐喇石窟開鑿的時間稍晚于克孜爾石窟。“公元630年,玄奘路徑這里,記載龜茲城西門外,般遮于瑟‘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迦藍,唐言奇特,其方位、地段等與庫木吐喇一帶的遺存相符。”
從現存佛教壁畫遺存來看,新疆境內的石窟壁畫大都有典型的地域特點,學者們稱之為龜茲風格,以克孜爾石窟壁畫為代表。其構圖上運用了菱形格的形式,鱗片似的交錯延展,橫、豎、斜成行的菱形格組成大幅裝飾圖案,簡潔而有趣。菱形格內大部分描繪獨立的佛傳故事,人物形象、樹林、飛鳥走獸大多以細線勾勒,再施以色彩,色與線渾然一體。人物形象運用了西域的凹凸法,在面部、身體軀干結構部位,用深淺逐漸過渡的手法進行暈染,塑造高低起伏的形體(圖1)。
龜茲地區的佛教到公元4世紀進入鼎盛時期,直到8世紀中葉,唐朝中央政府的力量被安史之亂削弱,無法保持龜茲已有的穩定政治局面,龜茲的佛教也開始衰弱。龜茲地區的石窟壁畫繪制于4世紀至8世紀,壁畫的樣式基本是統一的龜茲風格。然而龜茲地區的庫木吐喇石窟卻是特例,它有大量的漢風壁畫的遺跡。
二、佛教石窟壁畫對中原石窟壁畫的影響
(一)佛教傳入中原之前的中原繪畫
佛教傳入中原之前,魏晉六朝時期的繪畫現存甚少,從畫像石、畫像磚、墓室壁畫以及傳世畫作等遺存看,繪畫的圖像偏重線條造型,形象簡潔。由長沙楚墓出土的帛畫可見,當時線條主要勾勒出形體范圍和邊界,對物象的描繪更依賴于概念化的平面組合,顯現出線條互相間的動感韻律。在河北望都的東漢一號墓壁畫的人物,線條顯得比長沙楚墓更豐富,增添了寬粗線條表現衣服結構和褶皺,粗細相間的線條在表現物象產生生動變化的節奏感。這種用細線描繪對象的風格亦見于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女史箴圖》等傳世畫作中。
(二)佛教傳入中原對中原繪畫的影響
佛教傳入中原初期,大量寺廟、佛像的修建以及壁畫等的繪制,帶來印度西域的藝術樣式。
北涼時期敦煌壁畫的風格如敦煌莫高窟272窟的供養菩薩,明顯脫離中原之前線條描繪的方式。人物的眼眶周圍出現寬色帶,手臂、上身、腹部的色帶表現肌肉結構,這種手法源自印度的佛教圖式。人物造型是薄衣輕紗,服飾配飾也以質樸簡潔為主,對物象結構描繪用凹凸法,呈現物體的高低明暗。
可見,早期中原佛教壁畫是對印度傳來的圖像進行機械的接受和臨摹。隨著佛教傳播的持續深入,繪制過程中畫師慢慢理解和結合本土的方式創造出不一樣的圖式,如敦煌莫高窟285窟,中原的以線描為主的風格和外來的凹凸風格同時出現。到了隋唐時期的敦煌壁畫,如敦煌莫高窟276窟西壁的文殊菩薩,人物身體輪廓、衣紋飄帶主要由長線組合,完全不依賴于陰影,結構的交代基本依托線條。這類菩薩形象在敦煌莫高窟第112窟、第159窟及榆林窟第25窟均有可見。
石守謙教授曾談及盛唐白畫之成立與筆描能力之擴展的問題,提出:“畫家逐漸將學自西來凹凸法的描繪結構之能力,拿來增加了傳統所喜愛的筆描內容。”“筆描舊傳統在盛唐時的再生。此再生不僅使盛唐的筆描大異于漢晉者,而且也不同于凹凸法所附帶的線描性格。”“印度佛畫原有的精致凹凸暈染,在此相當長的傳遞過程中,原意逐漸淡薄,僵化,到了中國時終于成了徒具形式的技法母題。”克孜爾石窟第17窟的佛像或佛傳故事人物形象,與敦煌北涼272窟極為相似,而克孜爾壁畫人物的帶狀色帶過渡更緩和,大部分濃淡漸變關系處理得更自然。
三、中原漢風對庫木吐喇石窟壁畫的影響
當中原佛教壁畫發展出自身風格之后,其逐漸影響著周圍地區的佛教壁畫。19世紀德國學者勒科克,隨普魯士王國吐魯番考察隊進行考察,提到:“當佛教種子在中國土地上也結出果實”,“隨著一股反沖的浪潮,把原來由中國西部傳入的,而后來已中國化的佛教又送了回來”。庫木吐喇的漢風壁畫大概集中在第4、11、12、13、14、15、16、17、36、42、45、61、66、71、75窟。“北京大學考古系曾對庫木吐喇第14窟主室墻泥中草樣做過碳十四測定,測定年代距今(1982)為1210±35年,即唐天寶年間(742-756)”,其他漢風壁畫大致也可推測與庫木吐喇第14窟年代相同,大致繪制于公元7到8世紀。
(一)庫木吐喇石窟壁畫的歷史背景
640年,唐朝設立安西都護府,大量軍隊駐扎龜茲。《舊唐書·西戎傳》記載:“高宗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異龜茲等四鎮,移安西(都護)依舊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以西四鎮城堡并為賊所陷。”692年,唐朝重設安西都護府。“武威軍總管王孝杰、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于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武則天信奉佛教,佛教給予遠離家鄉的士兵民眾精神寄托,于是大量漢僧來到此地,修寺開窟,繪制壁畫,帶來中原化的佛教繪畫風格,包括壁畫的描繪方式、物象造型。唐朝新羅僧人慧超于724年游學印度歸來,路過龜茲。他所著的《往五天竺國傳》云:“又從疏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即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此龜茲國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蔥韭等也。漢僧行大乘法……”
(二)從題材上看中原漢風對庫木吐喇壁畫的影響
唐朝時期,西千佛洞、榆林窟以及莫高窟的壁畫大量出現經變畫的題材。庫木吐喇在這一時期的壁畫也出現了大幅經變畫,如第14、15、16窟,其構圖形式與敦煌地區的壁畫極為相似,且經變畫中多標有漢文榜題。
《觀無量壽經變》是盛唐敦煌壁畫經常出現的題材,庫木吐喇石窟壁畫亦出現這一題材。受年代變遷、自然、人為因素影響,庫木吐喇的許多洞窟破損嚴重,僅從遺存中所見,庫木吐喇第16窟主室南北壁各有一鋪大型經變畫,構圖相似,同樣是中堂式畫面兩側配以立軸式條幅,其中南壁的經變畫便是《觀無量壽經變》。
學者馬世長在《庫木吐喇的漢風洞窟》中這樣描述庫木吐喇第16窟的經變畫:“畫面被盜割多處,殘跡中有漢式宮殿建筑和著漢裝的人物,殘存壁畫情節雖不連貫,但仍可辨識其內容為未生怨。”德國學者格倫威德爾在1905-1907年考察時如此記錄:“人們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寫著中文榜題的特別畫面:佛陀、目犍連和舍利佛面對一僧人,這旁邊是一幅類似的畫面,下邊又是一座宮殿,兩個身穿白衣的人跪在宮殿的院子里……”日本學者渡邊哲信記錄的漢字榜題為“佛從歧阇崛山中沒王宮中見韋提夫人自武時”“韋提夫人觀見水變成冰時”。前輩學者推斷此立軸應為“十六觀想”。
“未生怨”與“十六觀想”是《觀無量壽經變》中經常出現的內容.據日本學者熊谷宣夫研究,庫木吐喇第16窟主室南壁中心所繪為《西方凈土莊嚴相》。這種中堂繪《西方凈土莊嚴相》,西側立軸條幅繪“未生怨”與“十六觀想”的題材和構圖形式,在敦煌地區壁畫中數量眾多,如敦煌莫高窟第45窟、西千佛洞第18窟、榆林窟第25窟等。
(三)從裝飾圖案看中原風格壁畫對庫木吐喇壁畫的影響
1.卷云紋
云在古代被視為祥瑞。《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名。”晉杜預注:“黃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紀事,百官師長,皆以云名號。”因此,古代中原地區都把云作為傳統的裝飾紋樣,以示祥瑞。漢代流行神仙思想,神仙方士把云氣表現作為天地間交往的工具,以流云為紋的裝飾圖案屢見不鮮。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中卷云紋是常見的圖案,這些卷云紋也出現在庫木吐喇的《觀無量壽經》《藥師凈土變》等經變畫中。
2.花紋邊飾
敦煌地區的石窟壁畫中,幾乎每個唐朝洞窟都有花紋邊飾,這種富有裝飾性的花紋以團花、卷草、茶花等紋樣進行重復。這種邊飾幾乎僅在庫木吐喇壁畫中出現,龜茲地區的其他石窟幾乎難覓其蹤,森木塞姆也僅有少數幾例。它們雖作為襯托,但精美程度令人無法忽略。格倫威德爾在記錄庫木吐喇緊那羅洞(庫木吐喇第16窟)中也稱之為“華麗的邊飾”,并有手稿記錄。窟中南壁的《觀無量壽經變》與東西兩側的“未生怨”“十六觀想”之間的邊飾,與西千佛洞的第18窟《觀無量壽經變》與“未生怨”之間的邊飾幾乎出于一類模本。
3.人物造型
佛像造型源于印度,傳到敦煌地區后逐漸呈現明顯的漢地風格,無論是佛還是供養菩薩、天人、僧眾多是褒衣博帶,不袒雙肩,衣服領子以左壓右。菩薩梳高髻,戴小花鬘冠,胸前佩戴細瓔珞,上身披巾橫于胸腹之間,是標準的唐裝菩薩像。
在庫木吐喇的漢風洞窟內,也可看到以線條塑造的佛、菩薩、飛天有著中原人的特征。其眉毛如柳葉,眼睛細長,鼻翼豐厚,手掌寬而飽滿。漢風佛像在披著袈裟時不袒露右肩和右臂,與中原地區流行的袈裟披著方式一致。庫木吐喇漢風壁畫的飛天形象或乘祥云,或飛舞于卷云和華蓋周圍,頭戴寶冠,胸前戴瓔珞,手臂纏繞著長長的飄帶、輕紗飛舞于天際,或吹奏樂器,或手捧鮮花,與敦煌地區壁畫如出一轍,如庫木吐喇16窟的西方凈土變、藥師變(圖2)。
4.華蓋
在敦煌地區石窟壁畫中,華蓋出現在大型經變畫和說法圖中佛、菩薩的頭頂,如敦煌莫高窟112窟、西千佛洞第18窟、榆林窟第25窟等,華蓋后方常有菩提樹的花葉相襯。主佛釋迦摩尼佛頭上的華蓋最為華麗,菩薩頭上也有較為輕盈的華蓋。盛唐時期華蓋最繁復,上有瓔珞裝飾,寶珠串成重疊的層次,華蓋下端有紗網裝飾,有的瓔珞下部垂有鈴鐺,可見庫木吐喇第14窟、第16窟的經變畫。
5.千佛
在洞窟繪制千佛的壁畫是中原地區經常見到的。克孜爾石窟也有千佛的壁畫,但其千佛都繪制在大小規整的菱形格中,用色富有裝飾性,菱格之間不用相同的顏色,按一定規律排列。而庫木吐喇受漢風影響的千佛,基本不畫界限明顯的分隔,僅以千佛的形體形成豎行或者橫行的布局,千佛的形象基本一致,底色大多統一為白色,是明顯的漢族傳統的繪畫手法。
四、結語
一直以來,人們談到西域壁畫,更多側重談外來文化的影響,追尋其源頭。當外來文化在本土扎根并發展,也會反之對周邊甚至更遠的地區帶來影響。這些不同時期各具風格的壁畫,反映出7到8世紀西域地區和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庫木吐喇石窟漢風洞窟壁畫的存在,在今天看來更具有現實主義的啟示。
參考文獻:
[1]霍旭初,王建林.丹青斑駁 千秋壯觀:克孜爾石窟壁畫藝術及分期概述[M]//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龜茲佛教文化論集.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3.
[2]吳焯.庫木吐喇石窟壁畫的風格演變與古代龜茲的歷史興衰[M]//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龜茲佛教文化論集.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3.
[3]賈應逸,買買提·木沙.歷史畫廊:庫木吐喇壁畫研究[M]//中國新疆壁畫全集:庫木吐拉.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5.
[4]石守謙.盛唐白畫之成立與筆描能力之擴展[M]//石守謙.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5]勒柯克.高昌:吐魯番古代藝術珍品[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6]陳鐵梅,原思訓,王良訓,等.碳十四年代測定報告:六[J].文物,1984(4).
[7]馬世長.庫木吐喇的漢風洞窟[M]//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龜茲佛教文化論集.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3.
[8]格倫威德爾.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M].趙崇民,巫新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9]渡邊哲信.西域旅行日記:卷四[M]//上原芳太郎.新西域記:上卷.東京:有光社,1937.
[10]趙麗婭.庫木吐喇石窟佛像的藝術風格及其特點[J].法音,2017(1).
作者單位:
廣州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