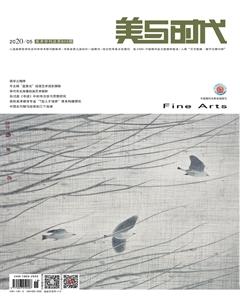地域視角下的漢代四川畫像磚研究
黃欣
摘 要:漢畫像磚在今山東、河南、陜西、云南、貴州等地都有發掘。四川以成都周邊出土的東漢中后期實心畫像磚數量較多,藝術造詣較高,是我們了解兩千多年前神秘瑰麗的四川漢代社會的活化石,它與全國其他地區的畫像磚相比具有明顯的區域藝術特征。
關鍵詞:四川;漢畫像磚;地域特點;藝術風格
基金項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廳地方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項目(DFWH2019-039)研究成果之一。
漢代是一個政權相對穩定、民族融合、商業手工業發達、對外貿易及交流頻繁的封建王朝。漢武帝以禮樂文教輔助統治,表章六經,設太學、置博士、創秘閣,開“黃門畫署”,后又有漢明帝雅好圖畫,創立畫官、畫室、鴻都門學,皆以“成教化,助人倫”“惡以戒世,善以示后”,發揮藝術的教育功能,為統治者宣揚儒家道德,強調人身依附關系,達到鞏固漢朝的封建統治目的。漢代先民崇尚“謂死如生”“事死如事生”的讖緯學說及宿命論,崇信原始神話傳說等學說思想,加上“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以尊老和厚葬顯示自己的孝行同時,東漢時期外來佛教的傳入使人們對“引魂升天、來世幸福”的追求愈加強烈,漢畫像磚藝術始于戰國至東漢到達頂峰,延續至宋金時期才逐漸衰落,是這個恢宏時代里一顆璀璨的藝術明珠。漢畫像磚繼承和吸收商周青銅紋飾、戰國帛畫及漆畫、秦漢壁畫及雕塑技法基礎,是雕刻與繪畫藝術融合的造型藝術形態,是主要應用于漢代墓室建筑的一種喪葬禮制性磚石藝術。
一、四川漢畫像磚文化綜述
杜宇氏教民務農,蜀人開明氏在川興水利,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工程,大大促進四川的農業發展。《漢書·地理志》載:“巴、蜀、廣漢……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江水沃野……民食稻魚,亡(無)兇年憂。”漢時成都成為西南政治、文化商業中心,躍居五大商業都市之一。
漢代崇尚“以孝治天下”,東漢王充《論衡》提出的“孝親才能忠君”思想,加之天人感應論、社會崇信巫術的風氣極盛,使統治者和達官貴族不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建造陵墓,有錢人家甚至平民百姓不惜傾家蕩產也要追隨厚葬的潮流。“察舉征辟”的官員選拔考核制度設立更是讓漢民攀比競爭心理、奢侈厚葬之風到了“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的地步。畫像磚藝術就是這股潮流下的直接產物。《蜀都賦》云:“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可見四川采鹽、制鹽業發達。“秦開五尺道,漢通西南夷”,且“遷六國豪強”的移民措施給西南地區帶來技藝高超的工匠和制磚雕刻技藝,加強了四川地區與中原的民族融合、文化經濟交流,使四川本土的先秦巴蜀文化、巫鬼文化、女神崇拜文化傳統受到中原漢民俗文化的影響。這些社會文化因素都是促使漢代四川地區畫像磚藝術興盛的重要原因。
二、漢代四川畫像磚藝術的分區
東漢中后期是漢畫像磚、畫像石的鼎盛時期,四川出土了大量的漢中期崖墓、磚石墓,集中于成都及其近郊的新繁、彭縣、廣漢、郫縣、新津等地,在今武勝、蓬安、南充、大邑等地發現了漢磚窯及畫像磚。總體來看,漢畫像磚多出自四川岷江主流及支流地區、嘉陵江主流及支流地區,并流行、傳播在四川其他分散的地區。由此可推斷出畫像磚在四川流行和發展的軌跡多出自以成都為中心、范圍不大的南北區域,以及分散的東西區域。四川地區目前出土漢畫像磚多達數千塊,各地畫像磚存在明顯的區域性藝術風格,反映出漢代四川區域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民俗喪葬禮制、大眾審美感知、儒家美學價值的差異性和相似性。根據近年考古發掘及畫像磚內容、風格、形制、特征、出土數量分析可將四川畫像磚分為四個類型:成都型、廣漢型、彭山型、其他型。
三、漢代四川畫像磚類型與藝術風格
(一)成都類型
成都類型包括成都市北和成都以西的雙流、郫縣、溫江、崇州、新津、新繁等地。成都是漢代西南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出土的畫像磚較其他地區也最多,較多反映政治生活、城市繁榮、貴族出行、生產勞動的題材和內容,實為四川成都地區漢代社會各個方面的縮影。其中描繪勞動生產、歌頌贊揚漢代先民勤勞與智慧的畫像磚最為精彩,如《播種》《弋射收獲》《舂米》《鹽井》《釀酒》;反映漢代初期小市場發展的《市肆》《沽酒》《宴樂》《觀伎》《笙歌》;反映剝削階級的享樂生活、森嚴封建等級制度的《收租圖》;《傳經講學》真實反映出漢時文翁興學,“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養老圖》畫像磚反映了漢代尊老養老的制度;《柵居圖》表現四川房屋“干欄式”的防潮、通風儲糧的建筑構造,是四川與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生活交往的實證;首次在四川新都發現的《駝舞》磚為漢代四川與西北邊塞地區、東亞國家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中外歷史文化交流提供實物資料。
成都類型漢畫像磚,出土形制多為高42厘米左右,寬約48厘米左右,色灰,質地細膩的方形實心磚,大多采用翻倒脫模法,銳器刻畫細節修飾畫面,一磚一模,模印結合,如《六博》磚。雕刻手法多平面淺浮雕,間以減地陰線刻或陽線刻,遠看似剪影效果,類似后世版畫風格。工匠善于運用富有生命力的長、圓線條,動感的曲線,使畫面顯得生動流利,而非呆板刻意;善于在長寬不過40厘米的磚面上,可以同時表現五六個人物或事件,運用散點透視方法,將多個內容、場景安排在一個畫面上,使畫面形象更為突出,整體感更強,而且人物形象寫實,姿態生動。如《觀伎》構圖疏密有致,勻稱和諧,富有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情調,顯示出漢代工匠高超的造像技藝,側面可以看出這些民間匠師善于觀察生活,具有豐富的想象力與非凡的藝術感知力。
(二)廣漢類型
廣漢類型以四川廣漢為中心,包括了周邊的彭州、新都、什邡、德陽、綿陽等地。廣漢型的分布地區大多居于成都型的北邊,岷江北段,地形較平坦,多處河谷地帶,漢時經濟較發達。廣漢型畫像磚在繼承成都型以及吸收三星堆古文化的基礎上演變出自己的特征:形制與成都型截然不同,多為長條形,一般長20~30厘米,寬6~10厘米左右,色灰,含沙量大,所以磚體較粗糙;反映政治生活的題材較少,多反映漢民的生產生活,以及漢代莊園經濟的發展狀況,較成都型更重世俗。如表現經濟生產的《播種》《市井》;表現人們娛樂活動的《六博》;歷史故事《四皓護太子》;神話故事的《四靈磚》《仙人戲馬》《采仙藥》《西王母》等;還出現了關于“璧”的題材,如《聯璧》《雙鳳戲璧》《錢幣、聯璧》。廣漢型畫像磚與成都型相比,藝術手法近似,又有所區別,由于土壤含沙量大、燒磚技術的不足、優秀工匠的匱乏,廣漢型較成都型畫像磚形制更小,大多為長條形、線條更為粗獷,人物更加簡潔化。它仍以線刻表現為主,但更多地使用高浮雕的技法,物體形象高凸出磚平面,細部有凹有凸,畫面富有立體感,更加飽滿。
(三)彭山類型
彭山類型以四川彭山為中心,包括周邊的峨眉、樂山、宜賓、仁壽等地。彭山型大多位于成都以南、岷江下游地區,地勢大多較高,畫像磚出土的規模較成都型和廣漢型更小,數量也更少。彭山類型畫像磚形制較小,仍然是以長條形為主,內容題材多為引魂升天、神仙故事題材,如《西王母》《伏羲女媧》,多紀年方磚、字磚,如峨眉出土的《建武十九年》。彭山型畫像磚藝術風格較成都型、廣漢型有明顯的差異性,表現生活和歷史故事的內容減少,引魂升天的題材增多,裝飾性和實用性更強,可見彭山區域的漢代人民對升仙思想、來世幸福的追求最為強烈。
(四)其他類型
距離成都較遠、較分散的其他四川地區,包括漢時為巴北郡的嘉陵江流域周邊的蓬安、南充、武勝,漢巴東郡的廣元、旺蒼、劍閣,成都以西的渠縣、西昌、蘆山等地。這些地區漢畫像磚出土數量較少,較分散,大多近年還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是組成四川漢畫像石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他類型地區的漢畫像磚多為紀年磚、花磚或字磚雜糅,與條形磚的規模大小相近,題材內容故事情節少,畫面多用分格式來構圖,帶有邊框,用文字裝飾圖案或用小的圖案裝飾字磚。大多是具有模印裝飾意味和象征意義的各種紋樣,一般有菱形紋、幾何紋、云紋、斜方格紋、規矩紋、柿蒂紋等。可見其他型的漢畫像磚是單純作為墓室的建筑構件存在,較其他三種類型更為簡潔樸實,審美型和裝飾性降低,實用性和專門性要求變高。
四、漢代四川畫像磚的審美文化精神
畫像磚除具有建筑性和裝飾性功能以外,內容大多可以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產生活經歷,有墓主“人間再現”的性質,類似于后世的“墓志銘”在漢代最早的體現。畫像磚這種古老的漢代“墓志”形式反映了漢民俗文化基因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長河中的流轉演變、延續和傳承。四川畫像磚主題鮮明,寫實的造型手法與藝術夸張相結合,充滿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色彩。較全國其他畫像磚類型來說,四川畫像磚少了具有矛盾沖突、曲折離奇、史詩般英雄頌歌的題材和內容,更重世俗的平凡生活,鄉土氣息濃郁、內容表現多是放在刻畫下層勞動人民的勞作形象、四時辛勤、簡淡寧靜的田園生活上,著重凸顯四川桑蠶、井鹽、蜀錦、釀酒、農事發展的地域特色,以及對下層勞動人民勤勞勇敢、勞動創造美好生活的歌頌,對剝削階級隱晦的批判,形成一種積極樂觀、熱愛生活、勤勞樸實、昂揚向上的“特殊四川漢代精神”。
五、結語
四川漢畫像磚審美氣象深沉雄大,匠心獨具,藝術題材褒貶善惡,藝術精神體現漢代先民積極進取的樂觀主義精神品質。四川是漢代畫像磚發現的集中地區之一,獨具代表性。對四川畫像磚的研究有助于探索漢代四川地域間的文化交流、生產生活、民風民俗、藝術審美。
參考文獻:
[1]高文.四川漢代畫像磚[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2]吳曾德.漢代畫像石[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3]馮漢驥.四川畫像磚墓及畫像磚[J].文物,1961(11).
[4]蒲永紅.四川與河南南陽漢畫像磚比較[D].四川師范大學,2011.
[5]袁曙光.四川漢畫像磚的分區與分期[J].四川文物,2002(4).
[6]范小平.四川畫像磚藝術[M].成都:巴蜀書社,2008.
[7]羅二虎.四川漢代磚石室墓的初步研究[J].考古學報,2001(4).
[8]朱存明.論漢畫像石的地域分布及特征[J].地方文化研究,2013(1).
作者單位:
西華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