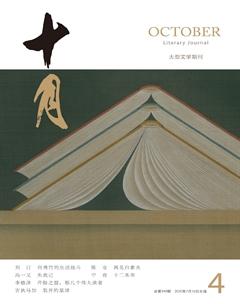我用機器思維寫小說
顏橋
我大約有十八年沒正兒八經(jīng)創(chuàng)作過中短篇,二零零二年,我大三,第一篇正式小說發(fā)表在上海的一家著名雜志,那段時間,還陸續(xù)拿了些小獎。我依稀記得,獎金是當(dāng)年學(xué)費的三倍,我當(dāng)時甚至無恥地認(rèn)為,自己或許能成為一個不錯的作者。
工作后,環(huán)境改變,心境也隨之變化,再也拾不起寫作的欲望。雖有創(chuàng)作,但更多了實用考量,它們不是純粹意義的文學(xué)。去年底,我忽然又找到寫作的樂趣,我戲稱自己為“冰柜里來的人”。冬眠醒來,滄海桑田,世界大不同了,必須擯棄舊有經(jīng)驗,重新找到一種屬于自己的創(chuàng)新之道。
一度很害怕寫創(chuàng)作談,我認(rèn)為:小說是一種呈現(xiàn),不是一種解釋。你做的菜不好吃,你卻寫個菜譜解釋,于事無補。不過,我還是樂于表達我個人更接近“機器思維”的創(chuàng)作法,它代表我的“一種小說觀”。
觸點
觸點像唱歌找“調(diào)門”,唱戲找“氣口”,吃面找“面頭”。小說家在“觸點”階段是純感性的,不加諸理性。《魚麗之宴》的靈感誕生在我去小區(qū)買菜,忽而從頭頂落下一個竹籃,二樓要一籃韭菜。賣菜大媽嘆氣,寧可死在樓上,也不愿下樓買菜。“竹籃打菜”的畫面,外加那句話,太可樂了,有很強的“生活感”。在年輕化的小區(qū),御宅族特多,有句老話,讓宅男下樓的終極交通工具,只有救護車。觸點有了,一個嘴巴刁鉆、卻下樓困難的宅男美食家,“人物”呼之欲出。
《干杯,元神》則是多年前,參加一位異性朋友聚會,她掏出自己的毛絨玩具,她稱呼它們?yōu)椤霸瘛薄;钸@么大,頭回去參加“毛絨玩具派對”,還挺尷尬,我一度懷疑這是一場惡搞,直到她演示她和元神們?nèi)ヂ眯械摹罢掌恪保@些玩偶就和“真人”似的,是一種“心理投射物”。那個派對,讓我印象深刻。
無獨有偶,我朋友圈有個還算知名主持人,她每次去旅行,有一只棕色的小熊,每次說晚安,都配張小熊躺在旅館床上的圖,蓋著被子……她倒像是陪游,毛絨玩具是主人。這不是孤例,或許女性中相當(dāng)普遍,這種玩偶的亞文化,引發(fā)我的興趣。
在日本秋葉原旅行,我見一位小女孩,背著比自己還大的熊本熊,她一邊走,一邊和“熊”聊天。這些細節(jié),觸動了我,獨生子女一代,與玩偶說話,仿佛玩偶就是另一個自己,這當(dāng)中的“豐富性”,無須一一辨清,圍繞一只玩偶,便可榨出“物件”背后的“隱痛”。
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要不忘“一口活氣”,一個觸點,也是創(chuàng)作原初的興奮,要守住這口氣,不然,再好的“技術(shù)”,也救不活“尸體”。
范式
范式一詞,是美國科學(xué)哲學(xué)家托馬斯?庫恩在《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中提出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存在“范式”。創(chuàng)新,源自對舊范式的改造。譬如“美食風(fēng)土小說”這一類型,早已在汪曾祺、陸文夫等前人筆下登峰造極。這一范式特點:食物高度“在場”,一切繞著“食物”轉(zhuǎn),敘述者自帶專家口吻,食物中心性被高度凸顯。
突破范式:《魚麗之宴》是一篇“偽美食小說”(電影里有一種“偽紀(jì)錄片”,或可比附),通篇像煞有介事談?wù)撌澄铩⒋┎迨匙V,卻無人關(guān)心食物,甚至無人關(guān)心味道。每個人都陷入關(guān)于食物的往事里,傾聽者無心旁聽,一味敷衍。
它借鑒美食小說的外殼,卻有意識打破美食小說基本范式,敘述者也不是洋洋自得地聚焦食物,或敘述者吃魚的動機,只是為了一枚鉆戒。食物是一張孤獨的網(wǎng),什么也沒網(wǎng)住。它試圖用現(xiàn)代主義解構(gòu)人與食物之關(guān)系。
與“魚”有關(guān)的菜,也是一種符號:家常菜“鯽魚豆腐”,可能意味情感漠視與冷暴力,它根本不能算“菜”。喜愛吃“法國濃味燉魚”的女白領(lǐng)(你知道,法餐要吃得很慢、很悠閑那種),她內(nèi)心一定渴望一種儀式感,因為在城市里一切駐留不定,流沙一般,她需要安定,需要某種程度的尊嚴(yán),這是她離開這個城市前小小的愿望。做“花膠石斑魚羹”老板呢,說不好,只能感受他。他破產(chǎn)了,這是他最后的“口腹之欲”,一定得是稀缺之物吧。他馬上會從高處掉落,打回原形,重新奮斗。他必須撫慰恐懼,食物必須彌足珍貴,這也是他再次征戰(zhàn)風(fēng)車的勇氣……一切都是你的感受,真正的秘密,只有他知道。
這種抽取本質(zhì)屬于數(shù)學(xué)抽象,用機器學(xué)習(xí)的術(shù)語,叫“提取特征值”。好比畢加索畫的牛,并不是真實的牛,寥寥數(shù)筆,提取出一只牛的“特征”。
小說創(chuàng)新=抽取范式→突破范式。
范式是小說家的“思維原型”。小說家生于范式,死于范式。范式是“框架算法”,細部紋理依然使用“藝術(shù)感覺”,這樣小說才不會成了僵硬“圖解概念”。
信息
小說是一門信息學(xué),這是小說的本質(zhì)。嚴(yán)肅文學(xué),是比拼單位長度的信息密度。你必須在一定時間段,持續(xù)供給讀者新的信息:人物的信息,情節(jié)的信息,情緒的信息……讀者一旦沒有新的發(fā)現(xiàn),書寫就無法縱深,成了平面上的詞匯游戲,進而產(chǎn)生厭倦。
伊朗導(dǎo)演阿巴斯說,電影是一個多面體,你只是讓觀眾看到一個面,想起其他的面。任何藝術(shù)都如此,中短篇更是如此。這不是關(guān)于信息的鋪張,而是關(guān)于信息的精簡、集中與壓縮,讓讀者聯(lián)想更廣義的“留白”。
我記得當(dāng)年教會我寫作老師說的“三行定乾坤”,只有三行的機會寫出人物,或許只有唯一一句對白。你必須在大腦演練數(shù)十次,哪一句對白,一定是這個人物最想說的,最準(zhǔn)確的。
寫作便是由右腦與左腦交替產(chǎn)生的智識算法,這是說小說,也是你認(rèn)識世界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