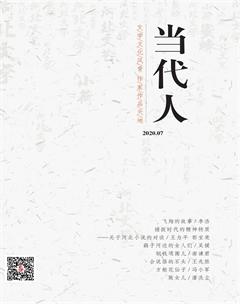月光灑滿高原
早晨,我佇立在高原的山野之上向遠處眺望:峽谷把視線徐徐拉開,像一幅山水畫展開了她的多姿與妖嬈,自然的色塊與激情像爆發的火山巖漿,從風里流出大滴的墨團,重重地甩在宣紙上凝固,再也化不開。
漫山遍野的花朵像鳥兒張開了嘴巴,露水從草尖上醒來,每一滴露珠里,都有一粒寶石的光澤在閃耀。
這里是觀察“雞鳴三省”的最佳位置,可以一眼望見黔、滇、川三個省份的屋舍與農田,樹木、炊煙與行人。
三條水質不同的河流日夜奔流,像一條淺綠色飄帶在高原大地逶迤而過,串聯起三個古老的地域:云南昭通、雄縣和威信縣,四川瀘州市敘永縣和貴州畢節的雞鳴三省村。
哦,三個省份的多個民族,擁有各自的語言和民俗,身上流著各自祖先的血,卻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遭逢,相依為命。千百年過去,他們休養生息,載歌載舞,各自安好。這讓我想起老子說過的話: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偉大的先哲,他以高度的概括力,短短的兩句話就描述了古人近乎原始混沌的生存狀態。小國寡民,安貧樂道,刀耕火種,自生自滅,當然,老子在《道德經》中還有一句“不出戶,知天下”,似乎是對前者表述的補充。我認為這句話只適用于兩千年前的農耕社會節奏,在那個時代,生靈的需求簡陋而單一。較之眼下令人恐慌的工業文明,無論農耕多么“環保”,都歸類于落后的體制結構。
時光悠悠行至當下,一切都變了——比如我早晨還在山東的床榻上昏睡,吃著魯地的飲食,而此刻,我卻站在云貴高原上鳥瞰河流、云霞與霧嵐。心潮澎湃,感受時光的變遷,生靈的演化,大地的滄桑。在當今信息暢通的網絡時代,雞鳴三省的典故,注定打破封閉格局,成為歷史景觀,成為坐標與見證,成為一塊地理意義上的“活化石”。
2
天剛剛放亮,苗寨里的女人們早早起床,在灶膛前點柴生火,讓屋頂冒出第一縷炊煙,勤勞的苗族女人,一生都在哺育兒女、做酒釀、蠟染、剝苘麻中度過。高原的水土好,讓苗族女人個個生得水靈白嫩,皮膚細膩,性格溫柔,說話聲音像唱歌一樣悅耳動聽。
苘麻,這種在我童年故鄉土坡上肆意生長的普通植物,到了貴州畢節七星關的大南山苗族山寨,經過苗族姑娘的纖纖手指點石成金,便有了舉世聞名的染布工藝。在苗族山寨,我看到一塊塊的藍印花布在繩子上晾曬,那些好看的圖案與花紋,飛禽走獸或花鳥魚蟲,都在布上神奇復活,向世界傳遞吉祥。她們一生的好時光都在與一塊花布廝磨,在木屋中,在爐火旁,守著一方木窗欞,聽著靜夜的風聲和雨聲,把全部的愛意與心思織進土布美麗的圖案中,這讓我瞬間生出敬意:苗族姑娘是在用生命寫一首長長的詩篇。
苗寨里的男人們則在坡地上勞作,種植苞谷和煙葉。牧羊人會趕著羊群出現在野花怒放的山坡。無邊的森林在遠山中靜默。牧羊人懷抱皮鞭,就這樣在年復一年的勞作中丟失了歲月,最終化為泥土,成為山野的一部分。山坡上遍布松林和墓碑,陳年的落葉,破碎的石塊,茅草和瓦礫間隱藏著多少生靈的秘密?
在此之前,我曾經無數次構想苗族山寨,甚至虛擬自己是苗寨的一員:在這里,我隱居群山深處,偶爾出沒于眾多生靈之中,時常騎一輛單車行進在春天的小路,早晨林間的霧靄和山寨的炊煙混雜一處,山雞在樹叢里咯咯鳴叫,各種氣息和聲音歡快地撲打在我的臉上和身上。春天的燥熱像醞釀了一冬的春雷,在我體內隆隆有聲,隨時都有可能落下一場陣雨。而殘橋路畔,有我的茅棚屋舍,屋內陳設簡易,但足可以躲避世間風雨;粗茶淡飯,足可以唇齒留香;一盞油燈,足可以照亮詩書黃卷。
在山野行走的過程中,我知道腳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埋藏著一段故事,有的被遮蔽得太久了,需要深深地挖掘才能浮出地表,還原真相。這些故事可歌可泣,屬于另一個勤勞的民族。
3
最早挖掘到的,是一個與土司莊園有關的故事,腦海里涌滿了歷史的場景與畫面,比如太陽下的祭典儀式,悠長的牛角號聲,烈酒血一樣悲壯,神靈之蝶在天空飛舞。
縱覽莊園豪華典雅的格局與氣派,你有理由想象莊園主當年如何顯達尊貴,森嚴的等級是封建王朝的本質模式。當然,外在表現無非是前呼后擁,一言九鼎,眾星捧月。
其實,始于元朝的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用來統治和解決西南少數民族的“緩沖地帶”,大屯土司莊園主余達父順理成章地承襲了祖上的冊封,但縱觀他的一生,會發現其本質上卻是一位革命者和法學家。
像一盞燈,他生前的光亮在黔西南一帶流傳不滅,映照高原大地。
如今,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間的大屯土司莊園只剩下了一座空空的建筑,它像各地巍峨的莊園一樣高大威嚴,客廳寬敞,居室幽暗,花園糧倉,雕梁畫棟,前院連接著后院,院墻高大森嚴。但它們擁有的共同點是一律落寞幽寂,散發陰氣,屋檐下方蝙蝠出沒,傳遞莫名的恐懼氣息。
似乎一切都在,卻又都不在了——籬墻邊的山茶花開得火紅熱烈,靜夜的月光依然照耀,貓與鼠在屋頂穿梭——從遙遠的朝代繁衍至今,一代又一代。
只有舊磚瓦在講述過往的榮耀或屈辱,勝利與失敗。
我曾經去過幾處中國有名的莊園,諸如山西祁縣喬家大院,陜西米脂姜氏莊園,西藏的帕拉莊園,山東棲霞的牟氏莊園,山東濱州的魏氏莊園等等。這些莊園都曾經擁有輝煌的歷史,又在時間的某個節點衰敗,似乎是一種歷史必然結局。在人們津津樂道莊園輝煌的表面時,我卻愿意繞開正面的敘事,去探尋被時光遺漏的縫隙和蛛絲馬跡,結果驚訝地發現一個共同的細節,那就是所有的莊園在儀式的背后充斥著不為人道的隱秘與悲酸,諸如親人背叛、女兒與仆人私奔、突如其來的陰謀與死亡……詭異的明爭與暗斗成為常態,無論多強悍的成功者,江湖傳說中老奸巨滑的大佬與強人,最終都逃不過人性的局限和時間的計謀,當生靈置身于錯亂的迷宮,更躲不開命運之手的擺布。
4
高原的夜空,天上的星星似乎只剩下了最后七顆——在頭頂熱烈地照耀,照耀著我們激蕩的心潮,來自遠方的心靈與之遙相呼應,早已點燃一簇篝火,歌唱,舞蹈;高高的野嶺仙霧氤氳,老鴰的翅膀被露水打濕。山腳下的茅舍,誰家的燈光還在燃燒?狗吠陣陣,山月凄涼,如果稍加諦聽,還會聽到隱約的狼嚎。
不久前,當我讀到這樣的句子:“黑夜,有人踏入了荒原。”——多年前夜行的經歷便會栩栩如生地浮現,令人難以忘懷,因為那種非常態的危險真實可感。我記得自己在十六七歲的年紀,終日無所事事,躲在某一部詩集里憂傷和做夢。我甚至懷疑自己患上了輕度憂郁癥,白天沉默寡言,深夜到荒野上游走。
哦,尖銳而不可預知、殘忍暴烈的黑夜,我就這樣狂熱地迷上了你,像迷上一把寒光襲人的七星劍。
而眼下這個時代的文學,多像一床散發著陽光氣味的棉被,蓋住了我們瑟縮的心靈,讓我們在高原月光的浪尖上尋歡。
泉水淙淙流淌,悉如鼻間的微息。這時,只要一抬頭,就能和高原山頂上那輪明月遭逢,亮閃閃,濕漉漉,飽含深情和樸素高貴的憂郁。這里的月光像是從一個盆里潑下來的銀子,似乎伸手即可觸摸到它一身的清寒雅潔,我望了它一眼,舍不得再望第二眼。
(周蓬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作協散文創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石化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省散文學會副會長。魯迅文學院第十一屆高研班學員。已出版散文集5部,長篇小說2部、短篇小說集3部,在海內外發表作品600余萬字。)
編輯:劉亞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