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刊文摘

當博物館開始重視移民文化
Illusionary equality? Museum politics, practice and immigrant heritage
全球化下的移民使得很多地區的博物館面臨著受眾變得多元的現狀,與之相對的是,博物館在過去建構的“共同的”國家歷史遭遇了挑戰。移民文化在歷史書寫和文化遺產生產方面的重要性使得博物館亟需將多元文化作為策展、收藏和研究工作的基礎,以如實反映它所面向的整個社群的歷史和現狀。
作為近年來深受移民潮影響的國家之一,挪威博物館界已經有了許多呼吁回應移民文化的聲音。同時,挪威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的幾波移民潮和新博物館學的產生和發展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新博物館學對博物館社會功能的強調也自然而然地嵌入了博物館移民文化的討論中。通過前期問卷調查,研究人員篩選了三家注重文化多元性的挪威博物館:呂菲爾克博物館(Ryfylke)、挪威民俗博物館(The Norwegian Folk Museum)和跨文化博物館(Intercultural Museum)。通過敘事研究的方式,作者梳理了三家博物館在工作中融入移民文化的方式。
其中,呂菲爾克博物館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了一系列移民相關的項目,回應從歐洲其它地區來到呂菲爾克的難民潮。其中既有關注移民身份的討論——不論他們的成長環境如何,秉持著怎樣的價值觀和宗教信仰,當他們來到挪威,他們的身份被簡單粗暴地概括成了“難民”,呂菲爾克博物館的項目試圖將他們還原成個體;博物館也有面向在挪威長大的移民兒童的教育項目。民俗博物館和跨文化博物館共同提出了一個名為“挪威的昨天–今天–明天?”的倡議,其中跨文化博物館通過將移民納入工作團隊的方式,使少數群體的聲音能夠充分體現在博物館的決策中;民俗博物館則一直在構筑和豐富由口述史、照片、物件、視頻等構成的移民文化檔案庫,并和奧斯陸大學歷史系合作,將檔案庫開放給研究人員。
研究人員調查發現,在所有給予回應、并有移民文化相關項目或計劃的近20家博物館中,33%的博物館通過常設展來呈現移民文化;52%通過臨時展;43%舉辦相關的研討會或講座;67%會舉辦一些特別活動,例如音樂節或市集。有61%的博物館項目是針對它們所在社區的特殊移民問題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博物館的社會意識。
來源: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2020年,第一期
作者:Grete Swensen & Torgrim Sneve Guttorm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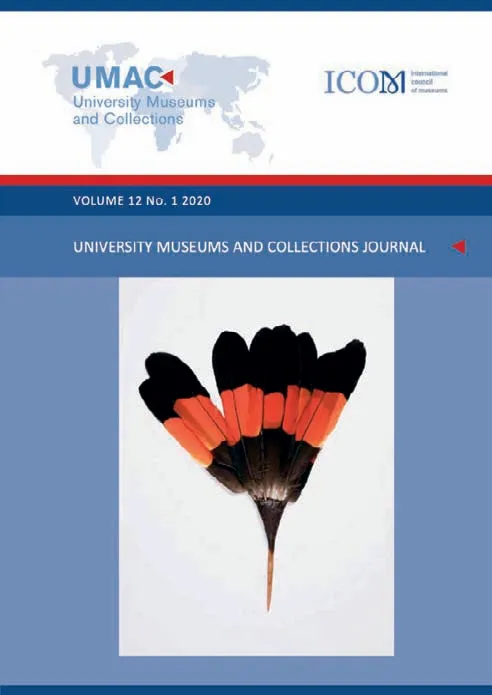
在新冠疫情期間策劃大學設計展
Mindplay: Curating and exhibiting design during COVID-19
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設計檔案館(The RMIT University's Design Archives,RDA)一直致力于20世紀以來墨爾本本地設計的收藏,這些收藏包含實物和虛擬作品,它們一起編織了設計之城墨爾本的現當代史;同時,自2017年以來,RDA一直保持著和院系的合作,將收藏開放給學生和教師,通過一年一度的策展項目推動以實踐為主的教學。
通常,策展項目會提前確定一個主題,學生會基于RDA提供的相關藏品進行研究和策展,最后呈現出一個實體展覽,其中所有的工作——從展覽設計、項目管理、展覽詮釋到媒體公關——都由學生主導。但隨著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出現,政府下達封城禁令,校園從3月開始關閉,線上授課取代了線下教學,實體的展覽和以工作坊形式為主的策展討論也變得難以實行。但對RDA和院系來說,這也是一個嘗試線上展覽的機會。線上展覽本身蘊含著更多線下展覽不具備的可能性,同時也可以令學生更自由地發揮創意。
2020年策展項目的主題是關于“澳大利亞設計之父”萊斯 · 梅森(Les Mason)。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不能見面的情況下保證學生之間、學生和RDA的工作人員之間的合作。項目負責人法延 · 戴維(Dr. Fayen d'Evie)在微軟的團隊協作工具Microsoft Teams上搭建了一個線上團隊,學生可以通過它分享視頻提案和電子藍圖,獲得老師和RDA工作人員的反饋,同時和其他學生進行交流。雖然彼此不能見面,但線上協作增加了合作頻率,也更方便工作過程的記錄和梳理。
另一個問題是,校園關閉使得RDA的藏品不能被隨時獲取。雖然在主題敲定時選好的相關藏品已經進行了電子化,但隨著研究的進行,產生了一些新的藏品需求,而有的藏品沒有電子文件。RDA的工作人員特地向學校申請,在一天內返回學校做了新藏品的電子檔案。
線上展覽的定位使“觀眾的線上體驗”成為了策展項目的重點,Z世代的學生們如魚得水地調配線上資源,使展覽更加“好玩和有互動性”。學生先是在展覽前期就開設了Instagram官方賬號@mindplay.lesmason,定期發布梅森的作品檔案和受梅森啟發創作的其他作品,在呈現Instagram展覽的形式上,學生甚至有意借鑒了RDA本身的櫥窗結構。線上展覽主要的呈現方式是網站,分為4個板塊:關于、故事、心靈游戲(Mind Game)和線上商店,學生們除了通過藏品介紹梅森的創作生涯和文化遺產外,還設計了允許觀眾制作梅森風格的貼圖和明信片的互動游戲,同時線上商店也搭建了一個展示和出售學生自己設計的衍生品的平臺,商品包括帆布袋、茶巾、明信片、字體和手機桌面圖,售出所得用以支持學院未來的教學工作。
來源: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2020年
作者:Ann Carew

數字時代的美術館:藝術的數據庫
Museums and digital era: preserving art through databases
數字語言的產生和進化意味著當代藝術在創作、傳播和保存方法上的改變。當代藝術作品變得不再有形,甚至不再是可以量化的物質。新媒體藝術成為了無階級的傳播空間、一種根莖般的結構,在這里藝術家的權威被稀釋,而公眾成為了開源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作品的意義只有在公眾參與的一刻、在作品不斷的復制和進化中得以完整。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美術館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以及傳統的保存和展覽方式也不再適用。
美術館在數字時代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新媒體藝術的出現恰好呼應了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新博物館學,比起只注重傳統的儲存與展示功能的博物館,新博物館學更強調博物館和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連接。這意味著美術館需要從倉庫變成一個開源的數據庫,里面儲存的信息也需要從靜態變成動態,隱藏變成可見。這也是對藝術轉向的呼應:數字藝術的角色也在向數據庫的方向轉變,作品成為了“用戶”分享知識和經驗的容器,藝術家是傳播過程的推動者。以安東尼 · 蒙塔達斯(Antoni Muntadas)的《檔案室》(The File Room)為代表的90年代網絡藝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古根海姆美術館對這一潮流做出了及時的呼應,在2002年委任藝術家馬克·內皮爾(Mark Napier)創作了網絡藝術《net.flag》。與此同時,出現了一些致力于數字藝術保存與展示的新型平臺,如獨立平臺“根莖”(Rhizome),又如古根海姆美術館的“可變媒體網絡”(The Variable Media Network)。
除了在作品和觀眾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梁外,對數據庫這一形式的強調還有另一層意義,即藝術作品應該以何種形式被整理和分類。新時代藝術作品的開放性和意義的不確定性,使得美術館不得不思考對元數據的重新定義。對內容和意義不斷豐富的數字藝術的保存變得更像是對不斷更新的數據庫的維護,這使得技術問題成為了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如何保證數據的安全,如何在儲存容器——硬件和軟件不斷更新的狀態下保證信息的正常獲取,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來源:Collection and Curation2019年,第四期
作者:Luis D. Rivero Moreno

如何展覽文學遺產
Literary heritage in museum exhibitions: Identifying its main challenges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作出了定義,并提出了一些保護和傳播的措施。這使得如何展示、詮釋和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了博物館學的一個研究方向。文學遺產因為其介于物質和非物質之間的特性,成為該方向很好的一個焦點。
起源于17世紀的文學之家博物館(literary house museums),通常選擇作家的故居作為展覽地點,同時試圖用作家的私人物件作為進入文學作品、創作背景的入口。從這個角度出發,文學之家不僅是一個提供沉浸式體驗的旅游項目,更是一個注重教育和互動的博物館案例。
本文著重分析的問題是:博物館在展覽文學遺產時,應該如何做才能使傳播效果最大化?作者采訪了7位加泰羅尼亞和俄羅斯的文學遺產和博物館學專家后,總結出了4點:首先是將文學類博物館營造成一個文學“景點”。雖然文學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在博物館展出的物件、手稿等是有形的物質遺產,需要在專家的指導下,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將無形的文化通過有形的物質體現出來。同時,專家指出了文學類博物館普遍缺乏推廣的現狀,并建議博物館和當地的文旅政府部門或公司合作。如何吸引訪客是個難題,因為普通觀眾,尤其是對其他國家的文學和作家不甚了解的外國觀眾,很難會主動去參觀一家文學博物館。此時博物館的角色可以轉變成將觀眾視為讀者的文學推廣者,作者稱贊了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純真博物館”(The Museum of Innocence),該博物館以同名小說為藍本,用83個展柜呈現了小說中的83個章節,帕慕克就是基于展柜中的物品展開自己的故事的。
其次,文學類博物館比其他博物館更需要專業導覽、工作坊、圓桌討論等公共教育活動,它們是在文學的非物質性和物質性之間建立對話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第三點,作者手稿、物件、故居等是非物質化的文學遺產的載體,它們也是文學得以被理解和傳播的基礎,因此博物館依然要重視展品本身的陳列,一些文學博物館甚至允許訪客聆聽或觸摸文學作品,希望從視覺以外的感官重現文學創作的歷史記憶;最后,文學作品的展覽往往不局限于博物館或故居空間內,因為一部文學作品的創作,甚至一位作家的人生軌跡,都和他所生活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息息相關。文學博物館可以和當地的文旅部門合作,將導覽拓展到博物館之外的空間,比如巴黎的雨果之家就在城市中設置了一條行走路線。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作者用4點標準檢視了3個著名的歐洲文學博物館網站:英國的莎士比亞故居博物館、德國的歌德故居、法國的雨果之家。之所以選擇網站而非博物館本身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網站通常是完整呈現博物館展覽和活動的平臺,并且網站經常是觀眾接觸到博物館的第一個途徑,網站本身設計得是否有趣,甚至會決定觀眾對這場文化之旅的期待程度。研究發現,3個博物館都比較好地反映了這些標準,同時又因地制宜地做了一些創新,可以成為全球文學博物館的參考范本。
來源:Muse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2020年,第三期
作者:Marina Strepetova, Jordi Arcos-Pumaro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