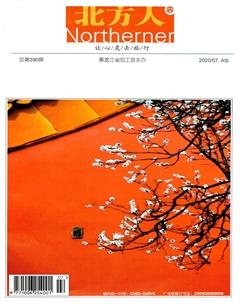真實(shí)、回憶與自傳
本·雅格達(dá)

回憶錄中的虛假還遠(yuǎn)不止刻意的謊言和虛偽的刪減。盧梭在《懺悔錄》中寫(xiě)道:“幾乎沒(méi)有一件曾打動(dòng)我心弦的事是我能清晰地回憶起來(lái)的。經(jīng)歷了那么多接二連三的事之后,很難避免把時(shí)間或地點(diǎn)張冠李戴的情況。我是完全憑記憶來(lái)寫(xiě)的,既沒(méi)有賴(lài)以佐證的日記或文件,也沒(méi)有能幫助我回憶的其他材料。我一生所經(jīng)歷的事情,有些像剛剛發(fā)生那樣,在記憶中十分清晰,但也有遺漏或空白,我只能用與我的記憶一樣模糊的敘述來(lái)填補(bǔ)。所以,有的地方我有可能寫(xiě)錯(cuò)了,尤其是那些無(wú)關(guān)緊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沒(méi)有找到確切的材料之前,我可能還會(huì)出錯(cuò)。但對(duì)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的敘述是準(zhǔn)確且忠實(shí)的。今后我仍將努力做到這一點(diǎn),大家盡可放心。”
后來(lái),盧梭還反復(fù)提到,雖然某些敘述可能存在謬誤,但這無(wú)關(guān)緊要:“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會(huì)記錯(cuò),我的感情驅(qū)使我所做的,我也不會(huì)記錯(cuò),我在這里寫(xiě)下的主要就是這些……我許諾交出我心靈的歷史,而為了忠實(shí)地寫(xiě)出這部歷史,我不需要其他的任何記錄,我只需要像我迄今為止所做的那樣,遵循內(nèi)心就夠了。”
盧梭一如既往地很有先見(jiàn)之明。如他所承認(rèn)的,也如一個(gè)世紀(jì)里心理學(xué)研究所證明的,人類(lèi)的記憶遠(yuǎn)遠(yuǎn)不能被當(dāng)成值得徹底信任的機(jī)制。傳統(tǒng)認(rèn)知把記憶當(dāng)成檢索系統(tǒng),就像能回放的錄像帶,或是能調(diào)取記錄的電腦。在這種模式下,記憶的能力受限于大腦的容量:當(dāng)某條信息被更新的或更緊迫的信息擠出去之后,它就會(huì)被遺忘。只有在患有精神疾病等特殊情況下,才會(huì)出現(xiàn)扭曲或虛假的記憶。
弗洛伊德提出了許多具有革命性的深刻見(jiàn)解,其中最為經(jīng)久不衰的觀點(diǎn)就是記憶是反復(fù)無(wú)常的。他探討了我們是如何被波動(dòng)的情緒捉弄的,以及我們的精神防御系統(tǒng)是如何(在他所謂的壓抑中)除去痛苦經(jīng)歷的。經(jīng)過(guò)無(wú)數(shù)次的實(shí)驗(yàn)和持續(xù)的研究,后來(lái)的心理學(xué)家取得了更大的進(jìn)展,他們發(fā)現(xiàn)記憶本來(lái)就不可信賴(lài):記憶不僅會(huì)因缺漏而變質(zhì),還不可避免地會(huì)被曲解和捏造。
記憶本身就是個(gè)有創(chuàng)造力的作家,它將“真實(shí)”的記憶、對(duì)世界的認(rèn)知、從各處收集來(lái)的線索以及對(duì)過(guò)往記憶的回憶拼湊在一起,看似有憑有據(jù)地想象可能發(fā)生的事情,然后妙筆一揮,把內(nèi)心的設(shè)想粉飾成了真實(shí)的場(chǎng)景。正如心理學(xué)家F.C.巴特萊特1932年在開(kāi)創(chuàng)性的著作《記憶》中所說(shuō):“記憶顯然更接近重建,而非單純的復(fù)制。”
而且,重建的過(guò)程受制于各種因素。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損失的部分越來(lái)越多。
導(dǎo)致曲解和謬誤的還不僅僅是時(shí)間。事件發(fā)生后,如果我們?cè)噲D記住得到的提示或建議,甚至是不易察覺(jué)的暗示,記憶就會(huì)迅速滋長(zhǎng)。
關(guān)于記憶的缺陷,著作最多的是心理學(xué)家丹尼爾·施克特。自傳和對(duì)過(guò)去的回憶都被他稱(chēng)為“偏見(jiàn)”的謬誤——我們的記憶總是不經(jīng)意地曲解過(guò)去。他在《記憶的七宗罪》中列出了記憶被曲解的五種類(lèi)型,它們都是經(jīng)過(guò)多項(xiàng)研究后總結(jié)出來(lái)的:“一貫型和善變型指的是人們根據(jù)自己的意愿和觀念,重新塑造或美化自己過(guò)去的經(jīng)歷。事后聰明型指的是人們用現(xiàn)在的知識(shí)去分析過(guò)去的事情。唯我型是說(shuō)在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感知和對(duì)記憶的精心編排上,自我扮演著重要角色。模板型指的是記憶在人們世界觀形成的過(gu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盡管人們對(duì)這種影響未必很清楚。”
以上幾種類(lèi)型的共同點(diǎn)在于,它們會(huì)讓記憶變得更引人入勝或更戲劇化,與充滿隨意性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相反。
記憶就像瑞士奶酪般漏洞百出,人們卻對(duì)其準(zhǔn)確性自信滿滿,這樣的矛盾似乎是人類(lèi)共有的特征。顯然,大多數(shù)自傳作者(盧梭的謙遜是個(gè)例外)反映了這一點(diǎn),他們甚至不會(huì)承認(rèn)自己的記錄并非百分之百準(zhǔn)確,哪怕其中包括對(duì)半個(gè)世紀(jì)前對(duì)話的逐字復(fù)述。實(shí)際上,記憶與敘述之間本來(lái)就存在一種無(wú)法解決的沖突,敘述講究細(xì)節(jié),而記憶在細(xì)節(jié)上著實(shí)不盡如人意。
自我暗示也是個(gè)問(wèn)題。寫(xiě)自傳這件事,與回憶這種無(wú)主觀傾向性的行為完全不同。在對(duì)各個(gè)事件、情節(jié)和人物進(jìn)行描述的表面下,是對(duì)自己一生的詮釋。隱含更深的是,作者希望證明把自己的人生寫(xiě)出來(lái)這件事具有合理性,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講了個(gè)有價(jià)值的好故事。
因此,事實(shí)是,一旦你開(kāi)始寫(xiě)自己人生中真實(shí)發(fā)生過(guò)的故事,還想把它寫(xiě)成別人可能感興趣的樣子,你就會(huì)開(kāi)始降低真相的標(biāo)準(zhǔn)。19世紀(jì),盧梭的后繼者中思想更成熟的一些人認(rèn)識(shí)到了這一悖論,其中包括司湯達(dá),他說(shuō):“我沒(méi)有說(shuō)我在書(shū)寫(xiě)歷史,我只是記下我的記憶,以便別人猜測(cè)我可能是一個(gè)什么樣的人。”
到了20世紀(jì)初,自傳已經(jīng)瀕臨崩潰。它承受了來(lái)自社會(huì)階層的差異、公共與私人的對(duì)立、坦率的限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壓力。問(wèn)題的關(guān)鍵還是易犯錯(cuò)誤的記憶,以及“真相”的混亂本質(zhì)。思忖至此,一個(gè)認(rèn)真的作家怎樣才能書(shū)寫(xiě)自己的人生呢?20世紀(jì)初,馬塞爾·普魯斯特做了一個(gè)極佳的選擇,那就是讓自傳在想象的加溫下慢慢升騰,最終被塑造成小說(shuō)。另一種選擇是承認(rèn)目前的困境,然后往前看。亨利·亞當(dāng)斯在自傳中以特有的第三人稱(chēng)視角來(lái)講述自己,率直、無(wú)畏且超前,像是美國(guó)版的盧梭。他寫(xiě)道:“這就是他記憶中的旅程。實(shí)際情況可能有很大不同,但實(shí)際的經(jīng)歷沒(méi)有教育意義,記憶才是最重要的。”
摘自《偽裝的藝術(shù):回憶錄小史》